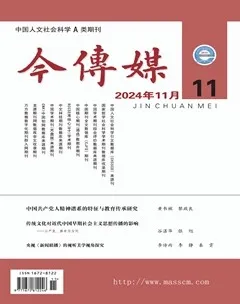主旋律影視作品中家國形象建構研究
摘 要:近年來,國家大力支持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創作發展。新時代背景下,電視劇《覺醒年代》作為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優秀代表,不僅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承擔了一定的社會文化功能。文化職能是主旋律電視劇的一個重要職能,主旋律電視劇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者,承擔著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文化功能。近年來,一些優秀的主旋律影視作品不僅展現了國家文化新的內涵,詮釋了新時代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增強了觀眾的文化認同感與自信心。本文對電視劇《覺醒年代》的敘事策略進行了分析,啟發觀眾正確看待歷史,全面認識歷史人物和繼承發揚中國精神。
關鍵詞:主旋律影視作品;敘事方式;文化內涵;家國形象建構
中圖分類號: J9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8122 (2024) 11-0068-04
一、主旋律影視作品的發展
(一)主旋律影視作品的文化功能
主旋律影視作品是一個特定概念,早在1987年時任國家廣電部電影局局長滕進賢就提出影視作品要“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化”,主旋律影視作品就此誕生。它是指以弘揚社會主義時代旋律為主旨,激發人們追求理想的意志、催人奮進的影視作品。我國的主旋律影視作品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能夠激發觀眾追求理想信念,給予人們奮斗向上的力量以及精神鼓舞,體現的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內涵。中華文化的特點在于崇尚禮儀,注重人倫關系和社會和諧。主旋律影視作品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下發展的,具有強大的文化引領功能,使觀眾能夠獲得對于新時代語境下自我的身份認同,也是升華內心情感的重要途徑。主旋律影視作品通過敘事的時間長度、傳播的廣泛性以及表現空間的復雜性,實現了自身的文化功能。
(二)主旋律電視劇的創作視角轉變
近年來,主旋律電視劇逐漸形成了多元化發展的局面,一系列視角多樣、題材新穎的電視劇作品出現在觀眾視野中。比如,引發較大關注的刑偵題材劇《狂飆》,通過時間線索串聯起重要節點,講述了主人公安欣與高啟強在20年時間里展開的博弈。整部電視劇不僅對人性進行了細致刻畫,也對社會現實進行了深度反映,引發觀眾思考。而當代農村題材電視劇《山海情》,是一部展現新時代社會變化的重要作品,該劇塑造了西北山村中的農民群像,真實反映當地環境,表現了人們在脫貧致富的道路上積極響應號召,為實現嶄新發展作出的一系列努力。這一題材與新時代息息相關,體現了藝術性與時代性的結合。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獻禮劇中,《覺醒年代》通過高質量的制作、多元的人物塑造得到社會廣泛關注,并獲得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實現了主旋律電視劇的創作視角轉變。該劇作為主旋律電視劇創新發展中優秀的典范,其創作方法有諸多值得借鑒之處:第一,新的視角。傳統主旋律電視劇多聚焦革命領袖、英雄人物的事跡,而《覺醒年代》則主要表現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人物形象。第二,新的形式。《覺醒年代》通過運用版畫的形式營造出凝重的歷史感和藝術感。第三,新的生態。《覺醒年代》運用商業化營銷策略,通過粉絲經濟和線上線下聯動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綜上所述,作為一部優秀的主旋律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以獨特的敘事視角,匠心獨具地展現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復雜的社會背景以及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二、電視劇《覺醒年代》的敘事脈絡
(一)宏大敘事與微觀敘事相結合
敘事策略是創作者根據藝術規律和市場原則針對特定題材而專門制定的敘事風格。宏大敘事是一種對人類歷史發展進程有始有終的構想形式,與著重描寫細節和個人生活的微觀敘事相對應。《覺醒年代》的宏觀敘事描繪了“近代內憂外患,先進知識分子希望拯救危難時期的中國”這一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社會背景。多羅西·羅斯曾說:“由于將一切人類歷史視為一部歷史,在連貫意義上將過去和現在統一起來,宏大敘事必須是一種神話的結構。”[1]但是,這種結構的宏大敘事難以讓觀眾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對此,創作者要將宏大敘事與微觀敘事相結合,關注個人命運和心理成長,這樣才能被觀眾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覺醒年代》展現了宏觀敘事層面的變革。辛亥革命后,為了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李大釗、陳獨秀等先進知識分子積極探尋救亡圖存的方法。故事背景設定在袁世凱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之后,著重展現了陳獨秀提出創辦新青年雜志、改造國人思想,以及之后的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幾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時間節點。
此外,《覺醒年代》中還穿插了微觀敘事來體現細節,通過陳獨秀、李大釗兩個家庭的故事,塑造了二人在家庭中作為父親、丈夫的角色形象,拉近了觀眾與歷史人物之間的距離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宏大敘事帶來的抽象性,使觀眾更容易產生共情。在以往的歷史作品中,李大釗常常被塑造成較為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而《覺醒年代》表現的是其作為普通人的形象,通過他和妻子趙韌蘭在相處過程中經常提到其小名“憨坨”這一細節,體現出家庭的溫情氛圍和李大釗人格的質樸。相比較而言,陳獨秀的家庭并不是很溫馨,由于他一心進行革命事業,幾乎沒有時間陪伴家人,兒子陳延年對此非常不滿,所以總是直接喊陳獨秀的名字,從不叫他父親。該劇沒有回避人物之間的矛盾,對陳獨秀父子之間沖突的渲染,不僅展現了陳獨秀復雜的人物形象,也讓觀眾更加理解他的想法。
(二)時間敘事和空間敘事相結合
時間與空間是構成世界的要素,也是影視藝術敘事的基本元素。影視藝術將時間藝術和空間藝術相互融合,形成了時空藝術的表現形式。巴赫金提出:“時間的標志要展現在空間里,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這種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標志的融合,正是藝術時空體的特征所在。”[2]
在時間敘事上,《覺醒年代》以歷史發展為順序,縱向刻畫了從1915年到1921年之間的思想文化變革,展現了一系列的歷史事件,依次為:第1集到23集的新文化運動, 24集到37集的五四運動, 38集到43集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在空間敘事上,以《新青年》誕生地上海和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作為主要陣地,通過時空交織表現出了中國社會的變化,以及民族覺醒的歷史必然性。作為一個完整時空體的兩個敘事維度,時間敘事與空間敘事往往并行,展現歷史脈絡,說明歷史邏輯。《覺醒年代》通過時間線上重大歷史事件的敘述,以及空間線上《新青年》雜志為承載,在北京、上海兩座城市開展運動時所作的努力,兩條線索相互穿插來表現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歷史脈絡,展現了立體的歷史背景。
(三)歷史敘事和情感敘事相結合
首先,主旋律電視劇作品中對歷史事件的展現是基于歷史共識的定論,表現厚重的歷史質感,但要設定一個起點,這是人為的,不是歷史本身的存在,設定時敘事的目的就已蘊含其中。比如,《覺醒年代》的故事起點設置在“二十一條”簽訂之后,且在第1集到第23集中采用較大篇幅表現新文化運動時期由器物逐漸轉向文化層面的變革,并對這一重大時期進行了完整書寫。此外,還通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內在聯系,勾勒出建黨的歷史邏輯;劇中的歷史敘事旨在發現歷史事件中鮮為人知的側面,而文化層面的變革、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也是通過辯論或者激烈討論進行展現,比如胡適和李大釗思想上的沖突,這種表現形式與真實歷史形成互文,實現了歷史質感與藝術效果的統一。
其次,《覺醒年代》敘事中的情感融入,突破了以往部分主旋律作品表現題材宏大、敘事內容空泛的問題,為宏大的歷史敘事融入了溫情。其情感敘事主要圍繞李大釗、陳獨秀的家庭關系展開。學生們對李大釗非常尊重,而妻子趙紉蘭經常會喊李大釗的小名“憨坨”,這為人物刻畫增添了一絲生動性,也對李大釗和妻子趙韌蘭的感情進行了渲染。趙韌蘭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婦女,雖然不懂李大釗的先進想法,但對李大釗毫無保留地信任,并且尊重支持他的事業。同時,情緒渲染也含蓄地表現了二人的感情。趙韌蘭來看望李大釗時下著大雨,屋檐下鈴鐺發出清脆的聲音,最終趙韌蘭看著李大釗的背影遠去,這種通過環境烘托人物情感的表現手法,非常具有感染力。同樣,在高君曼等待丈夫陳獨秀的場景中,她撐著油紙傘站在雨中盼望丈夫歸來并為他撐傘的畫面,令人動容,二人之間的感情也在傾盆大雨中更加堅定了。由此可見,情感的融入不僅淡化了主旋律電視劇歷史敘事的厚重感,也更好地體現了電視劇中的人文關照。
三、電視劇《覺醒年代》的人物形象塑造
(一)人物內在生命力的表現
影視作品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人物形象,內在生命力是人物形象的精髓。《覺醒年代》中每個人物都有其特色,并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因為作品在基于史實的基礎上進行合理化想象,推敲人物的動機,給思想變化和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撐,使觀眾能夠理解每一位歷史人物的抉擇。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之間的沖突更多是思想觀點上的交鋒。《覺醒年代》中的沖突大多是建立在人物觀點之上,無論是胡適和辜鴻銘的交鋒,還是李大釗和胡適的辯論,都是不同性格人物之間發生的碰撞,使得劇情合理嚴謹,并且表現出人物的內在生命力。
胡適和辜鴻銘的交鋒展現了二人的不同性格。北大開學典禮上蔡元培邀請胡適發表演講,辜鴻銘因對年輕且資歷尚淺的胡適入選評議會成員感到不滿,于是,在演講時用希臘文的《荷馬史詩》質疑胡適的發音不標準,并展示標準語調,這一情節著重表現他刻板嚴謹的性格——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規矩來。而胡適則認為內容遠比語音語調更重要,表現了他對于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系的辯證思考——從遵循較為刻板保守的形式到更加注重文字內容和表達的意義。胡適支持改革,在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后,就在與陳獨秀的交談中提到:“正確對待傳統文化不是全盤否定,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改良,新文化也是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產生的。”作為先進思想和保守思想的代表者,胡適和辜鴻銘二人的思想表現了新文化和傳統文化之間的碰撞,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也正是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開始。
(二)表現視角的客觀真實
表現視角是否客觀真實,對主旋律電視劇而言非常重要。《覺醒年代》的編劇龍平平秉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注重把握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主創人員為了更加真實地表現人物,搜集了大量資料,比如趙韌蘭對李大釗的稱呼——“憨坨”,就是在走訪了李大釗的后人之后才得知的。
對于劇中涉及的著名歷史人物,比如陳獨秀,創作者客觀真實地向觀眾展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并不是傳統的完美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位性格復雜多變的領導者,有時神采飛揚,有時灑脫不羈,有時比較獨斷。辜鴻銘是守舊派的突出代表之一,作為北大教授,盡管他學貫中西、精通多國語言、才華橫溢,但是,思想保守封閉、反對變革、不接納新的事物。留學歸國的胡適是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的學生,但他的見解與陳獨秀、李大釗二人相左。對于胡適的性格,在李大釗與胡適的爭論中得以體現,且二人的思想不盡相同。在胡適心里,學術前途和家庭的幸福是最重要的,并且提倡實驗主義。這與李大釗主張行動的觀點相悖,也為之后二人分道揚鑣、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作了鋪墊。從人物塑造的角度能夠看出,劇中人物都有其性格特點,這體現出歷史的真實性,也表現出電視劇創作中對于人物塑造的客觀辯證態度。
此外,人物謝幕的場景也頗具深意。陳獨秀最終走向森林深處,大片的綠色象征著朝氣蓬勃、充滿生機的中國共產黨逐漸成長為參天大樹。李大釗站在長城上眺望遠處的青山,宏偉遼闊的背景象征著生命不息、戰斗不止。對毛澤東采用仰視的拍攝角度,表現出偉人的崇高形象——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他站在山頂,欣賞著祖國的大好河山。這一場景表現出毛澤東豁達樂觀的心境,正如他在詩詞中所寫:“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四、電視劇《覺醒年代》的家國形象建構
家國形象的建構與民族文化認同是主旋律電視劇經常會表現的一個重要議題。家庭關系是主旋律電視劇中重要的表現內容。在《覺醒年代》中,通過敘述陳獨秀和陳延年、陳喬年兄弟二人之間從沖突、矛盾到和解的過程,展現了典型的中國式父子關系。陳延年、陳喬年兄弟二人在小時候對陳獨秀忙于事業而不顧家庭的表現非常不滿,也因缺乏交流而顯得非常生疏,關系僵硬,于是,陳喬年對陳獨秀直呼其名,陳喬年則偷偷地把父親飯菜中的荷葉黃牛蹄換成了癩蛤蟆。后來,在父子的相處過程中,陳延年漸漸理解了陳獨秀,對他的稱呼也從直呼其名到喊父親,并主動給他倒茶,而陳喬年也用自己做的荷葉黃牛蹄向之前對父親的無禮戲弄道歉。陳延年、陳喬年去法國留學前跟父親道別的場景主要是情緒的鋪墊,情節中沒有大段的臺詞。陳延年看著父親的背影,依依不舍,突然從背后緊緊抱住了父親,此時,陳喬年也上前,父子三人緊緊擁抱,含蓄而有力,這是他們最后的告別。當陳獨秀向家人道歉并最終決定獻身革命時,陳延年也表示要立志為國家奉獻,父子二人同為革命事業而奮斗。兩人之間的感情包含了陳延年作為一位革命青年對于革命前輩的敬意。為了國家而奉獻自己的一切,表現出陳獨秀父子的民族大義,該作品也通過對家庭和國家的敘事凸顯了我國革命先輩的堅定決心和偉大情懷。
在陳延年、陳喬年犧牲的最后一幕中,二人腳上戴著鐐銬,踏過路邊的桃花,英勇就義。最終,回眸的笑臉與陳獨秀的悲傷相交織,賦予作品更加深刻的內涵。盡管父親和兒子有著不同的初衷,但是最終走上了同一條路,為了革命而戰斗的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該劇通過敘述一個家庭對革命事業所作出的犧牲和努力,以小見大,以小的家庭來映照整個國家,展現出革命先輩崇高的形象,也表現出他們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與民族責任感。
五、結 語
綜上所述,《覺醒年代》將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相互融合,實現了對于主旋律電視劇的創新性突破,讓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得以詮釋。在敘事層面上,通過宏大敘事與微觀敘事、時間敘事與空間敘事、歷史敘事與情感敘事三種敘事脈絡交錯并行,構建了廣闊的格局,體現出厚重的歷史感。在人物塑造上,以性格之間的沖突來表現人物的矛盾,符合作品中文人的形象特征。在家國形象的建構上,以小見大,通過家庭來映照國家,體現出家與國的統一。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處在新時代,回望歷史,回望新文化運動時期文人志士為國家所作的貢獻,我們不僅要銘記在心,更要立足當下,為國家奉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不忘初心,繼續前行。
參考文獻:
[1] 尹鴻,楊慧.歷史與美學的統一:重大歷史題材創作方法論探索——以《覺醒年代》為例[J].中國電視,2021(6):6-12.
[2] 劉永昶.思想的光芒照耀歲月長空——論電視劇《覺醒年代》的歷史敘事[J].中國電視2021(6): 13-16.
[3] 崔靖晗,蘇米爾.我國主旋律電視劇的美學嬗變與品格建構[J].中國電視,2018(1):67-71.
[4] 宋獻偉.新時代黨史紀錄片時空敘事的美學轉向[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1(11):96-101.
[責任編輯: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