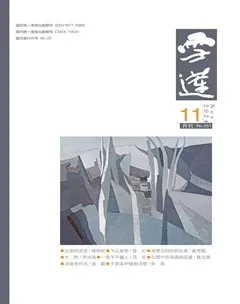一輩子不騙人(組詩)
一樹紅葉
剛剛在對岸
我沒有看見
那樹紅葉
我是在抵達
河的另一邊
朝對岸看時
才注意到
有一樹紅葉
經過辨認
還發現剛才
我就是從它
下面經過的
針 灸
我堅持只做按摩
不扎針灸
但最終因為
丁大夫的一句話:
“你兒子都敢
你怕什么”
放棄了抵抗
我是想體驗一下
針灸扎進肉
到底能疼到
什么程度
滾一邊去
走在兩個年輕人身后
聽到一個對另一個說:
“人老就應該滾一邊去”
我看了看伸手可及的墻
對自己的表現挺滿意
其實就是年輕的時候
我也是沿墻根走路的
不需要別人提醒
身為詩人我早就知道
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二月二
頭發還不長
我就不理了
就算頭發長
我也不用理
對于一個腦袋
從來都是
高昂著的主兒
我就不用
湊龍抬頭
這個熱鬧了
感 動
詩人湘蓮子
給我發來一篇
針對痛風患者
飲食注意
事項的推文
令我感動不已
盡管我有病
但不是這個病
暫時還用不上
在大學食堂
三十年過去了
食堂已不是
原來的食堂
但還在原來的位置
坐在那里吃飯
我以為會流淚
至少會傷感
結果一個都沒有發生
唯一的感受是
飯菜有點難以下咽
我沒吃完
我終于聞到了年味
老同事才讓
患了骨髓炎
流水不止的膝蓋
在他求醫無數
花錢無數的
七八年之后
終于愈合了
拜河南汝州
一個老中醫的
一貼膏藥所賜
是臘月二十七
我代表單位
前去慰問他時
才知道的
與此同時
還聞到了年味
雖然沒兩天
就要過春節了
但聞到年的氣息
還是頭一次
看 病
張大夫剛剛給我
講完飲酒的危害
興沖沖推門而入的
另一個大夫對他說:
“劉冰他們來了
今晚咱們攢一個飯局”
張大夫一改沉穩
也變得興沖沖地說:
“好啊,不醉不歸”
全然忘了我
這個病人的存在
打的的時候被打臉
時間緊張
我沖進路邊停著的
一輛出租車
司機告訴我等一會兒
上一位乘客
去手機城里拿車費
我等得不耐煩說:
“不會不回來了吧”
“才十幾塊錢
不至于吧”
“十有八九跑了”
正說話間
一個男人拉著
一個女人過來
女人用手機掃了
車里的付款碼
男人在旁邊說:
“你給他付15元”
我看了一下計價器
顯示的是14.20元
憂 慮
單位的兩個年輕人
相繼辭職了
他們的理由如出一轍:
“出版工作壓力太大
精神和身體都頂不住
想休息一陣子”
可他們卻分別在
離開我們單位
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出現在另一家
出版社的座位上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
不能說一句實話
當然對于他們來說
這可能不是問題
大 雨
抵達玉樹的當晚
下了一場大雨
當地朋友說
我們這里很久沒有
下過這么大的雨了
一定是你們帶來的
雖然我知道
我們沒有那個能耐
但我無法證明這一點
就什么都沒說
釋 然
早晨洗臉
聞到手上
有一股魚腥味
不免暗自納悶
近幾天我沒做魚
也未吃魚
后來依稀想起
昨夜夢中抓魚
在故鄉的
那條小河溝里
嘆 息
我還記得他
在一個飯局上
借助半斤白酒
激情澎湃地說:
“時間終會證明
我是偉大的”
可是離他故去
才僅僅三年時間
就很難在紙面
或者網絡上
見到他的名字了
偶爾有人提起
說的也是他
不夠檢點的私生活
這檔子爛事
魔鬼刀
買回魔鬼刀的當晚
兒子一臉慌張
從書房里沖出來說:
“把魔鬼刀撈出來
否則明天魚缸里的魚
會死掉一大片”
他還告訴我
魔鬼刀專吃他魚的眼睛
我不以為然
第二天果然出現死魚
是兩條魔鬼刀里的一條
我不但沒有難過
相反還一陣竊喜
對于將網絡視為上帝的兒子
這是一個教育
哪有那么多來日方長
有一年夏天
唐欣來青海
與他們學校的
老師和學生
給龍羊峽旅游公司
進行營銷策劃
一住就是一星期
末了我倆在西寧
匆匆相見
席間他說:
“如果合作順利
每年我都會過來”
言外之意
每年我倆都會
在青海一聚
而后他再未來過
即便他們學校
與龍羊峽還能夠
再續前緣
他也不大可能
利用這種機會
出現在青海了
翻過年他就要
步入退休生活
在醫院陪床
幾十年后
我又和我媽
躺在一起睡覺
(盡管分屬兩張床
但是緊挨著)
由此我發現了
我與我媽的角色
發生了互換
我變成了媽媽
她變成了孩子
我是在聽著她
發出輕微的鼾聲后
才漸漸入睡的
從酒吧里聽來的詩
五十歲左右
樣子疲憊的女人說:
“當初選擇的時候
我是認真權衡過的
覺得你不靠譜
他比你穩當一些
結果他也太穩當了
現在一句話都沒有
看來我錯了”
五十歲左右
樣子也疲憊的男人說:
“你沒有錯
如果那時你選了我
可能到現在
不但一句話都沒有
連婚都離了”
女人說:“你的意思是
我怎么選擇都是錯的”
男的說:“我拿不準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你的選擇不是最壞的
說不定還是最好的”
我很欣賞那個男人
在我起身離開的時候
還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竟意外地發現
也有一頭卷發
長得有點像我
自作多情
夜晚散步回來
遠遠地看見
兩個年輕人
在樓梯口擁吻
我沒有繼續前行
而是躲在一棵
老槐樹的后面
自然不是為了偷窺
而是怕打攪了
他們的好事
這下可好了
一呆就是抽掉
兩根香煙的時間
天氣寒冷
凍得夠嗆
好在有一個老頭
估計眼神不咋地
一頭撞了上去
直到我也沿著
老頭開辟的道路
途經他們身邊
也未見其分開
像被蘋果砸到的
英國人牛頓那樣
才徹底回過味來
原來是我想多了
他們不怕人
讀 史
盡管這無法證明
但我還是堅持認為
如果宋徽宗像接受
《千里江山圖》那樣
接受了《千里餓殍圖》
不殺作者王希孟
而是予以嘉獎并通告天下
他的大好山河就不會
在短短的十三年之后
被金兵踐踏摧殘
自己也不會那么快
成為北寒之地的階下囚
甚至終其一生
都不會成為階下囚
羞 愧
一場戰爭
將李白卷入其中
差點要了他的老命
在一片喊殺聲中
杜甫并沒有因為
李白所處的政治陣營
是自己反對的
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
對他大加同情
寫詩呼吁
釋放李白的意思
不長眼睛的人
都看得出來
對友誼的這種態度
擱到千年后的今天
也足以令人羞愧
至少我羞愧了
這個世界
下在立夏前夕的
一場暴風雪
被我拍成視頻
發到朋友圈
有人留言說:
“這個世界亂了”
其實沒有亂
或者可以說
一直都是亂的
在我身處的高原
幾乎每年都這樣
只是之前
我沒有拍視頻
發朋友圈
這樣一個人
在其晚年
把心愛的別墅
給皇帝捐了
建成寺院
把賴以為生的
職田生產的糧食
準備熬成粥
給災民們吃
盡管皇帝沒允許
把自己的官職
還給了皇帝
只求把弟弟
從四川調回長安
兄弟能夠相聚
活得這么明白的人
即便不是寫出
“行到水窮處
坐看云起時”的
我的大師王維
我照樣喜歡
并且尊重
美 味
在我家院子里
有不少標識鮮明的
鼠藥投放點
每次看到它們
我都會想
對老鼠而言
這一定是美味
盡管吃完
就不美了
進而想到
對人來說
是不是也存在
這樣的美味
而我們并不知道
在吃下之后
毒發之前
講真話豈是那么容易
我向一個人約稿
他給我發來
比我要求的
多得多的作品
我勉強選了一首
并且通知他
他不依不饒地追問:
“能否對我寫的詩
給一兩句真話”
真話是“你別寫了”
但打死我也說不出口
只能用一句假話代替
幻 覺
打針的時候
父親躺在病床上
睡著了
發出輕微的鼾聲
我坐在板凳上
撥拉手機
過一會兒就抬頭
看一眼點滴
在這個過程中
我出現了
好幾次幻覺
雖然我也清楚
這是幻覺
但又止不住
信以為真
流進父親
身體里的液體
也在一滴一滴
流進我的身體
打羽毛球
女孩每打不到球
就大聲責怪男孩
球打得不好:
“你是大笨蛋”
即便男孩每次
都努力按照方便女孩
接球的方式回球
也無濟于事
看得我哈哈大笑
但很快就笑不出來了
是因為想起某些人
其中就有我的一個
人生很不如意的朋友
在生活中的表現
跟這一樣一樣的
旱 獺
我手指車窗外
對后排的人說:
“快看,旱獺”
但是已經晚了
它瞬間鉆進洞里
除了我車上的
同伴無人得見
盡管沒有誰提問:
“為什么只有你
看見了旱獺”
但我還是要說:
“因為我一直在看”
不過也只是想了想
并未真的說出來
在梅家塢
看過采茶大媽
怎樣采茶
從山上下來
我再也不敢
跟賣茶的
討價還價了
雖然最終
因為囊中羞澀
還是討價還價了
馬大夫
接到一個電話
對方開口就問:
“你是馬大夫嗎”
我說:“不是
我是馬詩人”
掛斷之后
有點后悔
因為說了假話
我當然也是大夫
只不過他的病
可能不在我
診治的范圍內
耳 光
我媽給我二姨
寄了一包衣服
被快遞員弄丟了
在交涉過程中
快遞員向我媽
哀求不要投訴他
否則工作不保
包裹里的東西
不管值多少錢
他都會如數賠償
我媽據實相告
過了幾天
我媽來我家
并把此事告訴我
我也就順嘴一說:
“你多說一點
他也會賠給你的”
我媽的回答
雖然聲音不高
但還是響亮地
在我的臉皮上
抽了一記耳光:
“我一輩子不騙人
不能老了老了
為了一點兒錢
就把名聲壞了
我才沒那么傻”
賊心不死
世界接吻日這天
在我的朋友圈里
涉及這一話題的
只有幾個老男人
和幾個老女人
如果我不知道
他們都是詩人
一定會朝歪里想
使用“賊心不死”
這樣的形容詞
恐怕也在所難免
盡管他們的確有
賊心不死的意思
但對于詩人
這是允許的
也是必須的
任誰都能看出這是一個夢
司機跳下
行駛中的汽車
把不會開車的
一干人等
留在上面
其中包括我
車正在下坡
騎行記
我正在騎車
碰到同居一院
正在散步的老張
老張問我:
“你干啥呢”
我猶豫了一下
但還是如實相告:
“騎自行車”
快 樂
在盛夏的濟南
一片蟬鳴聲中
一個朋友對我說
他最快樂的事情
就是帶兒子
夜晚拿著手電筒
來到小樹林
捕捉剛剛破土而出
爬到樹干上的
知了幼蟲
拿回家
趁活著
油炸了
下酒吃
一點也沒意識到
他的快樂
是以屠殺
另一種生命為代價
獲取的
天 才
我遇到一個天才
他問了我一個
吃了幾十年西瓜
都從來沒有
想到過的問題:
“西瓜瓤為什么
是紅色的”
東京的夏天
我還沒有
到過日本
但我看見
東京的夏天
是美麗的
兒子在那里
戀愛了
他人不是地獄而是暖氣
如果你有大冬天
在路邊等出租車
等了半天才等到
前一位乘客剛下來
你就坐上去的經歷
而且就坐在了
前者的屁股
剛剛坐過的位置
你一定會同意
我的如上說法
格桑花
格桑花是高原上的花
在牧草里生長
與其他野花雜陳
非常遺憾
我尚無法說出
它的高矮以及
花瓣的顏色
無法指出
格桑花是哪一株
但我可以告訴你
草原的花都很美麗
它就在里面
風吹過
有一種香氣
為它散發
昆侖山
在格爾木街頭
當我提及昆侖山
你手指遠處
一抹朦朧的山脈
告訴我:“那就是”
我沒有驚訝
我已經習慣于
偉大的事物出現時
那種稀松平常的
靜悄悄的方式
腳踩軟墊
貓步而來
【作者簡介】馬非,生于1971年,詩人,出版詩集《寶貝》《青海湖》《那個人》《為時不晚》等9部,部分作品被譯成英語、德語、西班牙語、韓語、日語。榮獲2013年長安詩歌節現代詩成就獎、磨鐵詩歌獎·2017中國年度詩人大獎、第十屆(2020)《新世紀詩典》李白詩歌獎成就獎。現居青海西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