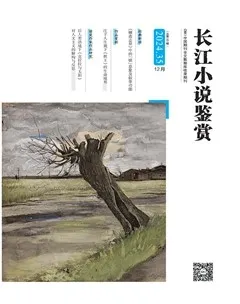逃遁?守望?和解?
[摘" 要] 杰羅姆·大衛(wèi)·塞格林在《麥田里的守望者》中塑造了一個被主流價值文化沖刷至社會邊緣的典型“他者”形象——霍爾頓。霍爾頓的生活狀況和精神追求體現(xiàn)出他對家庭、社會的逃避,反映出個體自我精神的孤身流浪。自我價值與在世價值的沖突與錯位,導致霍爾頓產(chǎn)生無處不在的疏離感,成為一個被社會“異化”的他者存在。
[關鍵詞] 麥田" 守望者" 他者" 霍爾頓" 異化
[中圖分類號] I106.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35-0054-04
《麥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國作家杰羅姆·大衛(wèi)·塞格林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于20世紀50年代,描繪了主人公霍爾頓的學習生活及精神狀態(tài),展示了霍爾頓對人生與生活的迷惘,對象征純真世界的“麥田”的無限向往。霍爾頓是一個時代少年群體的縮影,也是整個社會文化意蘊的承載者,我們可從他身上看到主體心靈與社會規(guī)約相互摩擦對主體造成的沖擊與碾壓,導致主體精神支柱崩塌,人生坐標迷惘,產(chǎn)生一種無處容身的異化感。雖然霍爾頓的時代已經(jīng)離我們遠去,但在信息化、現(xiàn)代化高速發(fā)展的今天如何避免“霍爾頓”式的精神悲劇,在競速時代如何實現(xiàn)“靈”與“肉”的和諧,實現(xiàn)“詩意的棲居”,這都是值得人們思考和探討的話題。本文試從霍爾頓的現(xiàn)實生活和精神世界兩個角度入手,分析霍爾頓的形象特點,揭示其“異化”生存狀態(tài)下的疏離感,探究其成因,尋求解決辦法,進而啟發(fā)人們對當下的生存狀態(tài)進行思考。
一、“他者”的境地——現(xiàn)實生活的反叛者與逃遁者
“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論中一個常見的術語,稱主體為“自我”,稱對方為“他者”。后來拉康和薩特把“他者”引入哲學,形成哲學名詞“他者意識”和“他者理論”,“他者”一詞被廣泛運用于女權主義理論著作中。“他者”意味著在當下生存環(huán)境中沒有自我主體意識,在客觀環(huán)境中處于被動地位,精神游離于主流價值觀以外,沒有主觀人格和話語權的異化形象。《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爾頓就是一個“他者”,他出身于美國20世紀50年代一個富裕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作為一個年僅16歲的中學生,首要任務應是好好學習,做老師心中的好學生,家長心中的好孩子。然而霍爾頓無心學習,考試成績很少有及格的,對校長及學校的一切都是一副不屑一顧的態(tài)度,屢次被學校開除。在被學校第四次開除后,他竟然像甩掉了沉重的包袱一般,離開了潘西中學,離開了他待不下去的令人窒息的“破環(huán)境”,因為他在學校總是感受到迎面而來的孤獨。最終他卸掉思想包袱,在大街上游蕩,做出一系列“流氓痞子”行為,如大口抽煙,拼命酗酒,隨意玩女人,遇到不順心、不合意的事就破口大罵“他媽的”。他渴望善良與真誠,但目睹的全是丑惡與欺騙。他用一雙獨有的、穿透現(xiàn)實的慧眼識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假丑惡,跟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打交道,發(fā)現(xiàn)有些孩子也都“成人化”了。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意味著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找不到自我存在的價值感與歸屬感,唯有通過反叛現(xiàn)實中的一切來發(fā)泄內(nèi)心的壓抑與痛楚。不好好聽課、考試不及格、跟老師頂嘴、滿口臟話、濫吃濫用等舉動意味著他走向一條離經(jīng)叛道之路,他鄙視流行的價值觀念,對正統(tǒng)的美國文化抱持逆反心理,他不想“上大學,坐辦公室,掙大錢,買混賬的凱迪拉克”[1],抱著“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傲然態(tài)度走向身體與心靈的流浪之路,尋求自我救贖。但這種方式并沒有讓他在世俗社會中找到自我的位置,也沒能獲得人們的關注。在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引領下,人們一切反叛現(xiàn)實、尋求自我的努力都成為荒誕之舉,而這也意味著霍爾頓對現(xiàn)實生活的所有反叛是一種徒勞。
在對主流文化價值觀的反抗失敗后,霍爾頓又開始尋求“逃遁”的慰藉,而充當這一慰藉的便是那頂紅色鴨舌帽,那頂帽子是保護內(nèi)心、逃避外界的屏障,象征著他對自我內(nèi)心的保護,象征著自我與現(xiàn)實生活的周旋。霍爾頓每次拉下鴨舌帽都會遮住自己的眼睛,他不想看到成人世界的污濁。被斯特拉德萊塔狠揍一頓后,他便開始尋找那頂能撫慰他心靈的帽子:“我哪兒也找不到我那頂混賬獵人帽子,最后才在床底下找到。”[2]這個紅色鴨舌帽就是霍爾頓精神遁世的避難所:當他無辜被室友毆打后,即便鮮血直流,也不忘找他那頂鴨舌帽,并且還戴著它照鏡子,尋求精神上的慰藉。鴨舌帽成了他逃避污濁世界和殘酷現(xiàn)實的有效屏障,帽檐的遮掩能讓他獲得一點精神的安慰,但超越世俗、追求純粹精神的自我是不現(xiàn)實的。畢竟霍爾頓是社會中的人,社會的道德制度、主流價值觀、行為規(guī)約猶如一張張結實的網(wǎng)把他牢牢網(wǎng)住,不論是選擇反叛還是選擇逃遁,他都不能徹底實現(xiàn)自我的解救與心靈的救贖,而是被置于群體之外的“他者”境地。
二、“他者”的守望——田園牧歌似的精神堅守
霍爾頓靈魂的自我指向恬靜悠然的大自然,渴望純真與童趣,而肉身的自我卻被社會的道德規(guī)約、主流價值觀推向追求人生的飛黃騰達、功名利祿。當靈魂的自我與肉身的自我背道而馳,肉身的自我自然會反抗與逃避,縱使肉身的自我無法跳出社會的大染缸,為了獲得一份撫慰,靈魂的自我也會為肉身的自我守護一片純凈的天空。霍爾頓去哪兒都戴著他那頂鴨舌帽,特別是當他遭遇不好的事情時,他會特地找來那頂帽子,把它反著戴上,以此守護內(nèi)心世界真實的自我。他還特別關心中央公園南頭淺水湖里鴨子的命運,而這些享受自由的野鴨子正象征著霍爾頓對靈魂自我的關切;他對象征童真與純潔的艾利和菲比的惦念與喜愛,則體現(xiàn)了他夢寐以求的理想——成為“麥田”里的守望者,守護純真與善良。
霍爾頓連續(xù)換了好幾所學校,終究沒能成功在學校待下去,他厭惡學習卻愛憎分明,他憤世嫉俗卻渴望童真美好,他有著強烈的純真情結和隱逸傾向。霍爾頓經(jīng)常回憶他的童年時代,童年時代的一切都是純真無瑕的,他喜愛弟弟艾里,并不是因為他們有血緣關系,而是因為在他的心里艾里純潔無比,沒有受到世俗的污染,內(nèi)心充滿童真與善良,霍爾頓一直把艾里作為自己的精神陪伴,以至于他從沒感覺弟弟艾里真的死了。每當霍爾頓在現(xiàn)實世界中感覺到精神危機的時候,他就會向艾里求救,“每次我要穿過一條街,我就假裝跟我的弟弟艾里說話。我這樣跟他說:‘艾里,別讓我失蹤。艾里,別讓我失蹤。勞駕啦,艾里。’等到我走到街的對面,我發(fā)現(xiàn)自己并沒有失蹤,我就向他道謝”[3]。菲比妹妹聰明可愛,單純善良,也是霍爾頓對抗現(xiàn)實世界的精神屏障和精神力量。菲比妹妹身上有著兒童所有的美好品質(zhì)——善良天真,童真純潔。每當霍爾頓陷入精神危機的時候,他的腦海里就會出現(xiàn)菲比的形象,她是他貧乏世界的精神救贖,也是霍爾頓在污濁和黑暗現(xiàn)實中行走的一道光亮,菲比的形象指引他追求內(nèi)心世界的自己,給他前行的力量。當菲比妹妹問到他的夢想時,他不無欣喜地說要立志做一個麥田里的守望者,以拯救數(shù)以千計有可能跌下懸崖的無辜的孩子們。“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塊麥田里做游戲。幾千幾萬個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賬的懸崖邊,我的職務就是在那兒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奔來,我就把他捉住……我只想當個麥田里的守望者。”[4]在“人為物役”的現(xiàn)實中,霍爾頓的理想不是追求世俗成就,享受物質(zhì)占有的快樂,而是想脫離世俗,在一大片麥田里,在無數(shù)的麥垛旁,做一個麥田里的守望者,守護一大群孩子在麥田做游戲,他唯一的職責就是防止他們跌落懸崖,看起來是一種很幼稚可笑的理想,實則寓意豐富。“守望麥田”意味著保護孩子純潔美好的心靈,“跌落懸崖”則意味著孩子們失去了本真的特性,過早“成人化”。霍爾頓想去“守望麥田”是希望保護孩子純潔美好的心靈不被成人世界污染。顯然,在偽善、丑惡的社會里,這樣的夢想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保護孩子,不讓弱小純真的孩子過早體驗世俗世界的鉤心斗角、爾虞我詐,這種超現(xiàn)實主義的反抗行為最終只能走向失敗。于是,在行動的反抗和隱遁都失敗后,靈魂的自我選擇做一個“靜靜的守望者”,讓肉身的自我得以寬慰,以此保護無辜的孩子們,雖然只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但畢竟是他反抗現(xiàn)存社會價值,反抗這個被資本主義世界觀異化了的世界的靜態(tài)方式。對霍爾頓來說,在這種被金錢觀異化了的復雜世界里,能有這種田園牧歌似的純真精神向往與追求,不能不說是一種理想的替代性滿足。
三、“他者”的緣由——主流文化價值觀的失效與信仰的缺失
霍爾頓并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作惡者,相反,他有著純潔善良的心靈,反抗現(xiàn)實世界的一切道德行為規(guī)約,善良仁慈,然而在物質(zhì)化、機械化高度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他個人的精神理想?yún)s隕落了,孤獨、寂寞、迷惘猶如無法抗拒的寒潮席卷而來。面對安托利尼說的“一個不成熟的人的標志是他愿意為了某個理由而轟轟烈烈地死去,而一個成熟的人的標志是他愿意為了某個理由而謙恭地活下去”,霍爾頓的反應是“我不太想專心聽他講,我突然感到真他媽困”。他就是一個“不成熟”的人,為追求靈魂自由,在現(xiàn)代社會化的過程中被異化。“在異己力量的作用下,人類喪失了自我和本質(zhì),喪失了主體性,喪失了精神自由,喪失了人性,人變成非人,人格趨于分裂。”[5]霍爾頓便是被異己力量異化了的人,在現(xiàn)實社會中怎么也找不到歸屬感,總覺得在社會的大染缸里只有孩童的心靈世界才純真美好,更難能可貴的是,其人生的終極理想只是想當“麥田里的守望者”。“他者”霍爾頓這一人物形象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陰暗與復雜,表明人們在現(xiàn)實的生活中沒有幸福和快樂可言,這種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原因是復雜的,涉及當時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觀。
《麥田里的守望者》創(chuàng)作于二戰(zhàn)后不久,主人公霍爾頓的精神困惑并不是他一個人的困惑,而是代表著一個時代青年人的煩惱與迷惘,這自然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治領域爆發(fā)了一場“白色恐怖”運動,執(zhí)政者無視法律,采取各種非人手段控制左翼人群的思想,對他們進行政治迫害。身處政治高壓、經(jīng)濟卻快速發(fā)展的時期,大部分美國青年接受父輩的價值觀,努力讀書,追求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這種大眾文化價值觀卻在追求精神自由與純真美好的霍爾頓式青年身上失效了,因此這一代被稱為“沉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霍爾頓并不甘心沉淪在這個功利世界中,也不接受普遍意義上的價值觀,眾人皆沉溺于物質(zhì)而唯獨他追求精神,在這種背離中他最終走向精神的自我救贖,而這與當時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物欲橫流、窮奢極欲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
二戰(zhàn)后,美國資本主義制度高度發(fā)展,人們沉浸在物質(zhì)的窮奢極欲中,精神信仰卻無處可依,于是便出現(xiàn)了霍爾頓式的反抗與逃遁,個體渴望歸隱,最終卻被棄之于社會的邊緣,淪落成精神流浪兒、物質(zhì)反叛者。
《麥田里的守望者》算不上一部真正的“異化”小說,但通過霍爾頓這一典型形象反映出現(xiàn)代社會的物質(zhì)發(fā)達帶來的異己力量對人們心靈造成的沖擊,讓人產(chǎn)生無處可依的荒涼感,通過分析霍爾頓這一“他者”角色的現(xiàn)實處境和精神尋求,我們或多或少可以窺見作者對個體生命意識的觀照,對個體精神歷程的探尋。顯然作者此舉意在引起更多人關注個體生命成長,激發(fā)知識分子尋求積極的文化價值觀。
四、“他者”的啟示——競速時代靈肉和解的審美救贖
縱觀主人公霍爾頓的精神歷程,從被潘西中學開除到在街上游蕩的三天,讀者通過他的視角觀察到的一切,都表明他始終以一個不被世俗接納、不愿融入世俗的他者身份存在。被諸多學校開除,意味著他對當下生活采取逃遁姿態(tài),以此反抗學生生活。被開除后在大街上游蕩不回家,以免讓父母第一時間知道被開除的事情,意味著他對家庭的反叛;觀看一群孩子在麥田里打鬧,立志做一個“麥田里的守望者”,更是體現(xiàn)了他與“人為物役”的社會走向了終極的決裂。雖然霍爾頓的時代離我們已經(jīng)很遙遠,但霍爾頓式的精神困惑卻沒有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得到解決,相反,隨著信息化、高科技的發(fā)展,個體的精神需求很大程度上還是被消解在群體的物欲追逐中,以至于出現(xiàn)“科技的發(fā)展或許并不能讓人們感到越來越幸福”的悖論,而這也正是霍爾頓“他者”生存困境帶給人們的啟發(fā)與思考。
在主客“二元對立”的西方世界價值觀影響下,人們過于夸大人類的力量,過分追求對物質(zhì)世界的占有,并且追求高效率、高速度,盡可能實現(xiàn)單位時間利益最大化,這意味著競速時代的到來。身處競速時代,作為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我們不可能像霍爾頓一樣犧牲人的社會價值去成全自我的精神價值——雖然看似“逍遙”,滿足了個體的生命體驗,實則是個體社會價值的泯滅。當然,我們也不能為了追求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讓個體生命需求完全消解在功利意義的追逐中,而是應該在兩者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最終實現(xiàn)靈肉和解。
一方面,我們享受競速時代的便捷與高效,但也不應排斥競速時代帶來的快節(jié)奏、高強度的生活現(xiàn)狀,而應該與時代的巨輪保持同向前進,讓個體的自我在世俗的社會中找到價值感。霍爾頓在工業(yè)化的快速進程中游離于現(xiàn)實生活之外,雖然他心地善良,見解獨到,可作為社會的人,他茫然麻木、沒有目標、沒有理想,既不認同當時的“物欲的極大滿足即幸福”的價值觀,又沒能找到真正的精神皈依,以至于不由自主地走向“精神荒原”。這是霍爾頓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作為個體,我們應緊跟時代的風向標,理性“識勢”,用心“蓄勢”,智慧“乘勢”,爭做時代“造勢人”。
另一方面,身處競速時代,我們既不能像霍爾頓那樣完全脫離現(xiàn)實,追尋虛無的精神理想,也不能為了追求物欲而讓自己靈肉分離,陷入無邊的精神荒原。我們可以試著在高度發(fā)達的信息化時代,讓自己適應“更高、更快、更強”的生活節(jié)奏,同時通過各種休閑方式,讓內(nèi)心暫時從現(xiàn)實生活中抽離,以此保護內(nèi)心,最終實現(xiàn)靈肉和解的審美救贖。
參考文獻
[1] 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M].施咸榮,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2] 尚曉進.精神危機與自我救贖——試評《麥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M]//汪義群.英美文學研究論叢(第二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3] 張介明.永恒的奧秘:向往自然——《麥田里的守望者》再論[J].湘潭大學學報,2002(3).
[4] 呂威.塞林格“守望精神”中的東方生命哲學——紀念《麥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七十周年[J].當代外國文學,2021(4).
[5] 邱意濃.《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異化主題[J].文學教育,2022(7).
(特邀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