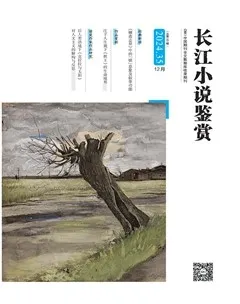麥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后現代崇高”
[摘" 要] 《星期六》是一部以“9·11”事件為背景的小說,表達了伊恩·麥克尤恩對個體生存狀況和英國社會困境的擔憂。作品描述了神經外科醫生貝羅安在恐怖主義籠罩的一天內遭遇的故事,展現了英國民眾面對動蕩不安的社會現狀時所表現的焦慮和不安。作家描寫并預言了恐怖主義事件,這是對不可言說的恐懼感的表達,體現了利奧塔崇高論中對不可呈現之物的呈現。在技術與理性操控下,人喪失了特性,崇高主體淪為“非人”狀態。作家寄希望于藝術,試圖拯救生活在恐懼中的人們。
[關鍵詞] 伊恩·麥克尤恩" 《星期六》" 后現代崇高" 恐懼
[中圖分類號] I1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35-0070-05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的《星期六》(Saturday,2005)是一部反映“后9·11”時代的文學作品。小說講述了神經外科醫生亨利·貝羅安在星期六這一天的不平凡經歷。當天清晨,貝羅安目睹了一架飛機著火,這立刻讓他想起了“9·11”恐怖襲擊。同一天,倫敦街頭爆發了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大型示威活動。駕車外出時,貝羅安不幸與街頭混混巴克斯特的車發生碰撞。為了逃離現場,貝羅安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羞辱了巴克斯特。這一舉動激怒了巴克斯特,導致他持刀闖入貝羅安家中,企圖對貝羅安的女兒黛茜施暴。最終,黛茜用一首詩歌感動了巴克斯特,化解了這場危機。《星期六》通過貝羅安的視角,展現了英國家庭在恐怖主義陰影下的生活狀態,揭示了英國民眾憂慮、恐懼與震驚交織的復雜情緒。
目前,國外學者已經探討了《星期六》作為一部“后9·11”小說的主題、敘事策略以及互文性①。中國學者結合文學倫理學批評,探討了小說中的倫理道德敘事和當代都市人面臨的生存困境②。學者但漢松指出,《星期六》反思了現代性中理性主義的極端發展造成的嚴重后果[1]。借助想象力和共情個體可以超越現實的局限,回到詩性的崇高境界。學術界對《星期六》中呈現的崇高情感還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以利奧塔的后現代崇高理論為依據,通過分析《星期六》中英國民眾在動蕩不安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下,人際的交往和人與社會之間的碰撞,旨在揭示小說呈現的后現代崇高。
一、后現代崇高話語
崇高(the Sublime)作為西方美學話語的重要概念,最早由朗吉努斯(Longinus)提出,強調其在文學中的修辭作用。伯克(Edmund Burke)的崇高論從人的生理和心理層面指出崇高的根源在于可怖性。主體面臨恐怖之物生出痛苦,又因與可怖之物有一段距離而產生快感。康德(Immanuel Kant)繼承并超越了伯克,強調主體對崇高感的把握。主體通過理性對抗恐怖之景,從而獲得超越恐懼的崇高感。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繼承和發展了伯克與康德的崇高理論。利奧塔在伯克崇高論中找到了崇高與主體心理感受的關系。他認為崇高來源于恐懼,懸置的恐懼因空虛、死亡的威脅減弱,狂喜便油然而生,這種崇高感令“心靈遭受‘驚奇’極大的震撼”[2]。對于康德,利奧塔否定其崇高論中理念的不可呈現性,強調崇高可以超越理性界限和表達極限,呈現不可表達之物:“我們無法呈現絕對之物,但是我們呈現‘有絕對之物’這件事。這就是一種‘否定的呈現’。”[2]崇高不僅是一種情感體驗,更體現了超越理性與表達限制的能力。主體體驗到那些無法用言語表達的事件,從而獲得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崇高經由朗吉努斯、伯克、康德和利奧塔的闡釋,逐漸從審美領域走向現代社會對人的心理關注,是“對主體生存體驗的感性維度的張開”[3]。利奧塔的崇高論是傳統崇高論的后現代轉向,同“顛覆性話語引發的身體感知、情感道德反應聯系起來”[4],捕捉了當代個體在理性與情感兩個方面對崇高事件發生瞬間的感受。
現代社會,崇高的語境發生了變化,令人畏懼的不再是自然界,而是危機四伏的世界局勢和資本化、技術化的社會。恐怖主義和無處不在的暴力彌漫在西方社會,恐懼感和焦慮感盤踞在集體和個體記憶深處,荒謬感浸透日常生活。崇高的主體不再是身心完整、具有偉大信仰的自由人,而是身處現代社會的個體,面臨著技術化、資本化社會的壓迫與威脅。
但是主體并非完全被恐怖壓制,而是展現出積極心理狀態或內在力量。“這是一種比古典傳統美學更深沉、更偉大的‘崇高’,一種面對絕望而永不放棄的‘崇高’精神。”[5]崇高是對現代人心理體驗的深刻反映,展現了人類在面對生存困境時所展現出的不屈精神與崇高情感。
二、創傷記憶喚起崇高感
創傷可以被視為一種崇高事件,“在很多方面,崇高乃是‘創傷’這一心理學概念在哲學上的對應物”[6]。小說對戰爭、游行和恐怖組織的描寫呈現了籠罩在陰影下的西方社會承受的創傷。這種歷史創傷是不可言說之物,承載著集體的記憶和歷史的烙印。它不僅僅是個人層面的傷痛,更是整個社會共同經歷的精神磨難。“9·11”事件給美國造成的打擊歷歷在目,英國人民也一直生活在恐怖與暴力的陰影中,擔憂隨時都有可能重現這樣的慘劇。當貝羅安凌晨醒來,目睹一架著火的飛機飛向機場,他立即聯想到恐怖主義襲擊,因為“飛機已不再是往日的形象,而是成為潛在的武器或是看起來在劫難逃”[7]。恐怖變成了生活常態,“大災難”“傷亡慘重”“生化武器戰爭”和“重大打擊”[7]等一系列描繪創傷經歷的詞匯逐漸從公共安全的范疇滲透到個體的生命體驗中。由于暴力和恐怖的本質難以完全呈現,主體只能依靠想象力去接近恐怖的客體,不斷趨近事件真相。貝羅安未曾親歷恐怖事件,但是目睹飛機事故拉近了他與恐怖事件之間的距離,誘發了長久以來被壓制的恐怖記憶。創傷記憶的恐怖程度超出語言表述范圍,超越理性的限度,為了盡可能呈現恐怖,貝羅安對飛機客艙可能發生的事件展開極度的想象,以此來消解恐怖的威脅。崇高就發生在對恐怖事件的暴力想象過程中,“想象無法表現客體。我們有世界(整體性)的理念,但無力證明這一理念”[8],這種崇高感挑戰了人的認知,令人痛苦之余感到驚喜。得知飛機安全降落機場,沒有人員受傷后,貝羅安感到十分欣慰。事后,貝羅安意識到自己竟然忽略了許多細節,誤認為飛機著火是因為恐怖襲擊。這一次事故令貝羅安認識到“純真的年代已隨風而逝。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是如此干凈,當時誰會料到今天的光景?時下連呼吸的空氣都今非昔比了”[7]。
“9·11”事件后,貝羅安一家對戰爭與恐怖主義的態度轉變,揭示了恐怖襲擊對個體心理和社會結構的深遠影響。這一歷史創傷不僅造成了不可言說的極端恐怖,更展現了人類在面對極端暴力時的復雜情感與道德反思。在貝羅安家庭內部,貝羅安和兒子西奧、女兒黛茜對戰爭和國際局勢持有不同的觀點。西奧認為這個世界糟糕透了,與其關注世界大事,不如“只關心自己的境遇”[7]。這是因為太多的災難故事已經在西奧心里造成了創傷,他對未來喪失信心,只能感到恐懼和不安。黛茜和貝羅安爭論伊拉克戰爭時,二人的態度截然相反。黛茜是堅定的反戰者,她厭惡戰爭,渴望和平。貝羅安起初對西方國家入侵伊拉克漠不關心,因為戰爭、暴力行徑不會立刻破壞他現在的生活。但是,貝羅安聽聞病人特勒伯教授在伊拉克被捕的遭遇,目睹暴力行為在教授身上留下的疤痕,貝羅安近距離地感受到戰爭和恐怖主義給個人造成的傷害。他的態度由冷漠轉變為支持英國出兵伊拉克。同時,貝羅安擔心出兵伊拉克會令本國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在貝羅安看來,聲勢浩大的反戰人士是一群沒有文化的社會底層人,他們的示威游行會令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下的暴力,這正是“現代恐怖主義最初的形式”[1]。
麥克尤恩將反戰人士的游行比作新形勢下英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并且預言了倫敦地鐵站恐怖事件。恐怖主義帶來的影響力無處不在,造成的恐懼感無法消解。恐懼本身就是創傷事件,因為其永遠未曾真正降臨,無法被掌握或消除[9]。以貝羅安為代表的白人中產階級擔憂無政府主義破壞他們現有的社會地位和生活,以穆斯林協會為代表的阿拉伯移民擔心英國同伊拉克交戰損害他們的權益。這兩大群體對伊拉克戰爭持有不同的態度,在某些觀點上甚至截然相反,這恰恰反映了暴力與恐怖事件所帶來的復雜性和不可通約性。這些無法直接呈現的恐怖,只能通過想象去盡力描繪,從而引發人們內心深處的焦慮與恐懼。麥克尤恩以寓言故事寫出了恐怖事件對民眾生活的影響,試圖呈現原本不可呈現的恐怖,讓人們發揮想象,極力去感受這種恐懼,體現了崇高的“開放的未完成性”[10],崇高感也正是從此而來。
三、崇高主體非人化
在現代資本和科技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技術與機械逐漸將人系統化、功能化,使個體成為資本主義機器中的一個齒輪。金錢和效率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人的存在被簡化為工作與消費,日常生活中所有不符合經濟效益的行為均被排除在外。崇高的主體由大寫的“人”轉變為功利至上、喪失人文精神的“非人”。
貝羅安是異化后的典型“非人”代表。他篤信科學,輕視文學,除了醫學和物理學的相關圖書,他對其他書毫無興趣。當女兒黛茜建議他閱讀文學時,他露出鄙夷的神色,因為“他自認為所目睹過的死亡、恐懼、勇氣和苦難已足以充實多部文學作品”[7]。作為一名堅定的實證主義者,貝羅安認為自然科學觀能解釋和把握一切現象。任何生理上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先進的醫學科技解決,手術的原理和“處理管道堵塞原理相同”[7],一旦安全通道打通,痛苦便消失了。在工作中,貝羅安充滿熱情,精湛的醫術令他有成就感。
然而,同巴克斯特的沖突徹底打破了貝羅安對科學萬能論的天真幻想。去打球的路上,貝羅安同巴克斯特的車發生剮蹭,他注意到巴克斯特不停顫抖的右手和面部異樣的抽動,當下確定巴克斯特患有亨廷頓舞蹈癥。為了成功逃脫,貝羅安利用了巴克斯特對疾病的羞辱感,“你父親有過這個病,現在你也染上了”[7]。當晚,貝羅安為此沾沾自喜時,巴克斯特闖入貝羅安家,意欲復仇。
貝羅安認為導致他和家人面臨恐怖威脅的主要原因是巴克斯特身體內“單純的分子變異和基因缺陷”[7],而非他對巴克斯特的侮辱。豐富的醫學臨床經驗和醫學知識儲備為貝羅安帶來了事業上的成功,但也剝離了他的情感體驗,使他缺乏同理心和人性關懷。在利奧塔看來這種理性主義主導下產生的“非人”是對大寫的“人”的標準化生產。它將人的特性抹殺,將其抽象化和標準化。人最終被異化為抽象的“非人”,失去了其本真的存在和意義。這次,醫學知識未能幫助貝羅安解除危機,反而導致了家庭成員被巴克斯特傷害。
巴克斯特對貝羅安的暴力行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利奧塔“非人”對抗“非人”的主張。巴克斯特代表的“非人”是被現代人文體系所排斥的、不被納入社會規范的個體。他們憑借非理性的情感,以一種原始的欲望去對抗那些非人性的、過于程序化和理性化的社會現象。貝羅安的“非人化”則是技術理性過度發展的后果,它剝離了人的情感,使人冷漠。這種“非人”之間的對抗使人焦慮和痛苦,但為人的存在提供了解放的空間,重新審視并放大了人性光輝,同時喚起了崇高感。小說尾聲,貝羅安在為巴克斯特進行手術的過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貝羅安感到平靜,心境開闊,充滿了實在的充實感。這是一種空靈的潔凈,深刻而沉默的愉悅感”[7]。這種愉悅之情,正是他心中“非人”力量抵抗“非人性”力量的結果。在這一刻,貝羅安心中喚起的同情心已經超越了他原本的理性思維系統,成為一種更高層次的感悟。
利奧塔的“非人”對抗“非人”理念,揭示了現代社會理性主義和資本主義體系下個體被異化的現象。他強調個體獨特性、情感豐富性和思想深度,反對將人簡化為一種抽象和標準化的存在。“非人”不僅是一種現代人的生存狀態,還是一種崇高的抗爭狀態。盡管伴隨著痛苦、不安與焦慮,這種崇高感卻促使個體深刻重新審視人的精神本質。
四、詩歌探尋人性之光
《星期六》描繪了英國在恐怖主義陰影籠罩下,隨時可能陷入戰爭的緊張氛圍以及民眾內心深處的焦慮與不安。麥克尤恩并沒有止步于揭露英國社會現狀,他回到詩歌,借用阿諾德的《多佛海灘》試圖拯救陷入黑暗的英國人民。與《多佛海灘》的創作背景相似,《星期六》同樣創作于英國和全球局勢發生重大轉折的歷史節點,社會內部的矛盾與緊張情緒暗流涌動。極端主義、氣候變化、政治糾紛、土地和淡水資源匱乏等問題交織,構成了一幅混亂而充滿危機的世界圖景。與此同時,科技的迅猛發展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與進步,卻也加劇人性異化的風險。個體的獨特性逐漸消解,被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所取代,人的生存意義變得模糊不清。這種變化加劇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疏離與矛盾,使整個社會結構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考驗。
小說中,詩歌阻止了巴克斯特進一步傷害貝羅安一家人。在巴克斯特和貝羅安對峙的緊張關頭,巴克斯特看到桌上的詩集,誤以為是戴茜的作品,并且要求她朗讀。巴克斯特聽到《多佛海灘》后,他想起童年的生活,陷入一種狂喜的情緒中,“從一個野蠻的恐怖主義分子瞬間轉變成一個驚喜的崇拜者,或者說一個興奮的孩子,如此巨大的轉化,他自己卻渾然不覺。他現在的表現就像個興奮的孩子”[7]。巴克斯特在詩歌的感召下,回憶起童年的碎片式記憶,體驗到懷舊的崇高。他看到戴茜孕育生命的肚子,那份母性的光輝仿佛化作了母親溫暖的懷抱,溫柔地撫慰著他那顆受傷的心靈。詩歌觸動了巴克斯特,最終拯救了貝羅安一家。
貝羅安聽到《多佛海灘》后,異樣的情緒也在他心底涌出。詩歌觸動他的聽覺和視覺,“他也覺得自己慢慢融入了詩文所描繪的那種境界。他仿佛看到戴茜在露臺上俯瞰著夏日月光下的海灘;漲潮過后的海面平穩如鏡,空氣中彌漫著一縷芳香,落日的余暉散發著最后的光芒”[7]。貝羅安不喜愛文學作品,推崇科學精神,卻受到詩歌的鼓舞,感受到詩歌喚起的悲傷和失落的情感,開始重新審視詩歌的價值。正是詩歌獨有的意象,“以它對生活的形象的闡釋,以及給予人們的安慰和支持,正可以替補信仰的空缺”[11],讓聽者聯想到海灘的潮水漲落,感受到世界的變動。詩歌啟發了貝羅安和巴克斯特兩個不同階級的個體,共同看到團結和愛可以慰藉焦慮的人。在沖突發生之前,貝羅安認為同情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即使你知道有眾多生命需要你去同情,但只有擺在你眼前的才真正困擾到你。所謂眼不見心不煩”[7]。但是小說結尾時,貝羅安寬恕了巴克斯特,為其做手術,并決定說服家人放棄起訴巴克斯特。作為醫生,貝羅安不僅在乎手術的成功,更意識到同情心和寬容的重要性。他深知“醫療體制的運作規則——好的護理和差的護理之間有著天壤之別”[7]。在面對生命與死亡的抉擇時,同情心與寬容同樣至關重要。
麥克尤恩肯定了藝術的感化力量,并試圖引導現代人從高壓的社會生活中解脫出來,用愛和關心緩解焦慮和恐懼,重燃對生活的熱情。現代工業發展雖帶來經濟繁榮與物質充裕,卻讓人內心難以滿足,人際關系變得冷漠。貝羅安夫婦便是典型例子,他們擁有體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但是二人因忙碌的生活缺乏最基本的交流,工作仿佛成了生活的全部,“每周通常是在星期日的晚上,他們會把各自的掌上電腦并排放在一起,像一對交配的動物,好讓他們的時間安排通過紅外線功能傳到彼此的記錄里”[7],夫妻關系因高強度的工作逐漸疏遠。父親和孩子也無法融入彼此的生活。女兒戴茜強烈推薦貝羅安閱讀文學作品,但是他拒絕文學,毫不掩飾對文學的不屑,甚至難以理解女兒對詩歌的喜愛。兒子西奧演奏的藍調音樂和貝羅安常聽的古典音樂曲風大相徑庭,前者注重變換的旋律,演奏中即興發揮,后者則遵循固定的音調和格律,一切有規可循,就像貝羅安的生活,程序化,講求精準。家庭成員互不理解,不認同彼此的生活,每個人都是孤單的。
《多佛海灘》中,當信仰的潮水退去,只剩下無邊無際的黑暗和憂傷的哀嘆。麥克尤恩引入詩歌并不是要詩歌充當改變人的工具,而是希望人們受到詩歌啟發,擁有一種緩慢前進的勇氣和信心,面對動蕩不安的社會局勢,仍然不失信心,相信彼此間的愛能幫助人們找到平靜充裕的內心世界。
五、結語
《星期六》是一部深入剖析現代人生存境遇的杰作,以主人公貝羅安的視角為線索,細致入微地刻畫了籠罩在恐怖主義陰影下的英國民眾日常生活。戰爭、暴力和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如影隨形,它們不僅撕裂了社會的和諧,更在無形中侵蝕著人性的底線。小說世界呈現了信仰崩潰、人性喪失的荒誕景象。外在戰亂與暴力,內在迷茫與空虛,共同構筑這一荒誕現實。人們迷失在混亂與不確定中,人性悄然流失,人際關系疏離冷漠。后現代崇高感在這樣的背景下悄然滋生,它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對崇高事物的敬仰和追求,而是一種對生命意義的深刻質疑和對人性的絕望反思。麥克尤恩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忠實地呈現了后現代個體的真實情感。他試圖通過文學的力量,喚起人們內心深處的共情和關懷,借助愛和關心幫助人們抵擋后現代精神危機對個體的折磨。
注釋
① 相關論述分別見以下文獻:Hadley E.On a Darkling Plain:Victorian Liberalism and the Fantasy of Agency[J].Victorian Studies,2005,48(1);Wallace E K.Postcolonial Melancholia in Ian McEwan’s Saturday[J].Studies in the Novel,2007,39(4);Ross M L.On a Darkling Planet:Ian McEwan’s Saturday and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J].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2008,54(1).
② 相關論述分別見以下文獻:宋艷芳.小說何為?——從麥克尤恩的《星期六》看小說的功能[J].國外文學,2013(3);尚必武.重訪“斯諾命題”:論麥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兩種文化[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3(2);曲濤,孟健.解讀后“9·11”小說中的道德敘事——評伊恩·麥克尤恩小說《星期六》[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3(5).
參考文獻
[1] 但漢松.論麥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后9·11”式崇高[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
[2]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時間漫談[M].夏小燕,譯.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3] 余沉.當代崇高的“復興”與利奧塔的后現代崇高[J].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1(4).
[4] Johnson D B.The Postmodern Sublime[M]//Costelloe T M. The Sublime: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5] 張奎志,張丹.從審美到人生:崇高的失落與當代書寫[J].學習與探索,2020(10).
[6] Ankersmit F R.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7] 麥克尤恩.星期六[M].夏欣茁,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8]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M].島子,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
[9] Redfield M.The Rhetoric of Terror:Reflections on 9/11 and the War on Terror[M].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9.
[10] 陳榕.西方文論關鍵詞:崇高[J].外國文學,2016(6).
[11]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 夏"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