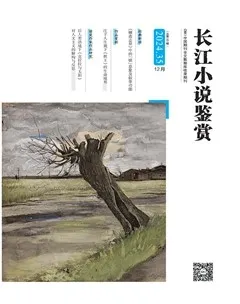他鄉書寫的非虛構敘事
[摘" 要] 非虛構文學作品以非虛構的敘事方式來保證真實性,并在敘述中融入文學的意蘊和情懷,強調作者的在場性,在有限的敘事空間內升華主題。非虛構敘事逐漸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羅偉章將“非虛構寫作”運用到對他鄉的書寫之中,創作出令讀者喜愛的脫貧攻堅紀實文學。涼山作為具有民族融合特點的典型地理區域,引發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其中,《涼山敘事》聚焦于脫貧攻堅時期的涼山昭覺,采用紀實性的敘事策略來最大限度地展現昭覺脫貧攻堅的艱辛歷程和巨大成就,并運用了獨特的敘述視角,以此產生陌生化的敘事效果,給讀者帶來真切的感受。
[關鍵詞] 他鄉" 非虛構敘事" 陌生化
[中圖分類號] I207.5"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35-0095-04
作為一部以學者做研究為敘事角度書寫涼山昭覺脫貧攻堅的非虛構文學作品,《涼山敘事》比我們熟知的非虛構研究文本多了陌生化敘事的內容。它將敘事技巧與脫貧攻堅的真實歷史相融合,呈現了羅偉章對涼山昭覺的深思,也將近幾年興起的非虛構寫作進行了延伸。他鄉書寫中的非虛構敘事使作品帶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在場感,并且使讀者會不由自主地觀照自己的故鄉,羅偉章的非虛構作品能夠很好地展現其對脫貧攻堅的關注,原因在于他采用非虛構的方式,呈現出時代巨變和政策扶持下貧困地區的顯著變化。“非虛構文學”這一概念最初誕生于20世紀美國,近些年來逐漸成為我國文學的主要形態之一。但早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史傳中,就已有著“非虛構”的影子存在。眾多史傳以史實為基礎,在記錄歷史的同時也會注重藝術的加工。五四時期出現的報告文學也是我國非虛構文學的前身,它以新聞紀實的方式書寫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跡,已經初步具備了非虛構敘事的特征。非虛構敘事作為當代敘事學的前沿課題之一,其形式比虛構文學更為多樣,敘事結構也更加繁雜[1]。
一、他鄉書寫中非虛構敘事的內容
1.新舊碰撞下的他鄉傳統文化
《涼山敘事》作為一部以脫貧攻堅為主題的非虛構作品,其中對于涼山的實景描繪是具有一定問題意識的。從作品中可以看出,在政策扶持和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下,昭覺的住房條件等基礎設施有了很大改善,但當地彝族人內心也經歷過陣痛。作品第二章第二節中,羅偉章專門談到了彝族傳統文化的消極面與積極面。作品中提到,著名彝族詩人吉狄馬加十分憂心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流失,羅偉章在晚會中也觀察到,彝族老歌遠沒有流行歌曲受歡迎。或許在彝族人心中,面對本民族傳統文化面臨的傳承挑戰,他們感到的是不舍與心痛。《涼山敘事》里提到的“鍋莊”就是在脫貧攻堅進程中逐漸消失的傳統象征物。對于彝族人而言,“火”在精神層面和現實層面都是不可或缺的,“火把節”就足以說明彝族人對火的崇拜歷史有多么久遠。然而,在現代人看來,鍋莊的存在似乎等同于落后,因為鍋莊意味著煙熏火燎,而鍋莊被取代則意味著干凈整潔,但同時也意味著沒有了火塘,無法再像以前一樣在家里烤火。人們需要去尋找傳統文化在新舊碰撞下的平衡與合理性。羅偉章客觀現實地給讀者講述了脫貧攻堅所帶來的“新”,也以冷靜的態度分析了改變“舊”中所遇到的困難。
對于幫扶干部們來說,最大的苦惱可能在于新舊碰撞下如何改變彝族人的固有思維。在幫扶干部們的幫助下,昭覺的彝族人住上了新房子,也新建了廁所。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彝族人的傳統居住方式是人畜混居,他們不會在家里修建廁所,大小便都是在大自然的環境中解決。他們剛住進新房子時,原有的思維還沒有改變,有的村民依舊在野地里解決。這是因為涼山是從奴隸社會直接跨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導致許多彝族人的思想觀念依舊停留在過去,無法迅速適應新時代。《涼山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為脫貧攻堅、改變落后思想而努力的不僅是扶貧干部們,許多彝族人也在進行自我調整,從本土彝族作家馮良、阿蕾等人的作品中,我們也能夠感受到他們對本民族問題的反思以及對民族未來發展的展望。
2.外地幫扶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共同努力
從《涼山敘事》中的非虛構敘事內容來看,對于昭覺的脫貧攻堅工作,外地幫扶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作品的第三章更是直接以“遍地英雄”來命名。羅偉章在敘事中以第一人稱的口吻介紹這幾位為昭覺脫貧攻堅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物,具有明顯的在場感,使敘事內容更加真實可信。這些干部們就像螢火蟲一樣,以微弱的光芒匯聚照亮前路,用土辦法和洋辦法相結合的方式來幫助昭覺。他們的付出對于昭覺、對于涼山而言,都是十分寶貴的。徐振宇是羅偉章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的人物,他扎根在涼山昭覺,在那里幫助彝族人移風易俗,推進脫貧攻堅。涼山在大多數人眼中分為大涼山和小涼山,但其實本地人更喜歡稱之為老涼山和新涼山。大涼山,也就是老涼山,是指昭覺、布拖等有著濃厚彝族傳統文化的地方,新涼山則是跟漢族文化融合更多的幾個城市。昭覺作為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縣,有著“彝族文化走廊”之稱,卻是涼山的深度貧困地區。
就像羅偉章在作品中所說的,扶貧干部們在昭覺除了扶貧,還在扶志和扶智[2]。彝族是一個十分注重家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組織)的民族,同時也十分注重“面子”。這種要面子的心理,間接使得一些“懶漢”貧困戶就算什么都懶得做,也不會承認自己缺乏脫貧的志氣。扶貧干部們摸準了這條路子,想出了“以購代捐”[2]的方法,讓貧困戶中的“懶漢”也行動起來,爭著比誰干得更好。《涼山敘事》中對于“扶智”的敘事書寫,更像是將讀者帶入那個場景中,讓人看得熱血沸騰,也想出一份力。扶貧干部們在扶貧時,并不是只做表面功夫,而是真心實意地為昭覺著想,引進了許多新產業和新技術,旨在授人以漁而不是授人以魚。除了外地的幫扶干部外,羅偉章對本地干部的描寫也深入人心。比如,連彝族年都沒有休息,依舊堅守崗位的拉格書記;無法照顧家人的宣傳部副部長阿克鳩射;退居二線后又深入脫貧攻堅第一線的吉夫格博等人[2]。字里行間可以看出,羅偉章真真切切地到過昭覺,接觸過這些脫貧攻堅的干部,深入了解過昭覺的脫貧攻堅工作,這也是這部非虛構作品敘事內容給讀者帶來的真實感。
二、他鄉書寫中非虛構敘事的策略
1.獨特的敘述視角
羅偉章在《涼山敘事》的開篇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不認識這個民族,我的書寫將毫無意義。”[2]由此可以看出,羅偉章是作為外人來到涼山昭覺的,但他在深入了解這個民族后,用在地化的書寫向讀者展現了漢族人眼中的彝族。整部作品以書信的方式構建結構,拉近了敘述者和讀者的距離。外部視角的運用其實在羅偉章的另一部非虛構作品《下莊村的道路》中也有所體現,都是作者以親歷者的視角,融入他鄉后的在地化書寫,使讀者感覺《涼山敘事》仿佛就是涼山人的自我表述。這是因為羅偉章以獨特的敘述視角,帶有問題意識地將昭覺的真實情況向讀者進行呈現。外部敘事視角的運用,打破了非虛構敘事原有的返鄉書寫的寫作模式,使作品具有一種陌生化效果。雖然是運用第一人稱敘事,但作者并未完全由全知視角掌控敘事內容,而是以“我”和眾多扶貧干部的在場講述來改變敘事的聚焦狀態。
面對他鄉,羅偉章理應感到陌生,但他卻以“涼山人”的口吻給“朋友”講述這里的扶貧攻堅故事,拋去傳統的旁觀視角后,他以反思者的角色融入昭覺當地進行在地化書寫,用細膩的文字勾勒出涼山彝族人生活環境和生活習慣的變化。在開篇介紹昭覺時,羅偉章用全知視角交代了涼山昭覺的位置以及涼山“一步跨千年”的歷史等背景,但他還是在開篇寫道:“單說涼山,無法理解真正的涼山。”[2]作為外人,要認識另一個相對意義上的他鄉,不能只從自我視角的表象下結論,而是要在深入并融入他鄉,透過表象去探尋本質,這是羅偉章用心良苦的敘事策略[3]。
2.多樣性的敘事文體
童慶炳在《文體與文體創造》中提出:“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歷史、文化精神。”[4]羅偉章在書寫《涼山敘事》時,將多種文體融入作品中,既有他自己經歷的田野調查,也有扶貧干部的口述實錄,還有涼山的相關史料。多種文體的雜糅運用,是為了更加真實地將昭覺呈現給讀者。
羅偉章用自己的足跡走遍涼山昭覺,用自己的行動書寫這片土地上的脫貧攻堅故事,充滿在場感的書寫建立在羅偉章漫長的田野調查基礎之上。史料的借用可以更好地體現文本的真實性,因為史料是時代變遷的縮影。《涼山敘事》的很多章節都摘錄了有關涼山彝族的史料,如涼山彝族的精神信仰、彝族發展的歷史、彝族的獨特文化等。這些史料為昭覺的貧困背景提供了參照,通過非虛構敘事呈現昭覺在歷史變遷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探討脫貧攻堅中遇到的困難,展望涼山彝族人的未來。口述實錄則一般通過采訪對話的方式呈現,因為口述實錄的對象是涼山脫貧攻堅的真實經歷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作者的主觀意志,更加具有真實性。
多種文體交叉敘事的手法,一方面真實記錄了羅偉章在昭覺的所見所聞,另一方面正是基于有了史料和口述的佐證,消解了外界對于涼山的刻板印象。為了避免《涼山敘事》過于主觀化,羅偉章多次在作品中警醒并審視自己對于彝族的書寫,從羅偉章列舉的眾多史料故事中,讀者能夠清晰了解到彝族人崇拜火的原因、彝族人居住高山的原因等,并由此看到這些傳統在時代巨變下所面臨的問題,引發讀者的深思。羅偉章在作品中談及彝族舊住房中的火塘等古老傳統時,總是保持中立態度,通過引用彝族古籍史料,再從客觀角度提出這些自古以來的傳統面對現代性的沖突,借助多種文體的交叉敘事來達到書寫真實、客觀的目的。
三、他鄉書寫中非虛構敘事的意義
1.在場性的自覺
非虛構作品自興起以來,一直都以真實性作為敘事策略,很多作者旨在書寫時代變遷下自己家鄉的種種變化,并帶有一定的問題意識。相較于梁鴻的“梁莊三部曲”、黃燈的《在大地上的親人》、賀雪峰的《回鄉記》等返鄉書寫的非虛構文學作品,羅偉章的《涼山敘事》作為一部書寫他鄉的非虛構文學作品,更需要強調文學的“在場性”。在場性通常是指作家的在場精神,在非虛構創作中,它成為文學寫作者的自覺意識、社會責任和時代使命。羅偉章想要給讀者呈現一個真實的涼山,就必須用包容的眼光去了解涼山,從更深層次出發,以平等的態度書寫涼山。作家自覺地觀照鄉村,進行在場寫作,是因為非虛構文學作品的創作都需要親歷,這種在場親歷并不僅僅指作家通過抒情等藝術手法來展現,而是指作家要親自參與現實,通過感知和深思進行創作。為了達到非虛構作品的真實性,《涼山敘事》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都是真實存在的。如果羅偉章沒有在場性的自覺,就不會了解涼山昭覺的一草一木,也不會聽到阿皮幾體、徐振宇等人的口述,更不會知曉“畢摩”對于涼山彝族人的意義。非虛構書寫并不像新聞那樣簡單地將事實進行呈現,它還包含了作者的藝術加工,羅偉章的《涼山敘事》打破了主流話語與彝族地方性知識之間的壁壘[5]。
羅偉章以給“朋友”寫信為原點,每一次寫信向“朋友”講述在涼山的一點一滴,最終這些點滴匯聚成了涼山脫貧攻堅歷程的輪廓,同時也構建了一個由羅偉章、扶貧攻堅干部、涼山本地人共同組成的人際關系網。作為一個外來人員,羅偉章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他通過自己的筆墨書寫出中國眾多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縮影。為了保證紀實性作品的真實性,羅偉章很多時候是運用有限的個人視角進行書寫,將真實的個人體驗傳遞給讀者,讓讀者自主思考。從一開始對涼山人歷史、習慣等細致入微的客觀講述,到作者與扶貧干部之間的真實對話,是外部視角從陌生到熟悉的過渡[3]。
2.觀照現實的新途徑
《涼山敘事》中,羅偉章運用跨學科理論,結合田野調查等方法將多方面的問題融入敘事之中,給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些素材經過藝術加工最終形成了這部作品。《涼山敘事》中,無論是史料還是個人口述,都被用來觀照現實。涼山作為一個資源豐富但整體貧困的地區,“移風易俗”成為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正是因為舊風舊俗的影響,外界對涼山一直存在偏見和誤解,羅偉章的《涼山敘事》以客觀的視角向外界展示了涼山彝族的實際情況,使讀者能夠更真實地了解涼山。在傳統虛構文學難以全面表達當代人民真實生活的同時,讀者對真實性的渴望日益增加,非虛構敘事通過文本與讀者建立聯系,傳達對社會現實的關懷[6]。
羅偉章選擇涼山昭覺作為寫作樣本,從彝族的神秘歷史和時代進程中的真實現狀出發,帶領讀者共同展望脫貧攻堅的未來。在多媒體時代,信息傳遞方式的多樣化使得真假信息對接收者產生了影響。《涼山敘事》采用非虛構敘事手法,向讀者展示了昭覺脫貧攻堅的真實狀態,避免了刻意的煽情和虛構,而是用寫信的方式引導讀者進入敘事現場,使讀者能夠真切地體驗涼山脫貧攻堅的現實情境。昭覺的脫貧攻堅歷程是中國許多農村脫貧攻堅的真實寫照,涼山彝族人的形象也得到了深刻反映。羅偉章沒有簡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從史料出發,追根溯源,向讀者揭示了涼山彝族人需要脫貧攻堅的原因。正是有了如阿克鳩射的《懸崖村》、羅偉章的《涼山敘事》、何萬敏的《涼山紀》等非虛構作品,現實才得以被讀者更好地觀照和理解。
參考文獻
[1] 張衛東.論非虛構文學的敘事學問題[J].國外文學,2021(2).
[2] 羅偉章.涼山敘事[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2.
[3] 阿牛木支.在地化書寫、地方性知識建構和理性思考——《涼山敘事》讀札[J].阿來研究,2023(1).
[4] 童慶炳.文體與文體創造[M].昆明:云南出版社,1999.
[5] 邱婧.文學民族志實踐下的新時代報告文學——以《涼山敘事》為中心[J].阿來研究,2023(1).
[6] 孫策.近十年“返鄉書寫”中的非虛構敘事研究——以梁鴻、喬葉、黃燈為中心[D].荊州:長江大學,2023.
[7] 陳思廣.直面涼山生活的思與詩——羅偉章非虛構文學《涼山敘事》小析[J].阿來研究,2023(1).
(責任編輯" 余"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