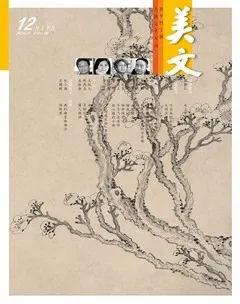南國植物標本往事
一
深秋的羊城,已能真切地感知秋風的蒞臨,華南植物研究所內,依舊滿園蒼翠,草木葳蕤,筆直的棕櫚樹一字排列大道兩邊,唯有池邊的落羽杉開始有了一點變色的跡象,再過幾場秋風秋雨,它們葉子的顏色將一點點變黃,繼而黃紅,再到棕紅,最終歸于大地。海南黃花梨、落羽杉、假檳榔、觀光木、瓊棕等珍貴植物隨性地散落研究所內。這是濃縮版的華南國家植物園,卻少了游人的喧囂,多了一份安寧清幽的學術氣息,與幾許生活的煙火氣。
轉過樹叢,一棟灰色墻體鑲嵌著藍色玻璃的四層建筑赫然入眼,門前水池旁,綠植掩映著“標本館”三個深紅色的字體,字不大,卻有一種天然的莊重感。相視的瞬間,風流云轉,因緣際會,往事雨打風吹,人影浮動眼前,感嘆世事總是這樣的勾連錯節,多少人與事都被掃入歷史的褶皺處,能被打撈的,終究是吉光片羽,更多的永遠沉寂在歲月深處。歷史就像一把篩子,過濾了曾經的大多數,過濾了具體的悲歡離合,只留下寥寥數語。標本館內,在這個注定被講述的季節,在親歷者的記憶中,依然能夠感受那些滾燙的際遇,跳動的脈搏,鮮活的人生,觸摸那些為了中國植物標本事業而曾經有過的,令人激動或悲傷的靈魂。
標本,是植物研究的基礎,也是靈魂。它是靜止的時間,凝固的歷史,也是沉默的訴說者。從繁華的枝頭落下,從遠古的歲月走來,主動或被動地封閉呼吸的閥門,收斂生命的氣息,讓水分回歸風中,讓細胞變得干涸。然而,干枯的枝葉花朵亦會說話,一如斑駁的石像依然能夠傳遞千年前的語言,沉入地底的化石可以清晰講述地球演化的密碼。標本將生命的氣息附著在葉脈上,將進化的規則刻在種子里,將繁衍的秘密藏在花蕊中,伴隨歲月一起寂靜在歷史的塵埃中,等待一道光將它們的記憶重新開啟。
仿若一個靜止的植物界,一個沉默的植物星球,泛黃的紙張,干枯的花葉,密密麻麻的標注,讓人不覺步履凝重,心神肅靜。那些曾經生動地在枝頭搖曳的花葉,銀杉、任豆、觀光木、大果木蓮、華蓋木、落羽杉;那些曾經穿梭在崇山峻嶺采集標本的前人,陳煥鏞、張肇騫、陳封懷、陳少卿、鄧世緯、何椿年、侯寬昭、賈良智、蔣英、劉玉壺,一一向我走來。
1928年,華南國家植物園創始人、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院士創建了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室,設立標本室;后改隸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2003年始用現名: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標本館。這是國內最早的植物標本館之一,也是華南最大的植物標本館,館藏熱帶亞熱帶植物標本超過115萬份。其中,最古老的標本,是采集于1808年的禾本科剪股穎屬植物,至今已有200多年,而收藏最早的本土植物標本,則是1872年采集于廣州的豆科植物短萼儀花。此外還有陳煥鏞發現的“活化石”銀杉,以及“紅木”原樹種花梨木等物種的模式標本。
華南植物園標本館的歷史,是中國植物學研究走過的百年風雨路。
二
時間的指針回到1919年,這一年,對于中國歷史具有分水嶺的意義,它將中國帶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而陳煥鏞帶來的,也將是全新的事物。
彼時,剛從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碩士畢業的陳煥鏞,在導師的建議和幫助下,踏上了前往海南島的標本采集之行。海南,這顆鑲嵌在中國南海邊的綠色明珠,是中國植物標本采集的空白地。“此前尚未有人深入調查其植物資源,采集結果可對東南亞地區植物分布有進一步了解,極具學術意義。”導師的話,海南島三個字,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撞擊著陳煥鏞的心,令他無比著迷。但世間萬物總是這樣,越是迷人,越是充滿未知的危險,此前,就有一名英國鳥類學家死在五指山附近,危險程度可見一斑。然而,陳煥鏞還是“憑著年輕人的全部蠻勇,單人匹馬出發了”。
茫茫海洋,波瀾壯闊,再次踏上遠航之路,陳煥鏞已不是當年那個遠渡重洋赴美求學的懵懂少年,他的眼神清澈而堅定,他的心中激蕩著回到中國開創植物學研究的赤誠熱血,他的心中懷著科技報國的遠大志向。
遙想當年,蘇軾被貶海南儋州,寫下“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此時,熱愛文學的陳煥鏞,不知是否也想到了蘇東坡在海南歷經艱難險阻卻九死不悔的決心。雖然800多年過去,此時的海南島仍未大規模開發,依然是瘴氣彌漫、現代文明之光尚未照耀的化外之地。在此之前,從未有植物學家上島,更不用說采集研究了,因此島上仍保持著原始的神秘狀態,這也是阿諾德樹木園的主任推薦陳煥鏞去的原因,沒有一個地方比海南更適合作為中國植物標本采集、植物研究的起點。
至今留存下來的陳煥鏞的眾多照片中,最具代表性和標識性的一張,就是在海南進行首次野外調查與采集時候拍攝的。照片中的他,頭戴遮陽帽,身著長襯衫、燈芯絨長褲,打著領帶,綁腿長靴,叼著煙斗,目視前方,身姿挺拔,氣度凌云,頗有美國西部牛仔的風格。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骕稱之為“攀登五指山極峰之第一人”。
陳煥鏞是公認的中國第一位到海南島進行植物標本采集的植物學家,開創了海南島采集標本的先河,這一年,他29歲。他的第一站是儋縣那大的沙煲山,即如今的儋州市,然而,他低估了海南環境的惡劣程度。交通不便、生活艱苦,這些他都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卻不曾想到會被毒蜂蜇傷,禍不單行的他又感染了瘧疾,最終被人用擔架抬出五指山。他不得不放棄原來的采集計劃,離島前往上海治療,并將采集之標本存放于上海招商局碼頭,不料碼頭大火,所有標本付之一炬。海南之行折戟沉沙,所得標本盡數毀于火災,這一度讓他感到消沉,但他沒有放棄這座神秘的海島,植物的天堂,后來依然多次派遣團隊赴海南采集,為編寫《海南植物志》打下基礎。
病愈后,陳煥鏞受邀到南京金陵大學執教,任農科森林系主任。在金陵大學時,他們便組建了一支以錢崇澍為隊長,陳煥鏞、秦仁昌、黃宗為隊員的鄂西植物調查隊,赴湖北采集標本。他們從宜昌出發,經由興山縣、神農架東側到達巴東,最高點到達海拔3000米的地方。錢崇澍專門采集草本,陳煥鏞采集木本,秦仁昌、黃宗充當助手,此行共采得標本近千號。多年后,秦仁昌回憶此次采集曾提到,1922年,他和錢崇澍、陳煥鏞一起赴湖北采集標本,需要600元路費,最終校方只設法湊到了500元,回來時他們已經身無分文,后來見到英國輪船,就連人帶標本往上爬,經過陳煥鏞與船長交涉說情,才回了家。而此行更大的意義在于,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大規模的采集隊”。然而,不幸的是最完整的一份標本,又再次毀于大火。似乎中國早期的標本采集,總是伴著火光和遺憾。
陳煥鏞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之后,為拓展植物研究,繼續赴廣州、香港、粵北、廣西、貴州等地采集標本,并與數十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取得聯系,建立標本交換關系,先后交換標本3萬余份,有力豐富了中山大學植物標本的數量。
除了交換標本,還與國外植物園交換種子。龍洞琪林亭亭玉立的落羽杉,便是這個時期與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交換而來,如今已遍布中華大地,成為一抹動人的風景。
三
陳煥鏞始終認為,“處于北回歸線以南的兩廣地區的植物種類十分豐富,在該地設立以植物分類學為主的植物研究所非常必要”。正是在植物采集基礎上,他提出設立植物研究室,邁出了創立華南植物研究所的第一步。
1928年,羊城的秋天比往年來得更早一些。為了開展對廣東省的植物分布調查和研究,同時改良及發展全省的經濟作物,陳煥鏞創辦植物研究室。經過一年多的發展,研究所各項圖書儀器等設備漸漸充盈,研究事業也蒸蒸日上,便函請校長將植物研究室改組為“植物研究所”。翌年冬天,植物研究所正式成立,所址設在廣州東山石馬崗的中山大學農學院內,僅有一間辦公室和一間標本室,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就這樣艱難起步。1930年4月,又在植物研究所前加上“農林”二字,隸屬于中山大學農學院,同時設立標本室、圖書室、采集隊、植物標本園和實驗室。
“生物研究,最重要的是標本。”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就明確了“本所之所立,以調查廣東植物種類為首要任務,并對采集任務作出全面規劃”,同時制定了采集計劃。此后,一代代植物工作者前赴后繼,以舍己忘我的精神,走遍中國乃至國外的深山密林采集標本,支撐起國內第一本地方植物志《廣州植物志》和第一本樹木志的編研。同時也支撐了《海南植物志》《廣東植物志》《香港植物志》等30多部植物志的出版,還為《中國植物志》的編撰出版提供支持,而這部植物志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從植物采集到標本的制作,最后進入標本館,有一套嚴密的流程。曾經從事過這一工作的何椿年回憶道:“我過去在植物所工作,是在標本室內整理標本,查閱英美等國出版的雜志,檢出提及我所標本室某號標本,一方面將該雜志對該標本的敘述,用打字機打出來,貼在該標本上,以供參考;同時,還要用小標簽,說明該標本室在某雜志幾卷幾期幾頁提過,以為這樣便可以加強某標本的確定性,增加該標本的價值。”
陳煥鏞不僅親自帶頭采集、鑒定標本,同時建立了三套完善的卡片系統,可根據植物的名稱、采集人、標本號、地區分布等,從三套卡片系統中迅速查到所需的標本。即使后來標本館實現了電子計算機管理標本,基礎依然是陳煥鏞制定的管理方法。
望著日益壯大的標本館,陳煥鏞心中的藍圖在一點點實現。他說:“本所成立迄今,雖為期五年,而所藏標本已超過6萬號,固不敢與國外著名植物園具有百數十年相為媲美,然以視國內各植物標本室,實未遑多讓……”
四
此后,隨著時局的變化及抗戰的深入,農林植物研究所也開啟了會址變遷與更名之路。先是國立中山大學新校舍在廣州石牌落成,中山大學遷入新校址,后農林植物研究所遷到法政路,同時在位于石牌的中大校園內開辟標本園,從事植物的引種栽培工作。
1937年7月7日,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此后,長達十數年的戰亂不僅將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拖入戰爭的泥淖,也沉重打擊了剛剛興起的中國植物學研究事業。
戰火起于北平,很快燒過平津,燒過滬寧,繼續向著南中國蔓延開來。日軍鐵蹄所到之處,天地變色,生靈涂炭,無數珍藏在各個研究所,植物學家費盡心血采集的植物標本在戰火中毀于一旦。位于北京的靜生生物調查所首當其沖,盧溝橋事變爆發時,靜生生物調查所尚未做好撤離的準備;滬寧戰役打響前,位于南京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匆忙撤離,然而缺少充足準備,只能將主要物品運走,大量標本落入日軍之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更是被日軍焚毀,多少心血、成果與希望,毀于一旦。
至此,早期由國人創立的生物學研究機構幾乎盡數遭毀,唯余南方的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一家。保護研究所,成為陳煥鏞重如生命的使命與責任,它是中國植物學研究的希望所在。
戰火燒到偏安南方的廣州。1938年,這一年對于廣州來說,注定被銘記。昔日繁華安定的廣州城淪陷,人們紛紛逃難,大量機構外遷,農林植物研究所珍藏的15萬份標本、4000多冊中外圖書文獻及各種儀器設備亦遭受嚴峻威脅。
早在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中山大學便開始準備撤離,然而,由于學校龐大,行動緩慢,陳煥鏞無法等待學校安排撤離,便自籌費用,分批將重要物品轉移至香港九龍。即便如此,也還是未能將全部物品盡數轉移。未能及時轉移之物品和房產,則留下人員看管。陳少卿留守石牌校園標本園,李耀、歐陽有群夫婦留守法政路所址。那時法政路仍留有“標本柜60個,還有泡花柜、辦公臺、公文柜等;復份植物標本30萬份、中山大學生物系植物標本2萬張、圖書儀器10箱”。這批物品在被日偽政權接管之前,陳煥鏞又想方設法轉移一部分至香港,并建造一座三層建筑,用以存放從中山大學轉移出來的物品、標本,亦是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香港辦事處。
遷港期間,植物研究所繼續從事標本鑒定、專科專屬研究及人才培養等工作,同時繼續出版《中山專刊》。期間,招收研究生何椿年,跟隨陳煥鏞從事榕屬植物研究,后來何椿年參與主持華南植物園的籌建工作,成為華南植物園的開拓者之一,為植物園早期發展作出開創性貢獻。
與此同時,中山大學遷至云南澄江,在戰火中繼續開展教育工作。蔣英、侯寬昭、李仲洛等一批研究所員工隨校遷移,在云南開展植物研究工作,并在昆明城郊設立經濟植物圃和藥用植物圃。而后,中山大學遷往粵北坪石,農學院設在距離坪石30公里的湖南省宜章縣栗源堡,植物研究所也隨著遷到栗源堡。蔣英等人隨著前往,并在栗源堡重新組建研究所,租用民房,“致力于廣東、湖南交界之植物調查與采集”“勘察湘江支流上游及兩廣邊境森林,為修建湘桂、粵漢兩條鐵路所需枕木、電線桿之用材等”。同時到莽山、衡山等地開展植物標本采集、鑒定工作,并開始對湖南進行大規模系統的采集,撰寫相關工作報告,編撰《栗源堡植物志》,并計劃重建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室。
即使流寓粵北湘南山區,植物學家們始終心系中國植物發展事業,在艱難的歲月里,酬唱應和,對未來抱著希望,展現出植物學家的襟懷。與植物研究所遷移香港后仍不間斷植物研究與人才教育事業一致,流寓湘南的中山大學農學院也恢復招收研究生,來自廣東蕉嶺的徐祥浩便是此時招收的兩名研究生之一。他于1943年考入中山大學研究院,成為植物研究所一名研究生,在武江上游河畔山間入學,師從蔣英教授。多年后,當他回憶起這段艱苦而快樂的學習生活時說到,這期間他最大的收獲就是到湖南莽山原始森林做植物調查,不僅采集大量標本,還見到猴子在樹上摘野柿,野山羊自由漫步山野,見過老虎窩,甚至還在樹上采集標本時遇見珍稀的飛狐。此外,他們還到南岳衡山及樂昌九峰山等地調查,為他日后從事植物分類學和植物生態學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專業基礎。
1945年的春天,天氣似乎格外寒冷,杜鵑花也開得比往年晚。粵北與湘南相繼淪陷,中山大學被迫疏散到東江龍口,植物所也疏散到距離栗源堡20公里外的坪游山繼續開展植物標本采集、研究等相關工作。彼時,植物所人雖然少,生活也很艱苦,但同仁間坦誠相處,互幫互助,吃苦耐勞,熱愛工作,奉獻祖國的樸素情感,卻顯得如此彌足珍貴。
五
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犯香港,農林植物研究所香港辦事處再次陷入危險境地。不久,香港淪陷,而植物研究所被不逞之徒舉報為重慶敵產而遭日軍搜索,所幸沒有違禁之物,陳煥鏞等人才免遭殺身之禍。然而,因為標本、圖書資料上皆有中山大學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標志,被指認為敵產而遭到監視騷擾。他們本可以混跡于難民中冒險離開香港,陳煥鏞卻“惟每念及畢生心血所羅致,儲存于一百余副柚木柜中,十五萬號之珍貴植物標本,及四千余部之中西文圖書暨儀器等,又豈忍恝然不顧,拱手以資敵人耶。在其嚴密監視之中,欲求保存,固有不能;將之毀滅,勢亦不許。再四思維,苦無對策,只有物亡我亦隨物亡,物存我亦隨物存,未敢先求去”。
最終,為了保存這批珍貴植物標本、圖書及儀器,陳煥鏞與所員一致決定,與汪偽政府合作,把研究所遷回廣州。這是一項風險極大的行為,也是極為艱難的選擇,甚至會被扣上漢奸賣國之罪,然而,為了保存這批“費盡幾許心血,歷盡多少艱苦博取得來之科學珍品”,陳煥鏞別無他法,唯有將自己的生命與聲名置之度外,犧牲一己之榮辱來保全,“名誠棄守,光復可期;文物云亡,難謀歸趙。為山九仞,豈虧一簣之功,來日大難,當抱與物共存亡之念,赴湯蹈火,生死不辭,毀譽罪功,非所敢顧”。
物資順利運返廣州,侯寬昭則留守香港,直至陳煥鏞及所里員工之物品全部運回廣州,他才返回。多年后,侯寬昭在回憶這段經歷的時候說道:“那時我是單身一人,假若要獨善其身的話,是不難離開此險惡環境的。但念未保存此血汗積成的文物,又不能不舍身以赴,因此決定留守到底,生死不顧。”
這是現代中國和世界最為動蕩的一個時期,也是植物研究所創建以來最動蕩的一段歲月,國內不少地方及不少國家的珍貴標本都毀于戰火。近的來說,陳煥鏞參與創立的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創立時候一無所有,從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撥贈20副柚木標本柜約3000號植物臘葉標本給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而后又在出席世界植物學大會時,為其在歐洲采購了一批植物學圖書、雜志、顯微鏡等資料和儀器,為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及近代植物學研究鋪墊了基礎。然而,隨著抗日戰爭爆發,日軍鐵蹄進入華南,廣州淪陷,梧州亦遭受空襲,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隨廣西大學農學院遷到柳州,此后又經歷多次遷移,跌宕起伏,風雨飄搖,不幸的事情終于發生。“1943至1944年間,該所植物標本、圖書、儀器,一部分沿湘桂鐵路西遷時被毀于侵略戰火,另一部分在貴州榕江毀于洪水天災,全部喪失,蕩然無存。”直到戰爭結束后,陳煥鏞再次從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抽出5萬份復份標本贈送給該所,助其復建。
而其他國家,如德國植物學家Burret為紀念陳煥鏞所作出的貢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瓊棕的主模標本,原收藏于德國柏林植物園暨博物館,二戰中被炸毀,后選模式仍然保存在農林植物所標本館。還有一批菲律賓的標本,其本國的標本在二戰中被毀,而存于植物所的標本因及時轉移到香港,得以完好保存。
多少人類文明成果與生命在戰火中灰飛煙滅,而農林植物研究所成為中山大學在抗戰中唯一能比較完整保留標本、圖書、儀器的單位,并且是我國戰后植物研究復興的主要機構之一,以陳煥鏞為代表的所有守護者可謂厥功至偉。
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所有為避戰火而遷往大后方的高校紛紛回遷,中山大學遷回廣州。“廣東植物研究所”亦遷回,并恢復農林植物研究所原名,被日軍毀壞的植物標本園開始重建,遷往香港的標本、圖書、儀器設備亦回歸,并開始編撰各類植物志,各項科研工作有序開展,對外交流合作順利進行。
在戰火連綿的幽暗歲月里,在風雨如晦的驚濤駭浪中,以陳煥鏞、蔣英、侯寬昭等為代表的一批中國植物學家、科學家,不計個人得失,不計生死榮辱,以生命守護中國植物研究之成果,為了真理、為了民族、為了植物跳動的赤子之心與報國情懷,隔著近百年歲月,依然清晰可感。那些為植物事業孜孜不倦追求的瞬間,那些與自然坦蕩相處的時刻,那些為守護標本而生死不顧的大義,成為戰火下的流離歲月里永遠蒼翠的記憶。
(責任編輯: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