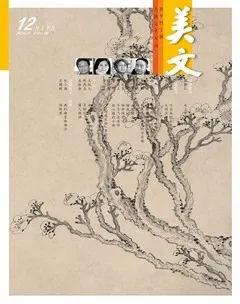俗世聞見記
單位旁邊有一菜市,我差不多每天要去轉(zhuǎn)一轉(zhuǎn)看一看。那些模樣可愛的蔬菜,還有賣菜的人,以及人來人往的熱鬧氣氛,都是我喜歡的。
一
五月十日。上午八點(diǎn)過,在單位門口碰上一個(gè)挑著擔(dān)子的老人往菜市走,我跟在后面,也往菜市去。他菜擔(dān)的前筐里是一堆土豆,還有一些韭菜,后筐里全是小白菜。那些菜,既鮮又嫩,讓人想起年輕、青春這樣的詞。菜都弄得干干凈凈,整整齊齊。那些韭菜,一樣粗,一樣長,青是青,白是白,絲毫不亂。小白菜也是這樣,一頭綠一頭白,清清爽爽,看了覺得舒服。我想,這些菜是他老伴收拾的呢,還是他自己收拾的呢?他們一定是認(rèn)真過日子的人。日子也一定過得清清爽爽的吧……老人進(jìn)了菜市,起初,他想把他的菜擔(dān)放在一個(gè)空地方,他前后看了看,覺得不夠好,因?yàn)樽笥叶际莿e人的攤位,中間這空檔太小,容不下他的擔(dān)子,就往前走,又見一個(gè)空地,停下來,打算放在那兒,可是那兒來往的人少,也不好,又朝前走,終于找到一塊地方,能容下他的兩個(gè)擔(dān)子,來往的人也多,又不妨礙誰,他就把他的兩擔(dān)菜安頓下來。他蹲在那兒,守著菜,等候顧客。我在旁邊看著他,他像一個(gè)父親守著自己的孩子一樣,臉上既歡喜,又有些不安。一個(gè)顧客來了,想買小白菜,他嫌給價(jià)低,沒賣。又一個(gè)顧客來了,問韭菜怎么賣,他說了一個(gè)價(jià),對方一聽就走了。第三個(gè)顧客來了,在筐子里翻他的土豆,他說了個(gè)價(jià),顧客頓了頓,還是走了。他旁邊的攤位,菜都賣得差不多了,他的生意還沒開張。我替他著急。這么大兩擔(dān)菜,得趕緊賣啊。如果賣不完怎么辦?肯定不能挑回去,專門來賣菜,哪有挑回去的道理。那怎么辦呢?只有一個(gè)辦法:減價(jià)。可是,這么好的菜,減價(jià),他愿意嗎?我離開那兒,到別處轉(zhuǎn)了轉(zhuǎn)。轉(zhuǎn)一圈回來,發(fā)現(xiàn)那地方空了,他和他的菜擔(dān)都不見了。是不是換了地方?四處看了看,沒有他的身影。他的菜都賣完了?咋又這么快了?是不是來了大主顧一下子全買走了?這種可能是有的。肯定是這樣。我想起小時(shí)候賣柴的事。我小時(shí)賣過柴的。我們天一黑就出發(fā),把柴背到街上天還沒亮。本來很早就到了市場,可是我們心大,要價(jià)比別人高,結(jié)果有人問沒人買,弄到后來,市場上的人越來越少了,還沒賣脫,心里就著急,也后悔,打算降價(jià)出售。這時(shí)卻忽然來了個(gè)大買主,他把手一揮說,你,你,還有你,都給我背到學(xué)校食堂去。聽說他是鎮(zhèn)上小學(xué)里管后勤的,一口氣買了幾百斤,一下子,我們的柴都脫手了,價(jià)格,比我們想象得好。我們的快樂是可以想見的。這個(gè)賣菜的老人,也許跟我們一樣幸運(yùn)吧?
二
五月十一日。早上下過一陣雨,七點(diǎn)多去菜市,到處是泥水,臟亂不堪。不過,那些擺在地上的菜,不管什么菜,都給襯得格外得漂亮好看,蔥子水靈靈的,茄子紫亮飽滿,黃瓜清秀鮮嫩,蘿卜白白胖胖……
可是,出現(xiàn)了令人不快的一幕。一位個(gè)頭矮小、滿頭白發(fā)的老婦,看樣子七十多了,背微微有點(diǎn)駝,挑著一擔(dān)菜走進(jìn)菜市,因?yàn)閬淼猛砹诵粫r(shí)沒找到合適的地方,就一邊走一邊找。她的擔(dān)子里有小蔥、瓢兒菜,鮮嫩碧綠。正走著,有人想買她的小蔥,她就地放下?lián)樱米詭У臈U秤給人稱量。旁邊攤位上的花衣女人不高興了,黑著臉剜她一眼說:“看你放的地方,把我遮到了!”老婦看著秤上的準(zhǔn)星說:“給人稱點(diǎn)蔥就走。”話里含著一點(diǎn)道歉的意思。可是花衣女人不依,從攤位上繞出來,將老婦一個(gè)擔(dān)子提起,咚地一聲扔到一邊。擔(dān)子里的那些菜好像嚇著了,簌簌地一抖。我擔(dān)心她們會吵起來。沒有。老婦看了一眼扔在一邊的菜擔(dān),沒說什么,給人稱了小蔥,收好錢,把兩個(gè)擔(dān)子提到一堆,彎腰挑起,到別處去了。
看得出來,花衣女人也是農(nóng)村來的,不過,她來得早,已經(jīng)在城里定居下來,在這個(gè)菜市,她有自己固定的攤位,就是那個(gè)用磚頭和石板搭建的平臺。老婦呢,城郊的農(nóng)民,每天挑著擔(dān)子進(jìn)城來,都得臨時(shí)找地方,她的攤位就是兩個(gè)移動的菜筐。因?yàn)檫@樣的差別,花衣女人在老婦面前就有了一種優(yōu)越感。因?yàn)閮?yōu)越,所以蠻橫。我想,如果跟老婦一樣,她也是從郊區(qū)來的,每天都要臨時(shí)找地方賣菜,她會怎樣呢?
三
五月二十四日。一個(gè)賣蛋的農(nóng)婦,把攤位擺在閑置的肉攤前。她坐在肉攤下一塊石頭上,后腦時(shí)不時(shí)要碰上肉攤上的鋪板。有人說,你坐在那里腦袋都伸不起,換個(gè)地方嘛。她說,沒啥,我一直是這樣。我想,她不講究,大約是苦慣了,麻木了,可以改變處境的時(shí)候,也不改變一下。在鄉(xiāng)下,這樣的人不少。
她左邊放著一個(gè)大花籃,里面裝滿雞蛋、鴨蛋,右邊地上鋪著一條塑料袋,上面堆著一大堆雞蛋、鴨蛋。雞蛋略小,淡黃色,鴨蛋略大,灰白色。買蛋的各自挑,要啥挑啥,都是九塊錢一斤。我給她拍照,她很高興,問:“你要發(fā)到抖音上去?謝謝你,幫我宣傳。”她并不等我回話,忙著招呼顧客去了。她性格直爽,肯說,口快,問什么說什么,有時(shí)不問也說。她說她是離城二十多里的凌云人,每逢一四七進(jìn)城賣蛋,已經(jīng)賣了七年。
我問:“你這些蛋是在鄉(xiāng)下收的還是自家產(chǎn)的?”她嘴里哧的一聲,不屑地說:“哪個(gè)去收蛋賣喲,我的蛋都是自家雞鴨下的。”“你家養(yǎng)了多少雞鴨?”“兩千多只雞、兩百多只鴨。這個(gè)季節(jié)正是產(chǎn)蛋的時(shí)候,每天要撿六七百個(gè)蛋。”我夸她能干,她一笑,說,她養(yǎng)雞鴨用的飼料,有稻谷、洋芋、苞谷,還有必不可少的青飼料,如蘿卜纓子、牛皮菜、包菜之類,都是自己種的,從來不去外面買那些添加了可疑之物的東西來喂雞養(yǎng)鴨。她的意思是,她的飼料是綠色無污染的,養(yǎng)出的雞鴨以及雞鴨下的蛋,都可放心食用。
她說話跳躍性大,忽兒又說到另一件事:村里有人本來在外面打工,看我們養(yǎng)雞搞得鬧熱,不打工了,回來修棚子養(yǎng)雞,可最后雞都死了。我問怎么回事,她說:“他修鐵皮屋子養(yǎng)雞,不通空氣,容易得病,得病就要死;我們是瓦房里養(yǎng)雞,通空氣,不得死。”“你家有那么多瓦房?”“我們借鄰居的房子。”她說,“一開始,我家老人打算自己修雞舍,我不同意。那要花很多錢,還費(fèi)事。我另有辦法。我們那一灣有十三戶人,平時(shí)大多在外面打工,年底才回來過年。他們回來了,我們就給每家送一百個(gè)蛋、一只雞、一只鴨,還送一方臘肉或者一個(gè)豬腳桿,總共值六百元左右。過了年,他們又外出打工,走的時(shí)候,都把房門鑰匙交給我們,一是讓我們照看一下房子,二是他們的雞舍和牛圈我們隨便用。年年這樣,我們就不另建圈舍了,省了好大一筆錢。”她很會盤算。
她接著剛才的話說:“他家的雞是伏在地上歇息,那樣雞肚子容易著涼,一著涼就屙白屎,這就容易生病。我們家的雞舍,是用竹篾編成笆子,再用竹笆搭成一個(gè)樓(離地一尺高),雞都歇在竹笆樓上,從來不會涼了肚子。”
我說,你養(yǎng)雞有這么些好經(jīng)驗(yàn),可以幫幫那些養(yǎng)殖失敗的人呀。她看看我,嘴一扁:“管那些閑事做啥?”她不肯金針度人。她又說,養(yǎng)雞不是簡單事,天晴咋喂,下雨咋喂,天熱咋喂,天冷咋喂,各有講究。我問,天熱怎么喂?她警惕地看我一眼,不告訴。我說我不養(yǎng)雞,不會搶你的飯碗。她說:“過經(jīng)過脈的地方不能說。對哪個(gè)都這樣。村里有人叫我講,我也是這個(gè)話。怎么什么話都給你講呢?總要留幾分。”
把一撥買蛋的招呼過了,看我還在,她又說起來,不過說的卻是另一層意思:“養(yǎng)雞苦啊,苦得不叫人。賣蛋也沒搞頭,一是掙不到幾個(gè)錢;二是離城遠(yuǎn),難得背,又耽擱時(shí)間;三是麻煩,路上要換幾回車,擔(dān)驚受怕——怕把蛋壓壞了,怕掉東西。原來娃兒給我弄了個(gè)微信片片(指二維碼),買蛋的一掃就付錢,方便得很,但是不曉得啥時(shí)在路上擠掉了,現(xiàn)在買蛋的都要付現(xiàn)錢了,你曉得,現(xiàn)在哪個(gè)身上還揣現(xiàn)錢?心焦得很……”
看樣子要跑題,我趕緊往回拉:“你說養(yǎng)雞鴨沒搞頭,那養(yǎng)啥才有搞頭?”
“養(yǎng)牛有搞頭。我家還養(yǎng)牛,現(xiàn)在養(yǎng)了三十七頭。”她說,養(yǎng)一頭牛政府補(bǔ)助一千三百元,如果母牛生了小牛,又補(bǔ)助一千三。她家的母牛一年要下七八頭小牛。“一頭小牛養(yǎng)大了,要賣八九千塊。”照她這樣說,養(yǎng)牛的確比養(yǎng)雞鴨“有搞頭”。
她說,其實(shí)養(yǎng)牛不費(fèi)事。早上趕出圈,它們自己去坡里吃草,天黑了又自己回家。“不回來的話,就跑到山梁上吹吹哨子,哨子一吹,就都回來了。”我差點(diǎn)笑起來。我小時(shí)放過牛,牛哪有這樣的。她說千真萬確,不哄人。
又有人買蛋,她稱蛋、收錢,之后閑下來,又跟我說話。不說牛了,說她跟丈夫創(chuàng)業(yè)的經(jīng)歷,說她的生活。聽得出,她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還有些自豪。她夸她丈夫會動腦筋,顧家,說他不像別的男人,總想著出去打工,他就在家里創(chuàng)業(yè),一開始是推豆腐賣,現(xiàn)在搞養(yǎng)殖。
“你家日子不錯(cuò),也修了新樓房吧?”這些年,農(nóng)村有錢的人家都修了新樓。“沒有。我們不修。”她說她家有四個(gè)娃,要送他們讀書,大女兒已經(jīng)送出來了,今年剛考上教師;老二老三讀中學(xué),最小的一個(gè)才讀小學(xué)三年級;最焦心的是老二,老二讀高中,喜歡音樂,要考音樂學(xué)院,每個(gè)周末要到校外培訓(xùn)機(jī)構(gòu)參加培訓(xùn)。“培訓(xùn)很費(fèi)錢,這學(xué)期開學(xué)交了五千,前幾天又交了五千。這些錢都要自己掙,我們從來都是靠自己,從來不要什么救濟(jì)款、救濟(jì)糧那些。有那本事生,就有那本事養(yǎng)。”
下午六點(diǎn)二十多,我在單位食堂吃過晚飯,又到菜市去,見她把攤位挪到了街邊的電桿下面。我說:“天不早了,還不回?”她說,還有二三十個(gè)蛋,賣完才回。“天黑了也不怕,反正是帶著電筒的。”她拍了拍胸前的小掛包說,回家先要坐車跑二十多里,然后有一段山路要走,如果天黑了,就用電筒照路。
有兩個(gè)老太太站在旁邊聊天,聽了她的話,暫停,轉(zhuǎn)而跟她搭話,一個(gè)說:“你一天真辛苦。”她說:“我進(jìn)城來賣蛋就是耍了,像這陣,有時(shí)間跟你們說閑話,就跟耍差不多了。在家里就不行,做完這樣還有那樣,哪有空閑跟人閑說……”這時(shí),一個(gè)中年婦女來買蛋,說:“天晚了,你減點(diǎn)價(jià),我給你全買了。”旁邊的人也附和,讓她少點(diǎn)錢。她不干。有人就說,掙那么多錢做啥嘛,你家養(yǎng)了幾十頭牛,每頭給你補(bǔ)助一千三百塊……她把眼睛一斜:“一千三百塊!你以為我全得?想得倒好,還要給人家吃些呢……”“吃”,本地方言,給人好處的意思。
“人家是誰?”有人問。“你各人去猜。”她不說。
她不降價(jià),中年婦女還是把蛋全買了。她背起花籃回家的時(shí)候,是六點(diǎn)五十二分。還有將近兩個(gè)小時(shí)天才黑。她半路上用不著電筒照路了,我想。
四
六月十日。天亮?xí)r開始下雨,上午八點(diǎn)過去菜市時(shí),雨小了些。我照例是東瞧西看。一個(gè)老漢挑著菜擔(dān)朝菜市中間走,我趕上去問,怎么這時(shí)才來啊。我是這樣的,在別處,比如大街上或電梯里,我是不隨便跟人說話的,城市嘛,都這樣;可是只要進(jìn)了菜市,不管認(rèn)識不認(rèn)識,我都能搭話,這就好比在一個(gè)村子里,跟任何人都能隨便說話一樣。有時(shí)想起自己這樣的舉動,覺得是個(gè)奇怪的事。老漢一臉皺紋,皺紋里是閃著油光的細(xì)汗,他說,他早上四點(diǎn)多就坐三輪車到八戒巷(臨時(shí)賣菜點(diǎn))搶位置,一直在那兒賣到八點(diǎn),城管人員來攆,才挑著剩下的菜來這里賣。說“剩下的菜”時(shí),他把臉扭過來,朝擔(dān)子里看了看。他的擔(dān)子里有藤兒菜、苕葉和絲瓜,每一樣都不多,確是賣剩下的樣子。他身上套著那種極薄極軟的油紙做成的雨衣,可他頭部沒有遮掩,濕的,鬢發(fā)一綹一綹地貼在臉頰上,像女人們做成的某種裝飾。我說:“你頭上都濕了,早上何不等雨停了再上街?”他臉上一緊,說:“不能等啊,雨再大,時(shí)間一到,披著油紙、打著雨傘也要出門——頭天晚上就把菜準(zhǔn)備好了,不趕快賣,會蔫掉的。”他邊說邊走邊看,看到一處空地,把擔(dān)子放下,站在一旁等顧客。我問,四點(diǎn)多就進(jìn)城,還沒吃早飯吧?他說賣完了去吃碗面。問其年齡,說是七十六。我有些吃驚。看起來他不過六十多一點(diǎn),竟是七十六了。
五
六月二十三日。遇到一個(gè)賣生姜的老漢。地上鋪張油紙,一堆生姜攤在上面。他在旁邊的地上坐著,屁股下面也鋪張油紙。擺談中知道,他是茶壩人,今天早上五點(diǎn)多出門,自己開三輪車?yán)獊淼摹K以诔抢镔I了房,兒子在北京打工,一家公司的高管,一年掙三十多萬。我說:“你家條件不錯(cuò)嘛,可以在家享福了,還這么辛苦?”他說:“務(wù)了一輩子農(nóng),天天做活路,哪里耍得慣?再說,這才六十七歲,如果現(xiàn)在就開始耍,怎么耍得老?”“耍不慣。”他又說。這話我是信的。農(nóng)村人差不多都這樣。我大爹已經(jīng)九十二了,還每天放牛。我舅父舅母,都七十多了,還在種田。他們的條件都是很好的,兒孫在老家給他們修了樓房,每月打錢回來,要他們養(yǎng)老,什么事也不要干,可他們不聽,要做,說是閑不住,耍不慣。
六
七月十三日。一個(gè)老漢來菜市賣背篼。一個(gè)農(nóng)民模樣的矮個(gè)男人摸著他的背篼說:“你這背篼是用往年的竹子編的。”老漢斜眼看他:“你是不是農(nóng)村來的?說這樣的話。”我接話:“從這竹篾的色澤看,是今年的竹子編的。”我是農(nóng)家長大的,有這方面的經(jīng)驗(yàn)。“陳年的竹篾是黃色,他這個(gè)竹篾是新鮮的綠色。”我猜,矮個(gè)男子可能是故意那樣說,大約是想買老人的背篼,先以此壓一壓價(jià)格?聽我這樣說,矮個(gè)男子走了。
老漢把他背上的三個(gè)背篼放下地,跟我說起話來。
我:“編一個(gè)背篼要好久?”
他:“一天嘛。”
我:“要幾根竹子?”
他:“兩根就夠了。”
我:“頭尾要去掉吧?”
他:“頭子要保留,尾子(竹梢)那一截,嫩,要去掉。”
我:“成年的竹子才能用。”
他:“最少要三四歲的竹子才能編背篼。嫩竹不能用。”
我:“一個(gè)背篼賣多少錢?”
他:“五十塊在賣,四十塊也在賣。”
這時(shí),一個(gè)年輕女人來問價(jià),他說:“你要的話,四十五塊錢一個(gè)。你看,我編的多硬扎。”說著提起一個(gè)背篼放在地下,兩手用力壓,背篼就一閃一閃的,一松手,又回到原來的狀態(tài),不變形,確實(shí)很硬扎。女人就買了一個(gè),說是要送回鄉(xiāng)里讓媽用,她媽在老家屋邊塘里養(yǎng)魚,用這種背篼割草喂魚很合適。
老人說他快滿八十了,是從白云過來的。他今年已經(jīng)賣了一百多個(gè)背篼。我說:“那你家栽的竹子多哦。”他說,現(xiàn)在農(nóng)村到處是竹子,沒人要,有些人還喊他去砍。竹子這東西,多年不砍不行,會老死。“我把竹子砍回去,收成料,堆在屋里,用油紙蓋好(保持水分),然后慢慢編,一天編一個(gè),編出十來個(gè)就弄到街上來賣。”
“你今天背來多少背篼?”
“十個(gè)。已經(jīng)賣了八個(gè),還剩兩個(gè)。”他說他從白云坐車進(jìn)城,在后河橋下車就開始賣,一路走一路賣,這會兒賣到了這里。
七
七月十六日。在菜市門口遇一老人賣花椒。他個(gè)頭不高,頭發(fā)稀疏,我估計(jì)他八十多了,近前問,老人說他1924年生人,今年吃九十八的飯了。我一驚,這么大年紀(jì)了,還做買賣。我以為他也是從鄉(xiāng)里來的,卻不是,說家就在城里,住老城白馬井,住那兒幾十年了。他家在頂樓,屋頂原來空著,他找人給鋪上泥土,栽上花椒樹,四五十棵,年年結(jié)好多花椒。這段時(shí)間花椒熟了,他天天來賣。一年能賣四五千塊錢。我說:“您這么大年紀(jì)了……叫家里其他人來賣嘛。”他笑了笑:“他們都有事,只我有空。”“您賣得的錢,自己花,還是……”他說,錢不重要,錢都給他們,他一分也不要,就想找個(gè)事兒做。他打不來麻將,也干不來別的,就喜歡弄一弄花椒樹。花椒樹結(jié)的小果子當(dāng)然是香了,它的葉子也是香的,也能吃,用油炸了吃,很香。“你吃過花椒葉吧?沒吃過?那你要試一試……”“我就喜歡弄一弄花椒樹。”他重復(fù)說。
八
七月十七日。有人賣桑葉,一塊錢一把,一把二十張,用來蒸苞谷饃的。這時(shí)節(jié)苞谷熟了,前兩天就有人賣苞谷漿了。用桑葉包上苞谷漿,放在鍋里蒸熟,就是苞谷饃了。還有人賣桐葉,一塊錢一大把,也是蒸苞谷饃的。
有人賣棗子,剛從樹上摘下來的,還帶著新鮮的枝葉。這是今年第一次在市場看到棗子。
還有一位老人賣馬齒莧,一塊錢一把。馬齒莧煮熟涼拌,是佐餐的好菜。我小時(shí)候,暑假期間,采過馬齒莧,一般吃過早飯之后去,因?yàn)樵缤硪排8畈荩坏每铡qR齒莧通常長在紅薯地里。夏季去田野里采野菜,上有太陽曬,下有地氣熏,人夾在中間,極熱。采馬齒莧是相當(dāng)辛苦的,一塊錢一把,實(shí)在說,太便宜了,差不多是白送。我買了三把馬齒莧,給他十塊錢。我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表達(dá)對他的敬意。
九
七月二十日,晴。上午八點(diǎn)多到菜市,遇一七旬老婦,她背上的花籃里裝一個(gè)鼓鼓囊囊的大口袋,手里又提幾個(gè)鼓鼓囊囊的小口袋,在人群里走來走去地叫賣。我近前問她賣什么,她把手中的口袋送到我眼前,說:“泡茶喝的,清熱解毒。”袋里是一些曬干的野草和樹葉。她口中的牙齒掉了好幾顆,嘴唇往里面癟進(jìn)去。她看我在注意她,趁勢又把口袋往我面前送了送,隨即介紹:這里面有夏枯草、車前子、過路黃、曲麥、金銀花、海金沙、桑葉、折耳根等十幾種,可以泡茶喝,喝了可除體內(nèi)濕熱,除了濕熱就神清氣爽。十塊錢一袋。她說她是鼓樓山的,七十五了,年年清明節(jié)那幾天上山扯草,大山里的東西沒污染,野草干凈得很,扯回來先洗后曬,切成一段一段的,這才拿到街上來賣,經(jīng)過好多手腳。“你去藥店買個(gè)感冒藥也要幾十塊,我這才十塊錢,一點(diǎn)也不貴。”她勸我買,我未及說話,又一人來問她賣的什么,她又一口氣報(bào)出一串名字:夏枯草車前子過路黃……對方?jīng)]聽完就走了,她怕我也走,趕快轉(zhuǎn)身跟我講:“我平時(shí)不上街,有人打電話才來。人事局有個(gè)人昨天打電話,叫我今天送些草草藥來,我早上天不亮就出門……”我打斷她的話:“你今天賣了多少?”她說賣了四五袋,接著又按她先前的思路說下去:“這些草草,淘得干干凈凈的,老的小的都可以喝,不苦不澀不酸。”看我還是沒有買的意思,她直接說:“你拿一袋回去試一下嘛,才十塊錢。”我勸她:“你這樣一直站著多累啊,走,我們到前面找個(gè)地方坐下來。”我掂掂她背上的花籃,二十幾斤的樣子,不重,不過,長久壓在肩上也是有些累的。她不去,說她還是喜歡走著賣,又說:“你買一袋嘛。”我正要說話,一老婦來問她:“你這里有沒有做豆瓣的香料?”她轉(zhuǎn)頭回答說,今年還沒到時(shí)間,過幾天才去山上采。問的人走了,她回頭又跟我說:“這些草草都是野生的,小娃娃喝了屙的尿都是清亮的……”我想,藥,那是不能亂吃的,不過,我得買一袋了,再不買,真不好意思了。就買了一袋,給她十五元。
這老人家,嘴巴真能纏人。不過,這草藥我小時(shí)也是采過的,比如柴胡、海金沙,還采過百合。放了暑假,我們差不多天天上山采藥。這些東西,山里多的是。可是要從山里弄回來也不容易,它們往往長在荊棘叢里,生在巖崖上。我們采回曬干,也是賣錢。不是去市場賣,是賣給供銷社。那時(shí)沒有自由市場。我們上學(xué)讀書的費(fèi)用,就是這樣一天一天采藥賣湊起來的。
十
七月二十九日。今天遇到個(gè)賣木制品的老人。他斜著身子坐在菜市一角的石桌上,石桌上擺著長長短短的木制品,搟面杖、鋤楔、搗蒜泥的擂櫆子,等等,有的是柏木做成,有的是青岡木做成,都磨得光溜溜的,摸上去感覺很細(xì)膩。我挨個(gè)看,挨個(gè)摸,贊嘆老人的手藝好。有一樣?xùn)|西我看著陌生,像個(gè)木棍似的,老人說那是咬牙棒,一種是花椒木做的(二十元一個(gè)),一種是柏木做的(十元一個(gè)),是給嬰兒咬著玩的。經(jīng)他一提,我記起,在農(nóng)村,嬰兒長牙的時(shí)候,大人就給他嘴里放個(gè)咬牙棒,好讓他磨牙。老人說,現(xiàn)在農(nóng)村的木匠還多,但做咬牙棒的人少。他二十歲開始學(xué)做木工活,幾十年來,從來不做這種小東西,做的都是大件,修房造屋,打柜子,做床,后來年紀(jì)大了(他今年七十五歲),就不做木活了,可有時(shí)想練練手,就做做這些小東西。我發(fā)現(xiàn)他左手有些特別,原來食指短了一截,中指呢,下端特別粗而上端特別細(xì)。老人見我注意他的手,就攤開兩手給我看:“做木活危險(xiǎn)性大,你看,我這一雙手弄成什么樣。鋸子把手指鋸斷——當(dāng)時(shí)就斷成兩截,鑿子把手肚上的肉鑿掉一大半……”他皺著眉,搖搖頭,好像危險(xiǎn)又發(fā)生在眼前。我聽得張開嘴忘記合上。停了停,他拿起一根搟面杖說:“有人看這么個(gè)小東西喊價(jià)十塊,嫌貴。他不曉得,做這東西要經(jīng)過好多手腳,費(fèi)工,還費(fèi)手,弄不好要受傷,還可能整掉一塊肉,哪是容易的事啊。”我以前也沒想到這些,聽他這么一說,覺得木匠不好當(dāng),他真不容易。“把這些賣了,我也不打算再做了。這活危險(xiǎn)性大。”他抬手指指右眼說:“那一回,差點(diǎn)把我眼睛弄瞎了。”我忙問怎么回事,他給我比劃起來:“那一回是做擂櫆子的擂棒,剛把一塊木料塞進(jìn)鋸片那里,哪想到一下子反彈回來,唿地一下打在我眼睛上,幸好,偏了一絲絲,打在眼角上,如果打在眼球上,當(dāng)場就要弄瞎了。”我聽得心驚肉跳。
走的時(shí)候,我買了一個(gè)咬牙棒、一根搟面杖。
(責(zé)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