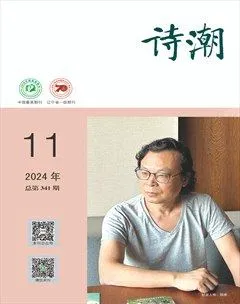我的理性與激情 [四章]

關于梅妻鶴子的現實困境
林逋是一個有疑問的人?林逋是一個解決了所有疑問的人?林逋的疑問有時不像個疑問,倒像是陰影,像一堆虛無的氣泡。明明是被一雙手送入空中,被一個嘴巴越吹越大,但你卻看不到,你依賴了虛幻的描述,依賴了一個人的品質和他明亮的本性,但你依然看不到。疑問本身不具有物質屬性,所以它才構成疑問?像菊花的精魂必須在它凋零之后,才能在空氣中感受它的肉體,感受它留在火光中的黃金和寓意。
我如果遇到這樣一片梅林,我會不會用大喊大叫來表達驚喜?會不會在雪地中翻滾直至筋疲力盡?大于三朵或三朵以上的梅花不屬于個人,它是一片森林。它是一片風景。必須由眾人所有,必須由眾鬼所有,必須由眾神所有,必須被眾多驚喜而熱烈的手折斷,并被帶回城里;而林逋僅留下風聲就夠了,風聲可以讓一片失敗的梅林更遼闊、更安靜。
天上的白鶴也可以就此解脫,藏身在落英中的梅花鹿也不必為此膽戰(zhàn)心驚。白鶴不必再向主人送去梅花開放和陌生來客的消息,梅花鹿也不必再到小鎮(zhèn)上去馱回糧食、菜蔬和酒壺。讓梅子腐爛在樹根下。讓草庵閑置到雜草叢生。讓白鶴和梅花鹿都遠遠走開吧,只留下林逋一個人在樹下放聲痛哭。
我的原意其實并不是這樣,我想把林逋帶回城里,改掉他閑散的個性,從此做個文明人,過錦衣玉食、兒女繞膝的好日子;像花園小徑上優(yōu)雅的月牙兒,夜夜徘徊在溫馨的夢里。但林逋死了。林逋死于東漢還是魏晉?死于衰老、疾病還是一個人的悲憤?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林逋留下了另一個疑問。林逋的生活是神仙的生活,神仙的生活需要避開別人;林逋的生活是鬼魂的生活,而鬼魂都隱匿在清風和露水之間,只有半空中的白鶴才能看清它們的藏身之處。而我需要披著蓑衣,抱一張古琴,或背著一把寶劍,一路高歌,才有可能在山中和他相遇。我披頭散發(fā)像游俠一樣落魄。我蓬頭垢面保持散淡的笑容。只有這樣,我才能敲響他秋風中破敗的屋門。而找到他又有什么用呢?他是個和影子結伴的人,他隨時都是一副飄走的樣子,我只能追上他的回音,而無力接受他的疑問。即使他毫不憐惜自己的問候,我又該如何向他介紹我的身份和來歷?
三百六十五棵梅樹是一片梅林。三百六十五包梅花是一片濃蔭。而三百六十五袋梅子是一個鬼魂一年生活的口糧嗎?要收獲谷黍需要在大地上終生耕耘。要得到魚蟹需要在波濤上付出勞役。而要在光芒中磨礪一個人的品質就需要在光芒中隱居嗎?那么林逋在山中說出的話語則必是光的果實?而他的身影和心靈,這片風景中的麋鹿、白鶴、流水和梅林是誰放在山岡上的?它們的心里裝著誰的秘密?是誰讓它們在這里等著一個書生的到來?這個書生是我嗎?
站在高高的山岡上,我看到的大地,是一片幸福的空曠和死亡的靜寂。
今天或明天:虛妄與現實
在蕓蕓眾生之中,我只與有限的人交往,只選擇三五個志同道合者成為朋友,只留下一個現實或虛構的人坐在心中;更遠處的生活我只能依賴想象,而無法參與其中;這就是我今天的局限。而我今天將要遇見的人,就是我今天的全部。我必須主動提醒自己:接受他們是命運給予的幫助,是神靈賞賜的果實;今天沒有善惡之分,只有先你而死的錯誤和庸人,只有帶著一顆干凈之心來到的嬰兒和內心暗藏苦澀,但依然滿臉浮現甜蜜耗盡余生的老人。
他們是一些生命靠近新生和尾聲的人。他們都是追不上我的人,而我占有了今天全部的時間和幸福。我有成熟的身心和思想。我和今天的神靈一起飛舞。在一個人的力量范圍之內,我見到的痛苦和享受的快樂既符合心靈和理智,也符合想象力的眷顧;所以我不必盲目回憶過去,也不必寄希望于來世,我只需細心地關注自己的今天,以免使自己的心靈因過分陷于思想的憂慮和時間的激流而迷失了應有的準確與清晰。
今天是一條河,我只是其中的一道渦流;而心靈則是身體的夢鄉(xiāng),屬于靈魂的只是一個夢中身影,或是夢中堆在云端的高高的巨浪和它雪白的浪花的回響。我好像又是另一種虛妄了。今天只是一所過客的居所,四面漏風,八面見光,但太陽是真實的,花草樹木和其中的風風雨雨是真實的。
除此之外,今天并不占有更多的奢望,簡單的今天為再有一千年的歲月而流下感激的淚水和幸福的沉默中飄滿了甜蜜的臉龐。但當你關上門,我的心靈變得一片漆黑,像夜晚來臨,我在顫抖,這是你送給我的孤獨和創(chuàng)傷嗎?我的靈魂并不因寄身在普通的肉體之中而自感卑微,但它一定會因更大的羞愧和獨立而找到自己的方向,這或者是一種大于今天的信心和力量?
死亡和生前一樣,它們寂靜而空曠;而現在它只是一種表象,只是通過“我”互相聯系它們。如果是空氣,我推動它們飄蕩;如果是火焰,我需要重新把它們點亮;如果是裂縫或一面墻,我就需要通過再生之手把它們接入。但我不會長久橫亙其間,我必須接受時間的安排,必須被時間所熄滅或重新點燃,必須在循環(huán)往復的寧靜之中騰出現在的位置,以繼續(xù)獲得生存的形式和遠方,那我也將樂于接受其中神秘的磨礪,而這就是我自己的今天和它的全部過程。
在生死之間,我只有一個困惑:如果我中途拒絕了今天和自己,我的心靈是否將無所依傍?是否將因此而更快地消散于寂寞的大地或暗淡的春光?
關于世界大洪水
我們始終是洪水的信徒。即使在方舟之上我們也從沒有把自己的錯誤歸咎于洪水。《圣經》上一直把它視為奇跡,因為有一艘大船畢竟在上帝所允許的高度上停住。當然這絕不是人類的理性,而是上帝對罪惡的懲罰一開始就擁有限度;人心高不過自己的頭顱,山峰高不過上帝的腳趾;洪水即使懷有深淵一樣的私心和天空般廣闊的激情,它也不敢把上帝的寶座沖毀;但把全世界都徹底淹沒而只允許一艘大船逃生的洪水肯定是源自無中生有。
一片云團推動的巨石在大地上滾動,它有雷霆的轟鳴和靈魂的顫抖;上帝要溺死人類的想法如同打開閘門放出地獄之水,即便上帝堅持一百五十天不讓洪水退卻,但為了給自己留下有數的祭壇,他還是原諒了那些高出我們人類視線的山頂;從此人類開始通過信仰相信了上帝和他的奇跡。但物理學家卻說:讓一場大洪水淹沒全球絕不可能。如同巴別塔和先知的驢子,上帝似乎在通過一個幻象考驗著我們的肉體和理解力,只是他捎帶著也賭上了我們慌亂的命運。
這厚顏無恥的上帝!在這一點上,我唯一與伏爾泰有所茍同:我們贊賞萬物而又不解于萬物。我們就是自己的陷阱。
波濤的歷史
“大明的船隊像云一樣飄過來,又像云一樣消失”。從此之后,片板不許入海。海洋成了中國人的精神禁區(qū)。只默許海盜占領島嶼,只默許海盜的后代用獵槍射殺礁石上的漁姑。而海盜的母親藏身在甲板下,默數著她所囤積的黃金細軟;她華貴的身體里長滿幽暗的苔衣,她像一個蒼老的巫師,長著漏風的牙齒。
她一個人在無聲夸耀著一群瘋狂的發(fā)現者所創(chuàng)造的時間和奇跡。從長安飛馬而來的錦衣使者,把皇帝的禁令掛在古驛道的旗桿下,并且大聲呼喊著,讓一個海洋帝國越退越遠,一個國家對自己的懲罰也在變本加厲。而陸地上越來越密集的人群,即使聞到海腥味兒也會眩暈和嘔吐。
直到今天,21世紀的今天,時間多么快。一群創(chuàng)造者使用輪渡的方式,才改寫了一片海洋到另一片海洋的歷史。從旅順口到煙臺或大連,從東北到山東半島,從膠州灣到達暮色蒼茫的南海,其實是一片波濤把一個歷史填埋,而另一片波濤則把一個新的歷史舉起。但波濤本身卻是從來也不會改變的,即使它天天大喊著從船舷邊跳過來,也不會有人認出它前朝的浪花和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