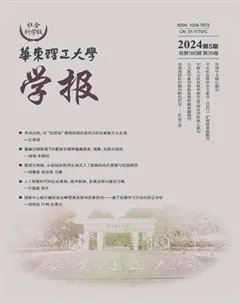作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五社聯動”
[摘要] “五社聯動”由“三社聯動”發展而來,是一個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從簡單到復雜、從分散到協調的必然趨勢。在本質上,“五社聯動”是一個人類行動者與非人行動者同構而成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其得以可能的關鍵在于核心行動者的“轉譯”。在未來的發展中,“五社聯動”不能僅限于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社區志愿者、社會公益慈善資源等既有的五類行動者,也將吸納新的行動者進入其中,并進一步完善“聯動”的形式和質量,成為一個“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區治理共同體。
[關鍵詞] 五社聯動 社區治理共同體 行動者網絡 轉譯
[基金項目] 本文系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青年項目“疫情常態化背景下社區治理共同體建設研究”(TJSRQN22-00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社區工作者知識建構及其應用的社會學研究”(24CSHI2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徐立娟,天津理工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基層社會治理、社會工作;劉振,天津理工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社會工作理論、基層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7672(2024)05-0086-11
2021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完善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治理激勵政策,創新社區與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會公益慈善資源的聯動機制”。至此,作為創新社區治理體系、提升社區治理能力的一般機制,“五社聯動”進入了治理現代化的規定內涵之中。迄今,“五社聯動”已逐漸向全國鋪開,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熱議話題。但在實踐中,不乏案例緊扣“五社”等五種治理主體,忽略了“聯動”的要義,使“五社聯動”成為缺乏活力的封閉系統。此即對“五社聯動”理解較為片面,未能掌握其本質意涵。鑒于此,本文嘗試梳理“五社聯動”的生成路徑,闡釋“五社聯動”的內涵要義,為“五社聯動”的未來發展提供參考。
一、 研究回溯與理論創新
(一) “三社聯動”與“五社聯動”:既有研究回溯
作為“五社聯動”前身和雛形,“三社聯動”的概念自誕生起即備受關注。“三社聯動”的基礎在“社”,關鍵在“聯”①,學界對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內涵要義和聯動機理兩大議題上。就“三社聯動”的內涵要義而言,主要有兩派觀點:一是治理主體說,即“三社聯動”是居委會、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等治理主體間的合作互動②;二是治理要素說,即“三社聯動”是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等治理要素間的資源共享、優勢互補與相互促進③。就“三社”的聯動機理而言,有學者認為,“三社聯動”在本質上是一種政社互動,促進國家與社會的共生是兩者得以聯動的基礎④;有學者建構了“接納—嵌入—融合”的理論框架,以期消弭“三社”之間的縫隙,使其得以聯動⑤;另有學者強調“三社聯動”中權力格局的張力⑥和“主觀有限理性”⑦是阻礙聯動機制形成的重要因素,而“社會自主聯動”⑧與“社區聯合黨建”⑨則成為破解聯動困境的重要抓手。
較之“三社聯動”,目前學界多是將“五社聯動”放置于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思考其概念界定和價值功能⑩,抑或將“五社聯動”視為滿足基層實際需求的治理工具。1112對于“五社聯動”的內在機理學界似乎默認等同于“三社聯動”,缺乏深度剖析。實則,“五社聯動”將“社會公益慈善資源”等“非人”要素納入了聯動范疇,“三社聯動”框架下的“治理主體說”和“治理要素說”都難以概括其全部內涵。以往“三社聯動”研究中的“國家與社會”視角和YyXhAUGif0BcdsK54JNCnQnA5ktQeYjQSEH8SMD2+qc=“嵌入”理論均難以解釋“五社”何以“聯動”的問題。故此,本文嘗試將“五社聯動”視為一種“行動者網絡”,應用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對“五社聯動”的本質意涵與發展路徑進行學理性解析。
(二) 行動者網絡理論:關于“五社聯動”的新視角
行動者網絡理論(ANT)是科學社會學的經典范式。1986年,米歇爾·卡龍(Michel Callon)在《行動者網絡的社會學——電動車案例》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行動者網絡”的概念。①此文描述了1973年法國電器公司(EDF)提出開發新型電動車計劃(VEL)的過程。在卡龍看來,電動車計劃涉及諸多公司、消費者、政府部門,甚至鉛蓄電池等非人因素都是“行動者”,彼此共同構成了相互依存的行動者網絡。可以說,行動者網絡遵循廣義對稱性原則,打破了人與非人、有生命與無生命、個人與組織的區分。②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在吸收米歇爾·卡龍(Michel Callon)、約翰·勞(John Law)等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行動者網絡理論。拉圖爾認為,任何通過自身行為影響了事物的構建過程或改變了事物的狀態的行動者都可以被視為具有能動性③,行動者之間是一種相互認同、相互承認、相互依存又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主要依托網絡系統模型呈現行動者之間的動力關系,將“行動者”理解為實踐中的一切因素,沒有主動被動、主體客體之分。
行動者網絡理論原是一種分析科學技術與社會如何相互構建的理論方法,近來被廣泛應用于社會治理、社區治理、鄉村治理等研究領域,為其開闊了研究視野、創新了研究思路。“五社聯動”涉及了不同層次的行動者,并將社會公益慈善資源這一“典型”的非人要素納入了社區治理機制,因此,運用跨越自然與社會邊界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解析“五社聯動”的內在機理尤為合適。本文主要借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行動者”“網絡”“轉譯”等核心概念闡釋“五社聯動”的內涵本質,分析“五社聯動”的發展路徑。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域下,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社區志愿者、社會公益慈善資源既可以從人類行動者的層面理解,也可以從非人行動者的角度分析,其中既有“五社聯動”的核心行動者,亦有“五社聯動”的一般行動者。“網絡”是行動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動力關系,行動者網絡的建構及其穩定性則取決于“轉譯”。④所謂“轉譯”即核心行動者將自己的利益(興趣)轉換為其他行動者的利益(興趣),使其他行動者認可并參與行動者網絡的過程。⑤故此,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域下,“五社聯動”是一個關于社區治理的行動者網絡,其得以可能的關鍵在于核心行動者的“轉譯”。
二、 偶然抑或必然:“五社聯動”的生成路徑
(一) “三社有限”與“聯動乏力”
黨的十八大首次把“社區治理”的概念寫入綱領性文件之中,賦予社會力量以“主體性”,使其能同等參與社區治理。如此背景下,“三社聯動”得以產生。2013年,民政部、財政部在《關于加快推進社區社會工作服務的意見》中提出,“建立健全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聯動服務機制,探索建立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的新型社區服務管理機制”。隨后,一些地方政府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嘗試把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三個方面有效結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積累了大量的經驗。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明確要求加強“三社聯動”的機制建設。至此,“三社聯動”成了創新社區治理的重要路徑,在社區建設的多個領域內廣泛應用。
“三社聯動”是新時代社區治理取得的標志性成果。較之以往單一的社區建設,“三社聯動”吸納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無疑體現出了社區治理的社會化轉型;“三社聯動”引入社會工作這一蘊含著豐富實踐智慧的社會行動,則給社區治理開辟了專業化路徑。然而,“三社聯動”這樣一個具有社會化和專業化取向的社區治理機制依然有其局限性,面對新冠疫情更是如此。新冠疫情暴發后,社區成了疫情防控的基礎單元。在社區防疫過程中,“三社聯動”的社區治理機制雖然功績顯著,但此時社區組織力量不足、資源整合能力不夠、社會動員能力有限等問題逐漸顯露。具體而言,新冠疫情暴發時“三社聯動”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三社有限”。面對疫情,僅靠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三方聯動,著實能力有限。當時的核酸檢測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即便專業化的團隊、默契的合作,也難以實現“以一當十”的效果。加之,新冠病毒肆虐期間生活資源和醫療資源的欠缺,更是顯現出“三社聯動”的有限性。二是“聯動乏力”。“三社聯動”普遍存在“三社”之間的張力,行政主導的慣習仍在發揮作用,不乏“三社聯動”模式會出現“名聯而實不動”的現實問題。①這時的“三社聯動”也多是基于行政指令的“聯動”,并不是一種社會自主的“聯動”,在一定程度上有悖其“政社合作”的本質,所以“三社聯動”效果不佳。
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三社聯動”只是一個較為簡單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大量的社區志愿者和社區資源等非人行動者并沒有被吸納到這一行動者網絡之中。此外,“三社聯動”也只是一個松散的行動者網絡,其中行動者之間的聯系與互動較為機械,協同性不足。質言之,“三社聯動”這一行動者網絡的轉譯機制尚不成熟。故此,“三社聯動”中更多的資源需要被激活,更多的社會力量需要得到釋放,三社之間的協同與合作也需要更加緊密。
(二) 歷史發展中“五社聯動”的必然趨勢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背景下,由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社區志愿者和社會公益慈善資源構成的“五社聯動”機制日漸形成,其于各省的實踐均取得了卓越成效,且逐漸走進政策話語中。較之“三社聯動”,“五社聯動”中增加了社區志愿者和社會公益慈善資源。社區志愿者是社區公共性和社區自治精神的體現,將其納入“五社聯動”的范疇,有助于提高居民自助和互助能力,有利于提升社區自治水平。社會公益慈善資源雖看似是一個物質范疇,但物質交織著社會,同樣有其能動性與社會性。“五社聯動”將社會公益慈善資源納入其中,體現出了“物質資源”在社區治理中的重要性,是一種社區治理的“資源導向”,亦是對社區治理內涵的擴大化。此外,“五社聯動”的提出也是對社區治理“聯動機制”的優化與超越。“五社聯動”通過完善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治理的激勵政策,形成了服務激活社會的治理模式,實現了多元主體的有效聯動,構建出了社區治理的新格局。①因此,“五社聯動”的提出不僅是基層社會治理中行動者的增加,也體現出了行動者的緊密聯系,以及多元主體協同共治機制的形成。
雖然,新冠疫情催生了“五社聯動”,但筆者認為,新冠疫情僅是“五社聯動”產生的“催化劑”。從“三社聯動”到“五社聯動”并不是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偶然,而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當下社會問題的日漸增多、人際關系的日益復雜,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中需要吸納更多的行動者,并使其聯系緊密、相互補足、走向融合。質言之,“三社聯動”這一簡單、松散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需要逐步擴充行動者、完善聯動方式,從而走向“五社聯動”。早有學者指出,“三社聯動”可分為自治取向的“三社聯動”和共治取向的“三社聯動”,兩者殊途同歸,應逐漸走向融合。②亦有學者將“三社聯動”分為強調專業社會組織的“嵌入式三社聯動”和強調社區自組織的“內生式三社聯動”,兩者融合亦是發展趨勢。③可見,從“三社聯動”到“五社聯動”的躍升是吸納新的行動者進入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的過程,是創新“聯動”方式的過程,更是多種“三社聯動”模式取長補短、趨于融合的過程。
總之,從“三社聯動”到“五社聯動”的躍升是歷史必然,其不僅是社區志愿者和社會公益慈善資源的加入,更是一個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從簡單到復雜、從分散到協調的動態過程。其間,社區治理行動者的類型不斷增加,社區治理行動者的聯系不斷緊密,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的“轉譯”機制不斷完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的能力不斷增強。
三、 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五社聯動”的內涵解析
“五社聯動”正是一個不斷完善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其能夠吸納、整合新的要素參與社區治理,是新時期社區治理創新的有益探索。但“五社聯動”中的“五社”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五種社區治理主體或五類社區治理要素,其“聯動”也并非僅限于人類行動者之間的合作與整合。對此,下文將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從“五社”和“聯動”兩個方面解析其內涵要義。
(一) 社區治理行動者:“五社”的意涵
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域下,“五社聯動”中的“五社”可以被視為社區治理中的五種行動者,每一種社區治理行動者均遵循廣義對稱性原則,既包含人類行動者,也包括非人行動者。
第一,社區。在“五社聯動”中,社區既可以被視為作為治理主體的社區居委會,又兼具治理空間抑或治理平臺的意義,其均是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中的重要行動者。社區居委會屬于社區治理中的人類行動者,它是社區治理中的既有主體,能夠與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區基金會、駐地單位等社區治理的多元主體建立互動關系,共同服務社區居民、滿足社區需要、促進社區發展。同時,社區又是社區治理活動開展的特定空間,可以是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情感空間,更是一種公共領域。因此,社區亦可視為一種能夠給社區治理提供平臺和支撐的非人行動者。
第二,社會組織。我國社會組織一般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涉外社會組織,但“五社聯動”中的社會組織應是一個包容性概念,既包括專業性社會組織,也包括內生性社區社會組織,兩者皆為社區治理中的人類行動者,代表著組織化的社區治理力量。此外,社會組織亦可被視為一種非人行動者,既是一種協商共治的治理理念,也是一種居民社區參與的重要載體。總之,作為非人行動者的社會組織應是社區治理“社會性”的體現。
第三,社會工作。“五社聯動”中社會工作代表著專業化的社區治理行動者,能夠推動社區治理共同體建設。①作為人類行動者的社會工作主要是指專業社會工作機構、社會工作站和社會工作者。但我國社會工作存在發展不充分、分布不平衡的問題,多數地區專業社會工作機構數量有限、社會工作站暫未全面鋪開,且專業能力受限,難以與眾多社區“聯動”。②③因此,社會工作也可視為非人行動者,即作為“方法”的社會工作。①作為專業化的“方法”,社會工作具有一定的滲透性,能夠與基層工作相融合,能夠與其他社區治理行動者相銜接,形成獨具特色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區志愿者。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志愿者已成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通常意義上,社區志愿者是指以社區為范圍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參與社區服務與社區治理等活動,奉獻個人時間和資源的人。作為人類行動者的社區志愿者是社區治理中的重要主體,兼具個體化和組織化特征,既可以以個體化的形式參與社區治理,也可以以組織化的形式參與其中。但在“五社聯動”中,社區志愿者也并非僅僅涵蓋人類行動者的范疇,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弘揚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社區志愿精神,此即作為社區公共性的非人行動者。
第五,社會公益慈善資源。在疫情常態化背景下,社區治理對“資源”的需求愈加強烈,僅從主體的角度來理解“五社聯動”具有較大的局限性。因此,作為非人行動者的“社會公益慈善資源”在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中的作用逐漸顯現。但社會公益慈善資源并非僅是“物質資源”,社區可獲得、可支配,可用于回應社區需求、提供社區服務、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發展的一切社會資源都可以被視為“社會公益慈善資源”,包括物質、資金、技術、服務、社會關系等。此外,筆者認為,社會公益慈善資源同樣可以被定義為人類行動者,包含社區基金會、社會企業、社區駐地單位等志愿參與社區治理、志愿提供社會公益慈善資源的駐地組織機構。
由上觀之,“五社聯動”中的“五社”具有雙重意涵,既可以是作為人類行動者的社區治理主體,包括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社區志愿者、社區基金會等,也可以是作為非人行動者的社區治理要素,包括社區平臺、治理理念、方法技術、公共精神、慈善資源等。“五社聯動”正是一個“五社”多重意涵整合而成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
(二) 行動者的轉譯:“聯動”的要義
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的建構由網絡搭建與合作生產兩部分構成。②在“五社聯動”中“五社”的存在只是網絡搭建,而實現“合作生產”更重要的是“聯動”機制的建立。“五社聯動”正是異質行動者之間互動、聯結,最終實現網絡搭建、合作生產的過程,其間最大的困難在于厘清異質行動者之間的關系,使其合作成為可能。
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域下,異質行動者網絡形成的關鍵在于核心行動者的“轉譯”。因此,“五社聯動”正是通過“核心行動者的轉譯”整合“五社”的興趣與利益,使其互動、合作,最終形成穩定、有效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那么,何為“五社聯動”的“核心行動者”?核心行動者又如何“轉譯”呢?實則,人類行動者或非人行動者均可成為“五社聯動”的“核心行動者”。如果站位于前者,在社區中具有權威的組織機構就可以成為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中的核心行動者。譬如,社區黨組織能夠協調社區治理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形成政社合作、內外聯合、主體與要素相結合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如果站位于后者,那么社區環境、社區公共空間、社區公共需求等反映社區共同利益訴求的非人行動者同樣可以作為核心行動者,吸納其他行動者參與到“五社聯動”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之中,實現“五社”之間的通力合作和有效聯動。筆者認為,“五社聯動”中的核心行動者應是一個因地制宜且不斷變化的行動者,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優勢和資源,可以形成不同的核心行動者,不同階段“五社聯動”有著不同的任務目標,可以選擇不同的核心行動者。質言之,“五社聯動”這一行動者網絡中雖有核心行動者,但卻能做到“多中心治理”。
行動者網絡理論中“轉譯”的實踐邏輯,包括問題呈現、利益賦予、征召、動員等四個環節。①“五社聯動”這一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的構建亦需要遵循上述“轉譯”邏輯,或曰,“五社”得以“聯動”的關鍵在于轉譯實踐。②首先,“問題呈現”是“五社聯動”的前提。“五社聯動”中的每個行動者都有其自身目標,同時也會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遇到多種障礙,因此,需要核心行動者找到滿足多元行動者共同利益的“強制通行點”(OPP),以統合行動者的共同目標,實現行動者的“去異質性”。其次,利益賦予是“五社聯動”得以穩固的關鍵。“五社聯動”的構建需要依據“強制通行點”(OPP),明確社區治理行動者的權責邊界,并對其進行利益賦予,以充分調動各個行動者的參與積極性。再次,征召是“五社聯動”得以擴大的基礎。在這一環節,核心行動者需要利用多樣化方法策略強化“五社聯動”中各個行動者的共同體意識,并盡可能吸納更多行動者進入行動網絡中。最后,動員是“五社聯動”的最后保障。在此末端環節,“五社聯動”中的所有行動者都需要參與互動,搞好合作,各自發揮自身優勢,從而建立動態平衡的行動者網絡,實現目標。
總體而言,“五社聯動”是一個人類行動者與非人行動者同構而成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五社”不能僅限于從人類行動者的視角理解;“聯動”也不能受限于人類行動者的合作。“五社”之間無疑有“異質性”存在,定然會存有張力。但異質行動者也并非非此即彼,“五社聯動”需要通過轉譯實踐,整合異質行動者關系,形成異質行動者互構共生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此即“五社”得以“聯動”的要義所在。
四、 走向社區治理共同體:“五社聯動”的未來趨勢
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經歷從“單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區制”的轉型,而社區制又經歷了“社區服務” “社區建設”“社區治理”等三次轉變。在這樣一個政府逐漸讓渡社區權力,實現協同治理的過程中,“三社聯動”是既往破解社區治理困境的創新機制,而“五社聯動”則成了當下解決社區治理難題的重要途徑。那么,在未來“五社聯動”該走向何方?筆者認為,“五社聯動”應是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也是需要進一步完善與提升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其在本質上是一種社區治理共同體的雛形。打破自然與社會邊界,不斷補充有效的社區治理行動者、不斷創新聯動方式、不斷完善轉譯機制,最終成為一個“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區治理共同體是“五社聯動”的未來方向和發展趨勢。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黨的二十大均強調“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社區治理共同體則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礎單元和主要抓手,在實踐領域尤為重要。對于“何為社區治理共同體”這一基本命題,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將社區治理共同體視為一種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的有效機制,以助力厘清政府、市場、社會的責任邊界,重塑社區治理結構,提升社區治理效能①;二是將社區治理共同體視為一種新的社會整合機制,以回應社區治理個體化、碎片化以及居民參與不足等問題②。但上述兩者均是將社區治理共同體視為由人類行動者構成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前者強調多元合作與組織協同,后者強調人際互動和情感聯結。實則,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構建一個合乎現代社會需要的社區治理共同體應具有多重意蘊。筆者認為,社區治理共同體應是一個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其組成部分并非僅是社區居委會、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社區居民等人類行動者,作為非人行動者的社區治理“資源”“方法”“精神”均應納入社區治理共同體的范疇中。質言之,社區治理共同體并非僅是治理主體間的協同合作,資源的共享、方法的互補或共同體意識的形塑,一切有貢獻于社區治理的“行動者”均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故此,在未來的發展中,“五社聯動”不能僅限于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社區志愿者、社會公益慈善資源等既有的五類行動者,也應吸納新的行動者進入其中,并進一步完善“聯動”的形式和質量。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理解作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五社聯動”。
首先,作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五社聯動”是一種多元主體的協同。“三社聯動”可以被視為一種主體間的合作,其關鍵在于政社協同。同樣,主體間的分工與團結亦是“五社聯動”的關鍵所在。“五社聯動”的運行離不開國家行動者的介入與支持,政社合作是“五社聯動”的必要條件。但“五社聯動”應是一個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能夠為社區治理提供資源、技術以及其他諸多方面支持的社會企業、駐地單位,乃至作為社區治理“權力馬車”的社區物業管理公司、社區業委會均應被納入“五社聯動”之中。因此,“五社聯動”主要是將國家行動者、社會行動者、市場行動者以平等合作的身份,整合到社區行動者網絡中,從而形成一種“國家—市場—社會”協同共治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
其次,作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五社聯動”是一種多方資源的共享方式。社會事實在人類行動者和非人行動者所組成的行動者網絡中聯結生成。①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自然環境、科技設施以及動植物都是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一切物質資源、文化資源、社會關系資源,乃至信息資源都應被納入“五社聯動”這一社區治理共同體之中。可以說,“五社聯動”不能拋棄“非人行動者”,應遵循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廣義對稱性原則。作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五社聯動”不再僅是治理主體間的有效協同,也是社區治理資源的共享,更是社區治理成果的分享。質言之,作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五社聯動”應打破治理主體間邊界,形成一個多方資源整合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為社區善治的目標服務。
再次,作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五社聯動”是一種3PvnCCcZOXlmSFjvpJQdAFwGrgtd3I82Vosw2wAMBW8=多重方法的互補形式。在“五社聯動”這一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之中,既有專業行動者,又有志愿行動者;既有社區內生性行動者,又有外部嵌入性行動者。然而,各類行動者均有其優勢所在。譬如,社會工作機構是具有實踐智慧的專業力量②,其專業化的方法理論能夠應對社區治理中的諸多復雜問題;社區居委會熟識社區的基本情況,其土生化的方法依然是社區治理的有效手段。因此,“五社聯動”不僅是行動上的合作,而且需要方法上的相互學習和互為補充。筆者認為,“五社”均有其自身偏愛的方法和理念,但皆存在不合理和不完善之處,“五社聯動”也需要將“五社”的治理理念和方法技術相整合,形成一種“方法”上的聯動與互補,從而在“方法”層面構筑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
最后,作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五社聯動”是一種共同體意識的形塑機制。“五社聯動”是依托社區平臺內的各類行動者,通過合作網絡實現社區治理創新。但在“五社聯動”的“合作網絡”中最重要的是價值共識的形成,可以說,“五社”之間的“聯動”也是行動者社區意識的交融和共創。具體而言,“五社聯動”應是各類行動者確立合作共識,突破傳統的社會責任觀念,改變單向度輸血的意識,形成參與其中各方受益、共擔社會責任、共享社會成果的價值共識。③概言之,“五社聯動”就是一種“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體意識,“五社聯動”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就是社區歸屬感建立、社區責任感的塑造和社區凝聚力的形成。
總之,“五社聯動”是一個不斷完善、不斷提升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其從“三社聯動”這一簡單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發展而來,成為社區治理共同體這一包容、開放的社區治理(下轉第108頁)(上接第95頁)行動者網絡是未來發展趨勢。可以說,“五社聯動”不是一套固定不變的“標尺”,在基層社會治理中不能緊扣“五社”這五類社區治理行動者,而應形成多元治理、靈活聯動的理念。在中國有“四舍五入”之說,“五”代表著“多”,作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五社聯動”可能是諸多人類行動者的合作,可能是諸多非人行動者的結合,也可能是多元化的人類行動者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聯合。關于“五社聯動”的社區治理行動者網絡的構建,正是在確立社區治理共同目標的前提下,通過轉譯實踐“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做到社區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
(責任編輯:余風)
治理前沿
微信公眾號
① 方舒:《協同治理視角下“三社聯動”的實踐反思與理論重構》,《甘肅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
② 徐永祥、曹國慧:《“三社聯動”的歷史實踐與概念辨析》,《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③ 葉南、陳金城:《我國“三社聯動”的模式選擇與策略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0年第12期。
④ 徐選國、徐永祥:《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三社聯動”:內涵、機制及其實踐邏輯——基于深圳市H社區的探索》,《社會科學》2016年第7期。
⑤ 王學夢、李敏:《接納、嵌入與融合:“三社聯動”的內在機理與關系建構》,《治理研究》2018年第6期。
⑥ 田舒:《“三社聯動”:破解社區治理困境的創新機制》,《理論月刊》2016年第4期。
⑦ 安建增:《主觀有限理性何以影響社區治理創新——“三社聯動”機制建設的內在尺度》,《青海社會科學》2021年第12期。
⑧ 李文靜、時立榮:《“社會自主聯動”:“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機制的完善路徑》,《探索》2016年第3期。
⑨ 韓冬雪、李浩:《復合制結構:“聯合黨建”與“三社聯動”科學對接》,《理論探索》2017年第5期。
⑩ 原珂、趙建玲:《“五社”聯動助力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河南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11 王玥、毛佳欣:《“時間銀行”互助養老模式實現路徑——以“五社聯動”社區創新治理為背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12 吳高輝、文宇:《卷聯式培育:黨建引領鄉村共治的創新路徑及其發生邏輯——基于“五社聯動”的多案例研究》,《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23年第4期。
① M. Callon,“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in M. Callon, J. Law and A. Rip, ed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1986.
② M. Callon,“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 Law, eds.,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 Routledge, 1986.
③ 布魯諾·拉圖爾:《科學在行動:怎樣在社會中跟隨科學家和工程師》,劉文旋、鄭開譯,東方出版社,2005年,第185頁。
④ Bruno Latour,“Postmodern?No, Simply Amodern! Step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 No.1, 1990, p.4.
⑤ 羅峰、崔巖珠:《行動者轉譯偏差:政策執行何以陷入“困局”?——以S市托育政策執行為例》,《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
治理前沿
① 關爽:《城市社區治理中“三社聯動”的發展條件與支持體系建設——基于治理情境的分析》,《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① 徐家良、成麗姣:《“服務激活社會”——五社聯動驅動社會建設的運行模式》,《治理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劉振、侯利文:《“三社聯動”的縣域邏輯:內涵、機制與發展路徑——以宜興為例》,《現代城市研究》2018年第8期。
③ 陳偉東、吳嵐波:《從嵌入到融入:社區三社聯動發展趨勢研究》,《中州學刊》2019年第1期。
治理前沿
① 付釗:《社會工作參與社區治理共同體建構的實踐策略與行動邏輯——基于“情感—關系—行動”解釋框架的分析》,《新疆社會科學》2023年第3期。
② 陸杰華、黃鈺婷:《過渡性治理體制下社會工作嵌入社區的困境與應對策略——基于W市Z街道購買公共服務的質性研究》,《社會政策研究》2022年第4期。
③ 劉振:《走向實踐自覺:社工站的實踐困境與優化路徑——基于W鎮社工站實踐的思考》,《內蒙古社會科學》2024年第1期。
① 劉振:《作為“方法”的社會工作——關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工作的思考》,《內蒙古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② 許文文:《超越行動者網絡: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建構的本土路徑——基于社區養老場域的田野觀察》,《學習與實踐》2021年第3期。
治理前沿
① 賀建芹:《拉圖爾眼中的科學行動者》,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1頁。
② 文軍、陳雪婧:《社區協同治理中的轉譯實踐:模式、困境及其超越——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
① 任克強、胡鵬輝:《社會治理共同體視角下社區治理體系的建構》,《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② 楊發祥、閔兢:《社會理性視角下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何以可能?》,《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治理前沿
①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p.16-18.
② 張超:《從思維到行動:社會工作實踐智慧的生成機制》,《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
③ 張敏:《結構再造、秩序整合與價值共創: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路徑》,《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