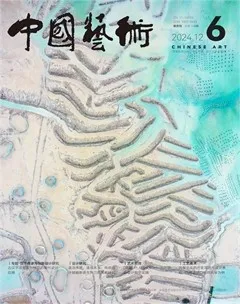版面重置:界格變化對清末民初蒙學讀本的影響








關鍵詞:清末民初 蒙學讀本 界格 版面
蒙學用書在清末民初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傳統的蒙學讀本從以識字為目的、以“三百千千”為主的訓蒙經典轉向了更多元化的內容。蒙學讀本在內容方面有所擴展的同時,其固定形制元素也在此時期開始松動。其中,界格的變化對整個版面空間的改變最大,對這一時期的蒙學讀本的版面設計產生重要影響。本文以界格為線索,考察清末民初這一時期蒙學讀本的版面變化。本文研究對象既包括以識字為目的的蒙學讀本,也包括其他具有開蒙性質的、適用于低年齡段兒童的教科書。
一、蒙學讀本的背景
從時代背景來看,在清末民初科舉制度廢除的前夕,新學制的規劃設置有了新的要求和內容。此外,西學知識的涌入、新式學堂的成立,促使適用新學制要求的蒙學用書大量出版。學制政策的變化帶來了多樣化的學習需求,需求的變化促進了新內容的生產,為蒙學用書的開發提供了契機。
從生產制作來看,印刷技術的提升革新了整個出版行業的發展模式,圖書生產制作的效率大規模提高。近代西方印刷技術傳入中國,改變了傳統書籍的制作模式,同時也催生了以內容制作、生產、發行于一體的近代出版機構。印刷生產效率的提高讓文本內容的傳播和復制變得更加便捷,為蒙學讀本提供了技術支持。
學制制度改革和印刷技術提升直接關系到新式蒙學讀本的生成和生產,這也給蒙學讀本的制作與設計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界格作為支撐蒙學讀本版面的骨架,為版面中的文本以及其他視覺元素的空間分配制定了框架。界格的變化也給蒙學讀本的版面設計帶來了創新。
二、界格在蒙學讀本中的變化
界格也稱“界行”“行線”“行欄”,是古籍版面中用來分割字行的界線,其來源最早可追溯到竹木簡書。界格作為傳統書籍形制中的標配元素,在清中期以前一直以穩定的形式出現在包括蒙學讀本在內的各類古籍中。清末以后,界格在書籍版面中的穩固性開始松動,在蒙學讀本中的變化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界格微變
界格作為傳統書籍頁面版框中的必備元素,存在于清末民初的蒙學讀本版面中,但已經發生細微的變化。這些變化具體表現在界格之間的欄間距變大,界格內開始安排其他的版面元素。
界格的欄間距變大,頁面內的行數就會減少,界格內的文本字體同時也會變大,與傳統蒙學讀本的密集型排列相比,字間距更顯寬綽,版面內容的清晰度增加,方便兒童識讀。從清晚期刊刻出版的《小學韻語》(羅澤南著)可明顯看出,隨著界格欄寬在蒙學讀本中變大的趨勢,文本字體也跟隨界格變大,格中大字規整且輪廓硬朗,讀之讓人賞心悅目。南洋公學于1901年在《蒙學課本》基礎上編著了《新訂蒙學課本》,其中的初編本內文部分的版面界格寬闊,給予了文本字體表現的空間。內容章節、例字詞語、例句解釋在界格中以高低不同的形式排列,這也體現出界格自身作為框架的容納特點,讓文本內容在其預先框定的范圍內展現出層級秩序和條理關系。(圖1、圖2)
此外,界格內還會安排文本之外的其他視覺元素,尤其是插圖。為了內容更好地展示,固定的界格形態被打破。清末民初的蒙學讀本中大量應用插圖,作為對文本內容進行輔助性解釋的插圖,根據需要放置在原屬于界格的空間,有的占據界格行高的三分之一,有的可能會占據半個頁面。1904年,由王亨統編撰、上海美華書館出版的《繪圖蒙學捷徑》中的界格內出現了許多插圖,其借用界格的邊線作為插圖的邊框,插圖基本固定在這個邊框內。插圖依賴界格內再分配的格而得到空間,這種“格內開格”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讓版面元素增多。上海美華書館不僅在中文鉛字發展的歷史中有一定的地位,同時也對蒙學讀本的版面設計發展做出了貢獻。從左往右橫排的英文和數字,從右到左、從上到下的豎排漢字,中英文排列、橫豎排共處于蒙學讀本版面,導致版式繁復雜亂,“格內開格”的方式改善了這一問題,這也是中西結合視角下對蒙學讀本版面設計調整的有趣嘗試與探索。(圖3)
(二)界格隱形
界格在蒙學讀本中隱形并不代表其劃分字行的功能消失,其雖隱卻在。界格隱形給予了版面內其他元素更多的展示空間。蒙學讀本中由界格框定的版面秩序被打破,新的版面秩序逐步形成。
界格作為構成傳統書籍版面的形制元素,具有功能上的“慣性”,在蒙學讀本中隱身,但其用于文本豎排、間隔字行的功能卻仍然存在。朱偉斌老師在其文章中曾提到:“雖然版面上不見了欄框線,但起規劃作用的欄線并沒有真正消失,在版面之下‘欄線’依然發揮著潛在影響。”界格長久地存在于中文傳統的版面中,消隱并不代表消滅,“欄線意識”在今天的中文版面設計中依然發揮重要作用。從供兒童閱讀的雜字書中可以看出,界格即使消失在版面中,但其作用于版面文本的框定作用和指引功能仍然存在。(圖4、圖5)在傳統中文版面中,從上到下、從右到左的閱讀習慣已是共識,界格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使版面設計更規范,建立版面設計的秩序。從傳統蒙學讀本中界格以實線形式存在到隱身,從支撐版面、劃分空間、間隔字行的多重作用轉變為只針對文本作閱讀指引可以看出,隱身后的界格功能雖在,但在版面中發揮的作用變小了。
在傳統蒙學讀本中,界格與其他版面元素都以固定的形式存在于頁面版框限定的空間中,使文本與圖像在預設好的框架體系內生成版面秩序。界格作為版面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文本和圖像起到了前置性的秩序規范作用。界格內規范文本,界格外與版框、版心形成統一秩序,組成具有固定樣式的版面風格。界格在蒙學讀本中隱身,其框定的版面結構被打破,使得原有框架體系下的秩序感消散,但文本字體與插圖的組合關系在版面中有了新的突破。新的版面秩序在界格隱身后開始出現并逐步形成,文本與插圖在版面中的位置關系不再受有形的實線界格的限制,版面元素進一步融合互動,版面空間更加開闊,蒙學讀本的版面設計更為自由。
(三)宮格應用
隨著界格在蒙學讀本中的變化,宮格逐漸被應用于蒙學讀本的版面設計中。作為劃分空間和支撐版面的框架,宮格可以容納文本和圖像,并給予圖文多樣的組合方式。宮格在版面中的應用給蒙學讀本帶來了具有“中式網格”風貌的版面樣式。
尤其是以字課圖說為代表的識字類蒙學讀本,其版框內部已呈現出明顯的視覺變化,內頁去掉了間隔字行的界格,變為六宮大方格的版面形式。六宮和九宮較早地被應用于中國傳統古籍版面中,如明代萬歷年間刊刻的《本草綱目》,其展示插圖的部分內頁就使用了六宮形式。從功能上來看,宮格的版面形式更易用,鄰近的宮格可以根據版面需要進行自由組合,每個宮格也能拆分成多個小格,以滿足內容編排的需要。宮格具有靈活變化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現代版面設計中的網格系統。(圖6、圖7、圖8)網格系統設計起源于瑞士,在20世紀60年代隨國際主義風格的興起而大規模流行,成為影響世界平面設計的重要力量。網格系統的理性與嚴謹的設計形式受到眾多設計師的青睞,被應用于世界各地的平面出版中,成為版面設計的標準參考范式。宮格在蒙學讀本版面中的應用與西方現代設計中的網格系統雖存在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但在版面空間的合理分割、圖文的排版設計上具有相似性。
宮格與網格在蒙學讀本版面中的呈現并非始于近代,這種不同于西方網格系統設計的理念邏輯來源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且始終貫徹落實在中國的文化實體中,尤其是以漢字為代表的書寫體系以及以漢字輸出的文化媒介中。劉暢老師曾詳細地探討了網格在漢字書寫以及古籍版式中的應用,她認為網格系統一直存在于漢字相關的平面設計傳統中,并構成了中文信息設計的基本框架。蒙學內容的層級關系在這種網格化的版面安排中被更有秩序感地體現出來,內容指向更為明確。不論是六宮、九宮或是十二宮,宮格作為版面的框架結構存在,輔助視覺元素在格內或鄰近格間進行組合與變化。彪蒙書室于1918年出版的《蒙學識字字課圖說》的版面以十二宮格作為框架結構,根據具體需要劃分內頁版面空間,既有均勻的分欄和分格,又有格內空間的靈活變化。宮格數量增多,也會增加版面層次,豐富視覺效果。(圖9)
(四)去界格化
蒙學讀本版面的去界格化讓版面中的視覺元素有了更多的表現空間,增加了視覺元素之間的互動性,圖像在版面中的比重得到提升,便于文字的閱讀。
蒙學讀本中的去界格化不僅增加了圖像的比重,也有利于文字的閱讀,更改變了書籍印刷中的字體字形字號。去界格化后的版面設計不再考慮提前置入的界格框架,整個版框內或相鄰的頁面都可以根據版面需要進行統一安排。去界格化的嘗試擴大了版面內視覺元素的活動空間,蒙學讀本版面內容發生了從以文本為主到文圖并存的變化,插圖在版面中的比重開始提高。插圖數量增加、尺寸增大,圖像語言開始在蒙學讀本中發揮主動性。同時,去掉界格也給予文本字體更好的表現方式,內文用字開始注重標準書寫,大號例字增多,從而引起了社會大眾對字體字形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傳統書法中的藝術形態出現在蒙學讀本中。此外,字體樣式與字號大小的變化與書籍的出版印刷方式的轉變有密切關聯。隨著西方石版和鉛活版印刷技術的傳人,傳統雕版印刷技術逐漸衰落,蒙學讀本中的字體細節由棱角分明的木板刀刻走向了充滿標準書寫的楷體風格。隨后,石版印刷被活版印刷取代,具備多種字號以及不同字形款式的鉛活版印刷登上歷史舞臺。
蒙學讀本去界格化的嘗試促進了版面內容之間的互動,增強了版面元素的節奏,給蒙學讀本的版面帶來了新活力,版面空間的整體編排也呈現出不同于傳統蒙學讀本的藝術形態。首先,文本與插圖在版面中的位置不再被格線分割和固定,文圖配合的自由度更加靈活,文圖關聯性進一步加深,圖文的編排方式也突破了受界格限制時的單一樣式。其次,文本和圖像通過變化與組合的形式,在蒙學讀本的版面空間中形成新的視覺節奏,文字的排列更加注重在整個版框區域內的視覺效果,既有均勻規整的豎向排列,也有頂末端不一致的動感排列。最后,版面空間的處理也進行了創新,每一頁根據具體的內容安排文本和圖像的位置,因勢賦形,把文本和圖像作為整體考慮,給蒙學讀本帶來了新的版面氛圍。正是在去界格化的過程中,蒙學讀本的版面設計逐漸呈現出新的視覺效果。(圖10、圖11、圖12)
清末民初,界格在蒙學讀本中發生的以上四個變化并不是按照排列的先后順序發生,基本是同時進行的。界格在蒙學讀本中的種種變化,既受到當時政策制度的影響,也與印刷制作技術的革新有關。界格從構成版面固定的形制元素到在版面中徹底消失,也是技術發展和審美進步的體現。界格的變化瓦解了傳統蒙學讀本版面框架的固有樣式,促進了蒙學讀本版面視覺設計的發展。
三、界格變化對蒙學讀本的影響
界格在蒙學讀本中的變化,給蒙學讀本的版面空間分布、虛實處理等帶來諸多改變,多樣化的探索讓蒙學讀本的版面設計朝更加生動的方向發展,催生了蒙學讀本版面新樣式的發展。
(一)由密到疏,由滿到空
清末民初的蒙學讀本的版面布局與傳統蒙學讀本存在顯著差異,界格對蒙學讀本中版面元素的排列組合變化起到關鍵作用。蒙學讀本版面呈現出視覺元素排列由緊密到寬松,版面氛圍由緊繃到活躍的變化。界格中的文字也從密集的不透氣式排版轉為寬字距的排版形式。當然,在傳統蒙學讀本中,文本內容的密集式排列與書籍本身的制作方式有關,因其在木板上雕刻,為了節省材料、人力、物力,所以會讓版面密集擠壓。印刷技術的發展是促使蒙學讀本版面由密到疏變化的原因之一,使文本不再局限于傳統木板雕刻的界格之中。
界格的變化讓蒙學版面內容的排列從密集走向寬松,寬松的排版給版面留出多余的空間,適當的留白讓蒙學讀本更具閱讀舒適性,這也是清末民初蒙學讀本版面變化的顯著特點之一。有界格的蒙學讀本版面對空白的處理主要體現在文本內容的間隔上,行欄內的字距、詞距一般會留出足夠的空間,讓版面有適當的喘息空間。蒙學讀本內頁在宮格限定的尺寸內置入文本和圖像,無論是大號例字、小字解釋,還是圖像,都按照一定的秩序排列在規定的位置。去界格化后的蒙學讀本版面像是一個存在虛擬空白背景的畫面,文本和圖像作為有形的實體置入其中,與背景進行有效融合,使得有形的實體與空白的虛體共同構成了蒙學讀本的版面空間。
(二)重布黑白,重建秩序
版面中的黑白既是字面意義上的對顏色的形容,也是對版面空間中有形有色的實體與無形無色的虛體的描述。界格是蒙學讀本版面設計的關鍵元素,對蒙學讀本版面視覺效果的營造發揮著重要作用。重布黑白是指對版面空間中虛體和實體的位置關系的處理方式。傳統蒙學讀本中的版面通過界格均勻分布,中間為版心,版框上方為天頭、下方為地腳,文本在界格內以單行或雙行的形式從上到下、從右到左密集排列,線形排列的文本、組成版面的形制元素與虛體空間共同構成了版面虛白實黑的視覺分布。從《寄傲山房塾課新增幼學故事瓊林》《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最新國文教科書》這三本不同的蒙學讀本內頁可以看出,其版面的黑白分布跟隨界格在頁面的變化而變化,去掉界格后,其他視覺元素的比例得以放大,版面視覺的黑白分布被打散,從固定均勻的線形排列走向了多元自由的不規則排布。(圖13、圖14、圖15、圖16)
界格的變化為蒙學讀本版面帶來新秩序,傳統蒙學讀本的版面秩序因界格的變化而松動,新的版面秩序使圖文聯系更緊密,內容的層級關系也更清晰,版面元素的安排更有條理,版面內容的組合方式更多樣化。此外,從功能設計層面考慮,蒙學讀本的使用者是低年齡段兒童,設計者對讀本內容的安排注重循序漸進,其寬闊的版面、優美的大字、精美的插圖既適合閱讀也有助于兒童的學習使用。
清末民初的蒙學讀本對版面設計的探索呈現出一定的主動性,嘗試打破原有的框架秩序。不論是宮格形式還是去掉界格的版面設計形式,都具有科學和理性的設計思考。同時,設計者對版面空間進行靈活處理,使其具有一定的藝術鑒賞性。
四、結語
界格是構成傳統書籍版面的重要元素,作為版框內部的骨架支撐,界格的變化對整個版面都會產生影響。清末民初的蒙學讀本版面設計發生了巨大變化,本文通過對界格在蒙學讀本中的變化進行考察發現,界格是促成蒙學讀本版面從傳統固定的形制走向具有豐富版面視覺效果的關鍵。界格的變化給予了版面內其他元素如字體、插圖等更多的靈活的展示空間。同時,界格的變化也重置了蒙學讀本的版面秩序,使得版面布局由緊到松,視覺節奏感增強,實體與虛體的結合更為自由。
另外,通過界格在蒙學讀本中的多種變化可以看到一種主動的設計探索和嘗試。如宮格在蒙學讀本中的應用,其分割空間、容納圖文的設計邏輯來源于本土文化,早于且不同于西方的網格系統設計,這也是值得關注的地方。
總而言之,因界格的變化,清末民初蒙學讀本的版面固有樣式松動,給蒙學讀本的發展帶來新的面貌,促進新的版面設計秩序形成。界格為當時的蒙學讀本版面設計帶來變化,也對后續的蒙學用書及教科書產生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