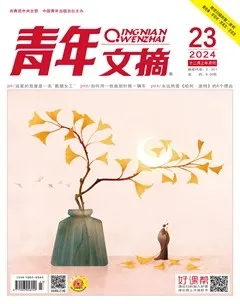韓江:避開痛苦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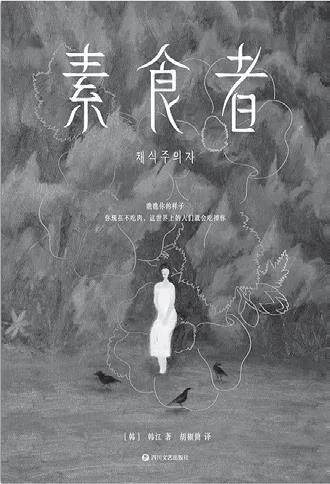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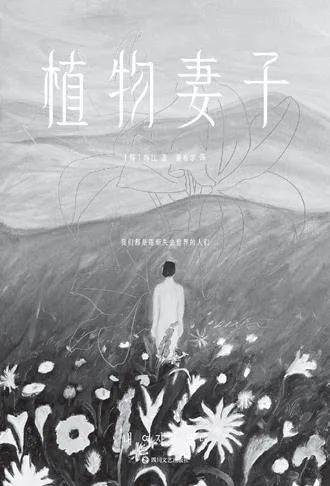

北京時間10月10日, 韓國作家韓江成為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也是韓國乃至亞洲首位獲得諾獎的女性作家。就在8 年前,韓江憑借小說《素食者》擊敗曾經的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奧爾罕·帕慕克以及因“那不勒斯四部曲”風靡全球的埃萊娜·費蘭特等知名作家,成為亞洲首位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的作家。
正如諾獎頒獎詞所言,韓江“用強烈的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傷,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在她的作品中,有聚焦女性和邊緣人的生活的《素食者》《植物妻子》等,以及書寫歷史創傷的三部曲《少年來了》《白》和《不做告別》,這兩類主題都是基于長久以來對個人和集體的暴力的探討。但也正如作者說的那樣,“盡管存在暴力,但人類擁有感受他人痛苦的力量,以及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能力。只要我們的內心擁有能夠提出疑問的力量,即使看似微弱,希望也不會消失,始終都會存在于我們之間。”
“作家之家”
韓江成為作家可謂水到渠成,她的家庭堪稱“作家之家”。父親韓勝源是韓國著名作家,兩位哥哥也都從事文學工作,丈夫洪榮熙是大學教授兼文學評論家。在家人眼里,洪榮熙評價妻子是“每一個句子都使出渾身解數,對自己異常嚴格,具有激烈文學追求的人”,而父親則評價女兒早已超越了自己。
在韓江的記憶里,小時候的自己除了書本什么都沒有,整天沉浸在讀書之中,青春期以后開始細細琢磨自己所讀的書的含義,后來自然而然開始有了寫作的欲望。韓江打過一個比方——寫作就像是點燃火柴,在一旁凝視火苗燃燒,直至熄滅。“也許這就是小說所能做的一切。就在這凝視的瞬間,向人類和人生提問。”人類的暴力能達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瘋狂,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別人……她決定用寫書來向這個世界提出問題和求解問題。
從延世大學畢業后, 韓江先后投身詩歌和小說創作。1993年,她在雜志上發表了詩歌;1995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麗水之戀》;1998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玄鹿》。1999年,韓江憑借中篇小說《童佛》拿到了韓國小說文學獎。進入新千年,韓江又陸續創作了《素食者》《少年來了》等代表作,獲獎不斷,在世界文壇嶄露頭角。
韓江從小就擁有很好的文學感覺,對生與死、人生與痛苦有著超出同齡作家的深刻理解,這不同程度地受到父親韓勝源的影響,尤其是韓勝源小說中對佛教的理解。2005年韓江以《蒙古斑》獲得韓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項之一李箱文學獎,當時她年僅35歲。有意思的是,韓勝源在1988年也獲得過這一獎項。
家庭對創作的影響可謂方方面面。韓江的小說幾乎完美平衡了暢銷性與藝術性,甚至可以說是近年來諾獎獲獎作品里尤其“流暢好讀”的。當被記者問道“為何作品具有強烈繪畫特性” 時, 韓江回憶說,小姑是美術大學畢業生,自己小時候經常當小姑的繪畫模特,她也常用畫家繪畫來比喻自己的創作。
避開痛苦是不可能的
韓江第一本被翻譯成英文的小說《素食者》2004年就已在韓國出版,還曾被拍成同名電影。小說通過描寫一名女性對韓國守舊傳統的叛逆和抵抗,探索人內心抑壓的瘋狂與傷痕。
韓江曾提及《素食者》的靈感來自韓國20世紀30年代被稱作“ 天才”“ 鬼才” 的作家李箱筆記中的一句話:“ 我認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在獲得諾獎后,韓江表示《素食者》重點講述主角想成為植物,遠離人間爭逐,以拯救自己, 擺脫人性黑暗面。“通過這么極端的故事,我感到我可以提問……最難的人性問題。”她說,自己的作品皆非大眾化或商業化,而是“質問人間的復雜格斗”。“琢磨這些問題后,我最近想到,過日子該著眼于人性中明亮而具有尊嚴的一面。”
盡管如此,對暴力和痛苦的關照始終存在于韓江的作品里,這或許應該追溯到她的生活經歷:韓江的出生地正是韓國最痛苦的歷史事件——1980年光州慘案的發生地,《少年來了》即以光州“5·18”運動為背景,通過還原少年東浩在抗爭中的經歷,向讀者真實再現了一段韓國現代史。她今年出版的小說《人類行為》同樣以光州暴亂為背景,再現了動蕩時代背景下的人物命運。
從時代記憶到個人經歷,韓江感受到,受傷之人、痛苦中的人想要恢復正常生活,不是指單純回到過去的生活,而是通過對痛苦經歷的審視繼而全新復活才對。韓江的腳踝部分曾因燒傷嚴重,很長時間患部沒有任何感覺,當終于有了痛覺時,醫生告訴韓江,這種感覺是她的腳即將康復的信號。韓江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漸漸認識到了痛苦的本質。
當被問到“您的小說作品中總是伴有痛苦,痛苦對您意味著什么呢”時,韓江回答:“我的永不休止的作業就是,如何接受在這個世界上總有個地方有痛苦人生這一事實。就算我現在活得很安穩和平,但總不能說這世界和平吧。我要摸索著寫下那些不起眼的、軟弱的人們為什么在痛苦之中做出那樣的選擇。避開痛苦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把痛苦當成生活的一部分來對待,除此之外毫無辦法。”
(資料來源:《北京青年報》、澎湃新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