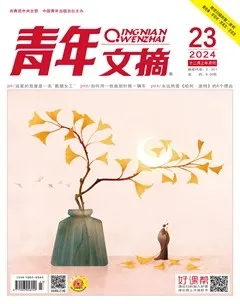寫作就是“看到什么,就寫什么”

作為一個副刊編輯,我發現很多來稿都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寫得很不具體。
比如,不久前我收到一篇稿件,標題叫作《泥瓦工》。對于這個內容我是感興趣的,懷著很大的期待去看,結果很失望。作者對于泥瓦工的了解不比我多,一大篇文章,要么是寫站在自家樓上遠遠看著對面燈火通明的工地,要么就是與泥瓦工泛泛的幾句交談。總之是特別概括,特別抽象,特別不具體。
抽象寫作更需要功力,寫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種金句,需要“撮其要、刪其繁、比方出來”的本事,非大師不能有。而普通寫作者能做的就是具體,并不是說要你去采訪,但你必須有具體的感受。毛不易有首歌《無名的人》,就是對一個群體的具體感受,我覺得送給泥瓦工也可以。
且來看看歌詞:“我是這路上沒名字的人,我沒有新聞,沒有人評論……我是離開小鎮上的人,是哭笑著吃過飯的人,是趕路的人,是養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無聲。我不過想親手觸摸彎過腰的每一刻,留下的濕透的腳印是不是值得,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
詞作者用“沒名字”“沒有新聞,沒有人評論”來表述默默無聞,用“親手觸摸彎過腰的每一刻”寫辛勞,用“哭笑著吃過飯的人、趕路的人、養家的人”,建立一條通道,讓這些“無名的人”和大眾產生更深的鏈接。雖然生存狀況有所不同,但說到底,大家都是同類。
接下來,場景被繼續推近:“你來自于南方的村落,來自粗糙的雙手。你站在樓宇的縫隙,可你沒有退縮。”這一句有一種喚醒的效果,讓我想起在摩天大樓上擦玻璃的蜘蛛人,他們背井離鄉,在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市縫隙里謀生,他們的表情里可能會有畏縮,但他們是真正的勇者。
而對回家過年的期盼是這勇敢的根源:“我來自于北方的春天,來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別的路口,溫暖每個日落。當家鄉入冬的時候,列車到站以后……在熟悉的街頭,有人會用所有的溫柔,喊出你的名字。”
你看這是多么動人的具體場景,都能看到主人公聽到被呼喚名字回眸時的喜悅。能寫得如此具體,是因為作者對于“無名的人”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張愛玲是金句王者,她能把抽象的東西寫得很好,但她觸動我的,是那些具體的感知。比如《半生緣》里,曼璐和祝鴻才做局,囚禁了曼楨。為了封母親的嘴,曼璐給了母親一筆錢。張愛玲寫母親摸到了曼璐給的那筆錢。一般人最多能寫到她摸到錢就改主意了,但是張愛玲把這筆錢寫得非常具體:“那種八成舊的鈔票,摸上去是溫軟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疊。錢這樣東西,確是有一種微妙的力量。”
這真是神來之筆,神在“溫軟”“厚墩墩”“方方的”“八成舊”這幾個詞。這筆錢實質就是顧太太賣曼楨的錢,如果是新的硬的,就非常刺眼刺心,良心會被折磨。但它是舊的,溫軟的,就體現出錢可親的一面,更讓人不能抗拒。張愛玲把一個母親出賣女兒的心理過渡寫得水到渠成。
想要寫得好,就要“看到什么,就寫什么”。這其實不容易做到。首先你要看到,同樣是看泥瓦工,有人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身影,有人卻能看到他們的來路和遠方,看到他們內心的曲曲折折。
其次你可能看到了,但是不敢寫。小時候受到的作文訓練或是閱讀不夠充分,人會不由自主地循著套路寫。所以母親就永遠溫柔善良,勤勞節儉,父親就永遠沉默寡言,堅韌如山,說是張三李四的父母都可以。但是你看魯迅寫他父親,在大雪天莫名其妙要他背書,彌留之際想要阻止他呼喊自己,這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就算朱自清寫他爸也是:“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一個無力者的努力讓人動容。
做人最重要是誠實,寫作也一樣。
(李金鋒摘自2024年8月20日《新安晚報》,阿悠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