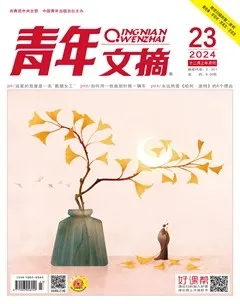袁枚:清代“網紅美食家”

袁枚是清代“乾嘉三大家”之一,是與紀曉嵐共稱“南袁北紀”之人,是9 歲讀《離騷》、24 歲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的天才少年。但他最被后人稱道的身份,是一名高級吃貨。
袁枚愛吃,也會吃。他在八珍玉食中嘗出人間百態,寫下“味甜自悅口,然甜過則令人嘔;味苦自螫口,然微苦恰耐人思”。這何止是美食的境界,還可以讀出做人的境界。
袁枚的一生可以辭官為界,分為鮮明的上下半場。前半生,他與傳統讀書人科考入仕的經歷相似,只是,年少時的袁枚要幸運得多。
袁枚自小是神童,文學天賦極高。乾隆元年(1736年),21歲的袁枚被舉薦到京城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博學鴻詞科乃科舉制度之外的臨時性考試,目的是選拔能文之士。作為當時年齡最小的與試者,袁枚名滿京城。
24歲那年,袁枚入翰林院,成為一名庶吉士。此時的他意氣風發,對未來充滿了抱負和期待。然而,這位才氣逼人的年輕人在三年后的散館考試中卻僅獲得了下等的成績。這意味著他的政治履歷大概率一直遠離中央,在各地方流轉任官了。
27歲的袁枚開始了外放到地方為官的生涯,先后在江蘇溧水、江浦、沭陽當了7年縣令。他為官剛正不阿,明斷曲直,身體力行地為當地群眾做實事,謀福利。離開溧水的時候,當地百姓為他縫制了一件萬民衣。
但具有名士風度、天性熱愛自由的袁枚,并不適應官場上嚴格的等級制度以及瑣碎的潛規則。與官場格格不入的他,對日復一日的官僚生活難以忍受。
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天,33歲的袁枚在江蘇江寧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以三百金的價格買下破敗的隨園。隨園本為曹寅在1706年前后所建,也就是《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原型,曹家被抄家后,園子歸江寧織造隋赫德所有,所以又名“隋園”。袁枚將其買下后,易名為“隨園”。這年秋天,袁枚托病辭官,后雖短暫再入仕,但不久再次辭官,從此隨園成了袁枚的固定居所和精神樂園。
袁枚頗具商業頭腦,在清朝時就做起了“販賣生活方式”的生意。他將荒蕪的隨園重新修繕,不僅修樓建亭,搭橋作舟,也栽花種竹,還將私家園林拆掉外墻,對公眾開放。他在門口放一對牌匾,上面寫著“ 放鶴去尋三島客, 任人來看四時花”。一時間, 隨園聲名大噪,前來玩賞的游客絡繹不絕,也常有文人騷客來此雅集,閑置房屋租金暴漲,而他本人廣收門徒和學費,潤筆費也水漲船高。
解決了錢的問題,袁枚就開始耐心鉆研自己的樂趣——吃。據傳,袁枚每次去朋友家做客,如果遇到心儀的美食,一定要讓自家的廚師去拜師學藝。他也喜歡結交天下名廚,南京名廚王小余廚藝高超,袁枚多次誠心拜訪,結果就是王小余拒絕了當御廚的機會,安心到隨園掌廚。
在食物面前,袁枚像一名虔誠的教徒。一天,袁枚到戶部蔣侍郎家做客,席上珍饈羅列,主人突然問:“你吃過我做的豆腐嗎?”袁枚搖頭,主人于是穿上圍裙,親自為他烹制一道芙蓉豆腐。豆腐清白如雪,花色艷似云霞,吃起來清嫩鮮美,令人嘆為觀止。袁枚急忙請教做法。主人秘不肯傳,笑道:“古人不為五斗米折腰,你肯為豆腐三折腰,我就告訴你。”袁枚當即離席三鞠躬,大笑道:“我今為豆腐折腰矣!”主人只好傾囊相授秘方了。
看遍天下山水、嘗遍天下美食是袁枚下半生的寫照。在外人看來,活得率性而灑脫的他,每日只需在隨園吟詩烹飪,便能日進斗金,坐收“睡后收入”。然而,他在瀟灑的皮相下,也不忘借食諷今,很多詩篇中,他那厭世而不避世的態度躍然于紙上。比如這首《雞》:
養雞縱雞食,
雞肥乃烹之。
主人計固佳,
不可與雞知。
養雞人縱容雞整日狂吃,只是為了早日將雞養肥,而被養肥的雞命運也就走向了終結。所以養雞人的心思,是不能讓雞知道的。這首詩表面上寫雞與主人的關系,實際上卻暗諷封建王朝的統治者與勞動人民的關系,表達了袁枚對統治階層的不滿,寄托了對普羅大眾的同情。
后來,袁枚將自己在餐桌上的見聞寫成一本《隨園食單》。他從才子、官員徹底變成了現代人心目中的美食網紅,擁有了煙火人間的瀟灑。
與懷才不遇或是自認天下無道而被迫歸隱的傳統文士不同,袁枚主動選擇了離開仕宦系統,他也不打算做遠離塵俗的清高隱士。相反,袁枚熱衷于世俗生活,隨園是他的世俗家園,他在那里網羅四海名流,享受財富與聲名,誠如他在一副對聯中所言:“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懶;難成仙佛,為愛文章又戀花。”
對于袁枚來說,研究美食比研究詩文更加重要,這是他“無官一身輕”后最悠然自得的愛好。他在隨園中踐行了賈寶玉在大觀園里也沒能實現的“富貴閑人”的人生哲學:
葛嶺花開二月天,游人來往說神仙。老夫心與游人異,不羨神仙羨少年。
(摘自《環球人物》,蝌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