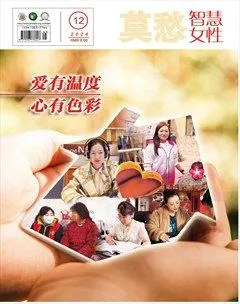娘家菜
云淡天高,陽光熱烈,屋前壩上母親種下的金針菜一路歡暢,開出燦爛的黃花,悠悠地在微風中招搖。母親倚在門口,出神地望著,喃喃地說:“今朝金針旺相,正好多曬一點,你小妹歡喜吃呢。”母親口中的金針菜,就是黃花菜,又稱作萱草花。
汪曾祺曾在《慢煮生活》中提到:“萱花未盡開時摘下,陰干,我們那里叫作金針,北方叫作黃花菜。我小時候討厭黃花菜,覺得淡而無味。到了北方,學做打鹵面,才知道缺這玩意還不行。”
母親每年都會曬制金針菜,實際上,我并不愛吃這個,總感覺嚼在嘴里爛唧唧的,像嚼一塊破抹布。母親曬好了金針菜,挑天氣晴好的周末,打電話叫小妹回來拿。小妹就從南京開車往返兩百多公里,捎帶著大包小包的禮物,回娘家來拿金針菜。一路上電話不斷,開心得不得了,一到家就纏著母親,嘰嘰喳喳講個沒完。
要說小妹有多愛吃金針菜,我是不信的,因為我清楚記得,小妹是頂歡喜吃肉的。小時候,為搶肉吃,這家伙沒少跟我干仗。每每此時,母親總會說,你是哥哥,讓著她罷。于是,碗里的肉就漸漸少了,一塊兩塊……我急忙夾了往嘴里送。
老家過年的時候,大年三十晚上,有一道菜是雷打不動的,方言叫作“如意菜”,恰似大雜燴,里面有金針菜、腌咸菜等等。這道菜里,其他菜品依具體情況可作適當增減,但水芹菜、豆芽菜、金針菜這三種是萬萬不可缺少的。老輩人說,水芹菜中空外直,寓意“路路通”;豆芽菜形似“如意”,便以其取名;至于這金針菜,恰好是金黃的,取“富麗堂皇”之意。
幼年的我覺得,前兩種菜的解釋倒也合理,唯獨這金針菜的說法經不起推敲。家鄉地里的胡蘿卜也是黃色的,又甜又脆,不知要比這軟塌塌的金針菜好到哪里去了。我曾“抗議”多次,試圖說服母親用胡蘿卜絲代替金針菜在如意菜中的地位。可惜,胡蘿卜絲是放了,金針菜依舊還在。
不知長輩為何如此堅持對金針菜的偏愛,直到長大后,我讀到關于萱草的詩句,才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古時候,母親居所的門前往往種有萱草,人們雅稱母親居所為萱堂,于是萱堂也代稱母親。孟郊在《游子》詩中曾寫道:“萱草生堂階,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我想,既然萱草、金針、黃花菜是同一種事物。如果我沒有牽強附會,那這金針菜就像是圖騰一般的存在,代表母親對子女的愛和牽掛,也代表母親向自己的母親致敬,其中有無盡的追憶、感恩和期許。
有一種思念叫團圓,有一種溫暖叫回娘家。小妹出嫁了,嫁到的是婆家,回到的是娘家。她在婆家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在娘家,她又變回了父母的孩子。這里是生她養她的故土,童年時代的風土人情,是記憶深處最溫暖的部分,所以她樂意回來,金針菜,只是一個由頭罷了。
味蕾有記憶,美食有鄉愁。金針菜,就是娘家菜,吃的不僅是那口家鄉味,更是娘家人對女兒的眷顧。
編輯 許宵雪 18507354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