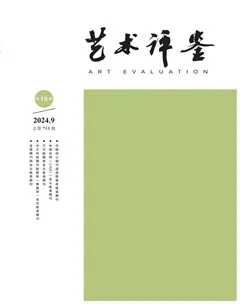中國懸疑題材網劇的創新路徑與審美嬗變
【摘 要】辛爽執導的《漫長的季節》是一部生活懸疑題材的國產網劇。該劇以外在的喜劇形式為載體,在內容上突破了我國以往懸疑題材國產劇的創作模式,構建了一個以普通小人物為主體的敘述框架,展現了底層群體對于生命價值與階層敘事的悲劇內核,進而觸及集體英雄主義與“人—動物”背后審美價值的終極追尋。通過對網劇《漫長的季節》在內容創新、傳播策略、影像制作等方面的探索及其審美嬗變的深入研究,文章旨在探討懸疑題材網劇如何通過與新媒體的融合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關鍵詞】《漫長的季節》" 懸疑題材" 國產網劇" 審美嬗變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24)18-0171-06
電視劇作為電視藝術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樣式,其真實性和生活化的美學特征在封閉、窄小的電視、移動電子設備屏幕內已然得到了最貼切的表達。然而,這段磨合期卻經歷了一段相當漫長的時光。因此,在5G技術背景下,現有的電視劇形態將依據技術的發展作出相應的調整,網劇形態就是其中之一。無論是內容創新還是形式創新抑或是平臺創新,對于電視劇而言,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網劇的敘事空間延展到了熒幕之外,這意味著電視劇延展形態的網劇將依據技術的發展、受眾的審美趣味作出相應的調整,在美學形態方面也會出現新的要求。
2023年,由辛爽導演的懸疑題材網劇《漫長的季節》受到網絡熱評。該劇扎根于現實,讓觀眾在劇中沉浸式審視著劇中的人物和時代的背影。同時,它又超越現實,在深層意義上揭示了人生與命運的真相。它講述了一段漫長的人生及一場漫長的告別,是關于人在現代精神場域下頻頻回眸的自我救贖、與命運和解的“活著”的故事。導演通過“輕喜懸疑”“生活懸疑”“亦悲亦暖”的獨特風格,以高質量的審美表達和頗具深度的內容呈現,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創作突破。該劇的成功推出,不僅革新了我國傳統電視劇的類型化創作模式,也基于中國互聯網環境和移動觀影情境進行了深度的本土化改編。它以喜劇化的創作風格、結構化的敘事方式以及細膩真摯的情感表達,獲得了高度贊譽。
一、本體創新:在朦朧隱喻的影劇相融影像中實現互動傳播
在當代影視市場中,“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往往成為衡量劇作優劣的一個原則。在《漫長的季節》的形式與風格方面,辛爽導演采用“悲劇的喜劇化處理”方式、生命倫理與情感救贖路線,將目光聚焦于我國底層群體,通過中老年角色的敘述視角,不僅深入探討生死的哲學命題,更嘗試呈現底層群體的情感波動與生活掙扎,從而構建出一個層次豐富、引人深思的敘事結構。
(一)制作層面:影劇相融打造視覺奇觀
制作周期的長短不一定是作品上市成功與否的關鍵,但一定是體現創作者態度的表達。《漫長的季節》只有12集,從劇本策劃研發到正式開播卻歷時3年時間完成。在富有時代氣息的環境塑造、飽有文化積淀的方言使用、多維的視角講述中,將電影的影像質感與網劇的故事結合,打造出視覺奇觀,展現出一種精致的視覺體驗。
首先,環境在網劇中作為空間敘事的載體,決定著影片的風格。巴赫金曾經說過,文藝“永遠都能在當地為自己找到直觀可見的依據”。《漫長的季節》中關于東北地方環境的描寫中蘊含著東北地區的地方經驗、文化想象、集體記憶。自然環境中的秋天的玉米地和冬天的雪,人文景觀中的學校、電影院、夜總會、樺鋼廠房等,這些景觀符號化的集合,表達出創作者的情動指向,傳遞出劇中人物的精神圖式。
其次,地方方言沉淀著地方文化,承載著地域信息,在精神上更貼近地方群眾的質樸情感,讓人們產生現場感、參與感和認同感。《漫長的季節》中東北方言的使用,符合東北人豪爽耿直的性格特征,這既能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又能以其真實、新奇、幽默、親和的獨特魅力,增強作品的感染力。如劇中“你是真的彪啊”“瞅啥呀”“扯犢子”等臺詞,不僅彰顯了本劇平民化特色,而且價值判斷在小人物身上得到了合理的注腳。
最后,《漫長的季節》通過使用全知視角和有限制的人稱敘事視角講故事,使本劇關于“善與惡”的思考更加立體。在劇中全知視角的敘述中,如寄人籬下的沈墨被大爺毒打時,大娘的無動于衷;傅衛軍的姐弟情深等,使劇中的人物更加飽滿。同時,劇中王響、龔彪、馬德勝等個體人物視角與全知視角相互補充,增強了觀眾觀劇的驚異感。
(二)傳播層面:樹立全媒體思維,網劇受眾雙向黏合
多樣化和創新性是雙向的,它不僅僅體現在制作層面,在互聯網傳播上也尤為突出。《漫長的季節》打破了以往“流水線制作”劇集、互聯網鋪天蓋地宣傳的模式,主要利用觀眾看劇過程中產生的“自來水”劇迷進行跨平臺、多渠道的傳播,通過他們對網劇的多方位解讀設置社會議題,借助互聯網的開放性、互動性為該劇營造熱度。
其一,雙向二度創作實現多重熱度。《漫長的季節》是根據于小千創作的小說《凜冬之刃》改編的。移動互聯網的便捷性使眾多觀眾在看劇前就已經閱讀過文本,這為網劇的傳播打下了良好的受眾基礎。網劇以一種通俗化的敘事影像實現了小說的二次傳播與二度創作。另外,《漫長的季節》播出后,引發觀眾自發式的解讀和猜測,這些解讀和猜測通過視頻彈幕或者短視頻的形式投放市場,形成了一個觀眾自主創作的熱點圈。同時,互聯網的自由與靈活性讓該劇在長度上不再拘泥于傳統的45分鐘,而是以講好故事為目的。
其二,互動性是《漫長的季節》傳播中的一大特征。全媒體的宣傳模式、觀眾自主性的參與盤活了該劇。一方面,自媒體生產者借助該劇本身的熱度提高受眾對自己的關注度,并在這過程中擁有了接受者與創作者的雙重屬性。另一方面,短視頻流量會部分回流到騰訊平臺上去觀看該劇,并在短視頻平臺上和其他受眾進行狂歡式互動。短視頻平臺用戶選擇的自主性、視頻長度的微小化、情節主題的集中性、觀點解讀的多元表達可以更好地滿足受眾的需要。
(三)主題意蘊:理性內容感性轉化,主題闡發外淺內深
主題是故事的靈魂,是貫穿全劇的主線,是網劇的內涵和思想。人物是主題呈現最重要的載體。《漫長的季節》通過鮮活的多人形象不斷回眸俯瞰歷史深淵,他們既有知大義、慷慨豪邁的英雄面貌,又有小人物式的平凡側面。以王響、龔彪、馬德勝等小人物為代表的底層工人形象,生動展現了當時社會大眾的精神狀態與生活方式,拉近了角色與觀眾的情感距離。它使觀眾剝離理性走向感性,深切感受其中每一個人物的生存狀態。時代的變換與更迭在宏觀的視角下拉高了網劇對日常生活的平淺化敘事,拉扯出一個東北地區真實多面的表達,展現出一種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個體與時代的生存哲學。例如,劇中龔彪最后中了彩票后宿命般地墜入河流意外死亡,馬德勝腦梗后的神奇般破案,王響倒在玉米地的開放式結局等,展現了時代發展和社會巨變中人物的悲劇性。
另外,主題意蘊在言已盡而意無窮的影像中直指人心。在《漫長的季節》中,運鏡速度的變化不僅再現了生活,也將導演對主體的感知不著痕跡地揉碎在其中。首先,光影的變化是洞察人物命運的關鍵。在視覺要素的展現中,光線的散聚表達了人物的真實境遇,如劇中王陽和沈墨約會的畫面,暖色調的散射光表達出兩人內心純潔溫暖、彼此愛戀的情感狀態。其次,道具的符號化表達,恰如其分地彰顯了敘事的合理性和宿命性。例如,紅色毛衣隱喻著王響作為父親對尋找兒子死亡真相的執念,以及案件本身所承載的悲苦情感。最后,嫻熟的轉場技術使這部劇視覺要素的豐富性得以展開。其中,出入畫轉場、特寫鏡頭轉場是劇中典型的兩種轉場方式。
二、審美表達:在精深合力的沉浸式探索中達成善樂體驗
數字技術的到來,為影視創作者們提供了平臺渠道支撐,并在審美偏好、審美感知和審美體驗方面開辟了一個新的視野。數字技術不僅為藝術創作帶來了無限可能,還為網劇拓展了電視劇視覺藝術的新視角和創新突破口。網劇《漫長的季節》在講述故事時,將時間設定在秋天,采用的是暖色調高亮度的視覺感知。該作品打破了以往觀眾對東北嚴寒蕭瑟的刻板印象,通過獨具匠心的鏡頭語言、自然流暢的轉場,結合音樂和色彩的敘事功能,呈現出生活化的臺詞與情節、細膩而飽滿的情感表達,從而構建出一種具有“生活懸疑”特質的全新美學風格。懸疑題材的網劇以獨特的觀賞體驗和深刻的價值內涵,在審美效果上給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
(一)審美偏好:深度表達與精度表達的合力
審美文化是在當代消費文化影像下形成的審美形式。審美偏好則是一個時代經濟、文化、政治等綜合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當代中國審美文化的發展已超越傳統藝術的界限。技術進步與大眾傳媒的廣泛滲透,催生了大眾藝術生產方式從個人手工向機械復制的轉型。同時,大眾讀寫能力的提升、多樣化的藝術傳播途徑、流行時尚與亞文化群體間的關系等因素交織,構成了復雜的審美景觀,這顯然已無法在傳統的個體創造力或單一案例分析范式中得到有效解釋。
《漫長的季節》在審美偏好上力求精度與深度的結合。精度在于為觀眾奉獻一個扎實的好故事,深度在于讓人們了解故事、參與故事后思考生命的意義。王陽的“向前走,別回頭”,簡單的六個字臺詞在故事的結尾起到了一種升華主題的作用。另外,網劇在輕松幽默的喜劇外殼下包裹著悲劇內核。它試圖在過去二十年的社會情、理、法中探討父子親情、愛情、友情等社會議題。對于導演辛爽而言,“離地半米”是他在作品里追求的感覺。
《漫長的季節》這部懸疑題材網劇最為可貴之處,在于它在深刻的主題之外還有詩意與音樂。在電視劇的結尾,王陽和沈墨兩個人在鐵軌上讀詩,與王響跟王北坐在一起讀詩的場景是一次呼應。在那一刻,王陽與王響找到了彼此理解的方式。《漫長的季節》作為現實主義作品,切中了“現實主義+類型化”的網劇脈搏。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的基礎上,它充分尊重觀眾新的審美需求,在深度與精度的共同表達中,升華出故事本原之上的人生感以及復雜人性中的共鳴與共情。
(二)審美感知:沉浸式體驗的深層探索
借助空間與歷史的稟賦,得以觀照東北地域中不同內涵的文化心理圖式。而從以情感波動為核心的生活譜系中,又能夠透視出在不同文化心理統攝下人們尋覓本真的路徑與面對現實情境的方式。“敘事的關鍵在于那些付諸行動與思考的人物主角,而不是圍繞某個明確終點所展 開的行動系列。”《漫長的季節》以橫跨18年的一樁懸案作為切入口,在案件偵破過程中,庖丁解牛般地細致剖析與三線并進的敘事節奏相輔相成,極大地增強了目標受眾的情緒體驗。劇中融入的社會生活相關敘事元素,為該劇在內容深度和廣度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創作空間。通過融入更多與大眾生活、社會情境相關的敘事元素,懸疑類題材電視劇不僅調動了公眾當下的觀看情緒,更在類型表達的背后彰顯了深層的社會價值與行為導向。
王響和兒子王陽的重要矛盾是代際鴻溝。王響在尋找兇手的過程中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不理解造成的心中的遺憾,這也是形成整個故事的主要動機,它在感知層面引領觀眾達成沉浸式體驗。在視覺上,《漫長的季節》采用了富有時代感的敘事場景、光線強弱、色彩明暗等技術手段;在聽覺上,它采用了契合受眾獵奇心理、刺激性聲音以豐富受眾的視聽感官,用隱喻的符號價值、新奇的敘事結構吸引受眾的審美欲求。
在《漫長的季節》中,對于王陽的特寫鏡頭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學校遇到沈墨的場景中;第二次是在殺人之后;第三次是在1997年,王陽在家里洗頭時開心地照著鏡子的場景。三次特寫鏡頭的轉場都別出心裁,讓觀眾感受到時間的連續性和王陽的個人體驗。懸念的層層設定使受眾不自覺地進入影像敘事之中,參與劇情的解密推理過程,并在生活中延續這種故事的快感,討論思考劇中人物的命運走向、導演的創作意圖,以及年代轉場的敘事意味等。無論是想象還是猜測,無論是思考還是語言表達,在這一過程中都能夠催生出接受者個人獨特的美學體驗,滿足了觀眾的參與體驗感,激發了他們的想象力與判斷力,滿足了他們進行二度創作的熱情。
(三)審美體驗:至善原則的撕裂,快樂原則的實現
懸疑劇的核心特色在于對人物個性的細膩描寫、典型形象的精準塑造以及社會生活環境的深刻再現。它通過影像對社會情境的真實還原,映射出復雜的社會議題,引發大眾的深層反思與情感共鳴,從而凸顯出主流社會價值觀的表達。馬克思曾說:“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突出人物個性描寫,重視對于社會生活環境的生動刻畫。”影像符號在網劇敘事場景的搭建中,不僅是人物心理的展現,更是隱喻性的呈現。這一手段在懸疑類現實主義題材劇中尤為關鍵。通過影像符號,人物形象得以深刻塑造,故事亦能折射出社會語境。
《漫長的季節》以東北方言的形式呈現著最直接的喜劇效果,但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的結局,卻處處彰顯著殘酷的現實——中年喪子、喪妻的王響,愛而不得的龔彪,年少時遭猥褻的沈墨等形形色色的人,無論是犯過錯誤還是沒犯過錯誤的人最后都走向了死亡。悲與喜的對比,理性思考起來是如此的殘忍,但它在導演的融合下卻彰顯出浪漫和詩意。這或許源于辛爽對生死的思考。“悲喜是人生的常態,其實你甚至可以跳出來看,這里說的不只是東北,是人類共通的東西。講的是命運,命運一定包含悲和喜。每個人看到的東西都不一樣,不代表死了就是悲。死亡是一個很中性的東西,它對每個人都公平,每個人都要經歷。”
非線性的敘事結構結合多維敘事視角,輔以巧妙的懸念設置、反轉情節及蒙太奇剪輯技術,實現了敘事的陌生化。該劇在平民視角的喜怒哀樂中,展現出創作者強烈的平民意識與人文關懷。影像中傳達了創作者對平民生活及其困惑的理解,揭示了一個既充滿幸福喜悅又滲透著殘忍的現實世界以及復雜詭譎的人性宇宙。該劇在人本善與快樂的淺層視像中,探索深層的社會議題,展現多元的人性,最終實現真善美的高度融合。
三、瓶頸與突破:在懸疑敘述慣性中的審美迷失與價值重構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近年來,在已經接近飽和的網劇市場中,網絡懸疑劇成為創作者競爭追逐的題材。《白夜追兇》《無證之罪》《隱秘的角落》《沉沒的真相》《漫長的季節》等出圈作品是懸疑類網劇的典型佳作。盡管如此,懸疑類網劇在創作的過程中依然面臨著眾多瓶頸與挑戰。因此,懸疑網劇既要克服敘事慣性帶來的審美疲勞,又要突破市場導向的局限,在優化節奏的同時,注重作品的人文價值。
(一)固化與創新轉型:懸疑元素的重復應用與多樣化重塑
隨著懸疑網劇作品越來越豐富,類型雜糅成為其必不可少的選擇,如《隱秘的角落》就因青少年犯罪問題引發社會關注。《漫長的季節》被定位為生活懸疑,采用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近實際的原則,融入對社會、歷史、人性的多面思考。但在進行題材創新的同時,難免慢慢走向相互模仿的同質化道路。例如,在《漫長的季節》和《隱秘的角落》中,最后兇手的呈現都摒棄了傳統中窮兇極惡的人物形象,而是讓兇手回歸到生活中的普通人,有著善意與單純,有著生活的無奈與迷茫。比如朱朝陽、沈墨,他們在劇中的形象都是生活中的“好青年”。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形成了觀劇時的驚異感,但在“找兇手”的情節、“好人被逼無奈成為壞人”的人物設定等元素上,創作者要避免走向同質化。創作者需要在懸疑元素的應用中尋求創新路徑,通過多樣化的視角和豐富的角色設定來重新激發觀眾的興趣,從而實現敘事模式的革新與突破。
(二)節奏調和:敘事節奏的優化與觀眾體驗的提升
懸疑劇的敘事節奏直接影響觀眾的觀看體驗。隨著媒介融合的發展,碎片化傳播成為社會中的主流現象。網劇在創作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種“集數短”的趨向,比如12集。但仍然存在“注水”的問題,導致觀眾的實際感受與期待產生偏差。
《漫長的季節》并不完美,比如在節奏、敘事效率上還有待提高。在敘事結構方面,前面九集基本是慢節奏,最后三集是快節奏,給觀眾難免有頭重腳輕的視覺感官。三條敘事線索中環環相扣是值得贊賞的,但劇情設定上前面略顯拖沓。值得一提的是,它作為一部網絡電視劇在將懸疑劇向現實主義進行延伸方面做了新的嘗試。它并不僅僅是一部簡單的尋找殺人兇手的電視劇,而是超越了傳統現實主義懸疑題材電視劇的創作范式,立足于“中老年底層”主體的身份與視角,從時代、情感與階層的邊緣位置出發,力圖構建出具有多重邊緣屬性的深層話語體系。因此,在敘事節奏的處理上,創作者需要精細調整,在緊張與舒緩之間尋找平衡,使觀眾既能享受敘事推進帶來的快感,也能在角色的情感世界中找到共鳴。這不僅提升了作品的觀賞性,也增強了觀眾對劇情的持續關注。
(三)市場與藝術的平衡:從單向追求商業效益到深耕人文價值
隨著技術的發展,市場導向在懸疑網劇的創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鮑德里亞在其《象征交換與死亡》一書中曾提出擬像理論,并指出商業利益的衡量是創造虛擬世界的主導因素。網絡懸疑劇在藝術接受的過程中,往往會在潛移默化中陷入算法文化,一方面逐漸被網劇的劇集所吸引,另一方面則甘愿淪為算法文化的附庸,墜入商業利益之網。而《漫長的季節》并沒有啟用超一線明星,而是專注于人物的真實塑造與復雜人性的展現。例如,王響、沈墨、王陽不再是非黑即白的白描式書寫,而是每一個人物身上都展現其行為動機。沈墨被朋友背叛,最終她走上了復仇與救贖的道路。因此,用好的劇情和人物塑造《漫長的季節》既達到了追求商業利益的訴求,也為觀眾呈現了一個生動的故事。優秀的懸疑劇也應當在商業效益與人文關懷間達成平衡,不僅滿足觀眾的娛樂需求,也要注重文化內涵的傳遞和社會議題的探討。通過賦予作品深層次的情感與思想意涵,使其在獲得市場認可的同時,展現更為廣闊的藝術價值與文化意義。
《漫長的季節》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藝術手法,通過劇中小人物的個體經驗與東北地區小城鎮的現代化進程,透視時代前進過程中的歷史傷痛。“文化藝術不是簡單地為時代做一個記錄,它是通過你對人物的塑造、主題的開掘以及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探索,特別是對人性的穿透,表現出人性的真善美、假惡丑。”文藝工作者在當代能夠不忘初心,深刻認識到任何類型的劇種本質上都是在講人的故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這不僅需要深厚的人文功底,而且需要遠大的藝術理想。要努力用網劇的多元書寫去承載百姓的喜怒哀樂,將更多蘊含社會意義和深刻人性的主題融入作品中,實現寓教于樂的功能。要想使網劇創作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與歷史的沉淀,創作者需要根植于人民情懷之中,緊密結合時代發展的宏大背景,創作出有思想、有筋骨、有溫度的藝術作品。
四、結語
《漫長的季節》作為中國網絡懸疑劇的典型代表,展現了在內容創新和審美表達上的重要突破。該劇通過將懸疑元素與生活化敘述相結合,打破了傳統懸疑題材對線性敘述和單一人物形象的依賴,賦予觀眾豐富的觀看體驗。該劇不僅在敘述手段上借助多視角、非線性時間軸等技術手段,深化了人物與情節之間的復雜關系,更通過地域文化的表達,體現了對特定歷史背景下社會變遷的思索。它通過對小人物命運的刻畫,揭示了洪流時代個體的掙扎與救贖,并以隱喻和象征手法賦予其深刻的社會意蘊。作品通過幽默與悲劇交織的敘事手法,不僅滿足了觀眾的娛樂需求,更在情感層面引發觀眾對現實生活的共鳴與反思。劇中視覺語言和方言的運用,以及全知視角與限知視角的交替,使得作品在藝術性和觀賞性上達到了新的高度。該劇不僅展現了網劇在數字技術支撐下的創新潛力,還通過其對社會、歷史和個體命運的深刻繪畫,凸顯了懸疑劇在新時代背景下的獨特藝術價值和文化意義,為后續網劇的創作提供了優秀的范本。
參考文獻:
[1]范雪嬌.為國產懸疑劇的表達提供更多可能[N].中國藝術報,2023-05-24(004).
[2]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劉晉汝,王秋實.迷茫的樂觀與悵惘的堅定:城鄉敘事中的東北印象——以《鄉村愛情》系列和《漫長的季節》為例[J].當代電視,2023(09):4-11.
[4][美]羅伯特·斯科爾斯,[美]詹姆斯·費倫,[美]羅伯特·凱洛格.敘事的本質[M].于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5]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導演辛爽:時間的痕跡[DB/OL].澎湃新聞,2023-05-16.
[7]謝飛,尹鴻.電影需要進入人性層面:對話謝飛[J].當代電影,2019(11):2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