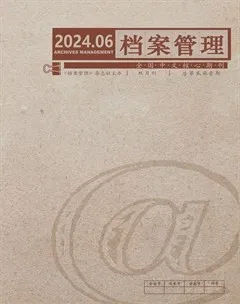底層敘事視域下口述檔案與非虛構文學書寫互現
摘 要:本文探討了底層敘事視域下口述檔案與非虛構文學書寫的互現現象。底層敘事視域強調了來自社會邊緣和弱勢群體的敘述,為那些在主流話語中被邊緣化的聲音提供了平臺。口述檔案作為收集和儲存這些聲音的工具和文本,正與非虛構文學書寫產生了互動關系。這種互現促進了底層敘事的多元化和豐富性,并為社會正義和歷史記憶的追尋提供了重要的資源。通過對口述檔案和非虛構文學書寫的互現現象的分析,本文為研究者和實踐者提供了對于底層群體敘述的更深入理解,同時強調了口述檔案與非虛構文學書寫的相互關系對于文化多樣性和平等性的重要性。
關鍵詞:檔案;底層敘事;口述檔案;非虛構文學;報告文學;口述歷史;社會記憶;文化傳承
底層敘事視域的背景可以回溯到20世紀70年代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提出了關注邊緣群體和邊緣化經驗的觀點。底層敘事視域試圖通過傾聽邊緣化聲音和關注個體經驗來改變話語權的分配。底層敘事視域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文化多樣性和社會正義的視角。它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范圍,使得那些被邊緣化的個體和社群的敘述得以被聽見和賦予意義。通過關注底層敘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社會中的權力結構、身份認同和社會正義的問題。[1]同時,底層敘事視域也促進了文化批評的多元化,使更多的文學和文化作品得以被探究和理解。
底層敘事視域還在于它為社會變革和歷史記憶的追尋提供了重要的資源。通過呈現被邊緣化群體和個體的敘述,我們能夠更全面地認識歷史事件、社會轉型和個體經驗。[2]這有助于建立公正的歷史敘述和社會記憶,在于它關注被邊緣化群體的聲音和經驗,擴大了文學研究和文化批評的范圍,并為社會多樣性、正義和歷史記憶的追尋提供了有益的視角和方法。它鼓勵我們聽取和關注那些在主流話語中往往被忽視的聲音,推動社會變革和文化創新的發展。
1 口述檔案的概念和構建
口述檔案是一種記錄口述歷史的文獻資源,通過口述訪談的方式收集和保存個體或社群的口述記憶。[3-5]它是以口述者自身的經歷、見解和回憶為基礎,通過采訪、錄音、錄像等形式進行收集和記錄,以保存和傳承口述者的故事、經歷和知識。口述檔案和非虛構文學書寫有助于保留和傳承重要的歷史記憶。通過記錄個人經歷、親歷者的見證和口述歷史,這些文獻記錄了那些在現有歷史敘述中被忽視或邊緣化的故事和聲音。它們提供了對歷史事件和社會發展的新視角,從而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理解過去和現在。口述檔案具有口述性、主觀性、多樣性、反思性、公正與倡導等特點。
口述性:口述檔案主要通過口述訪談的方式進行收集,口述者親自講述自己的故事和經歷。這種直接的口述性質使得口述檔案能夠保留個體或社群的獨特的觀點、情感和記憶,呈現真實且生動的歷史圖景。
主觀性:口述檔案呈現的是口述者的主觀經驗和個人觀點,與官方歷史和正式檔案存在一定的差異。口述者能夠提供與現有歷史記錄不同的細節、情感和背景信息。這種主觀性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元的歷史視角和理解。
多樣性:口述檔案涵蓋了各種不同背景和經歷的口述者,包括不同性別、種族、地域、社會階層等。這使得口述檔案具有多樣性,能夠呈現各種不同人群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承。
反思性:口述檔案可以反映時間的推移和社會變遷對個體和社群的影響。通過口述者對過去的回顧和評述,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歷史事件的影響和演變,并對社會變革的過程進行反思和分析。
公正與倡導:口述檔案可以提供被邊緣化和忽視的群體機會,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經歷,并促進社會公正和民主價值的傳播。它為那些在官方歷史中沒有被充分記錄和代表的個體和社群發聲,增強他們的存在感和認同感。
通過口述檔案的收集和研究,人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歷史和文化,呈現多元的視角和聲音,同時推動公正和包容的社會發展。它在研究歷史、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等領域具有重要的價值和影響力。
2 文學敘述中的口述檔案應用與底層視角
在文學敘述中,口述檔案和底層視角可以被運用來增添真實感和情感共鳴,并呈現出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經驗和故事。通過引入口述檔案和底層視角,作家可以更真實地描繪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情境、心理狀態和存在感。這樣的敘述方式有助于賦予文學作品更強烈的感受力,使讀者更能夠理解和共情社會底層群體的掙扎、歡樂、希望和悲傷。傳統的文學敘事往往以主流社會的角度來呈現,而口述檔案和底層視角提供了一個機會,從被邊緣化和忽視的群體角度來重新詮釋和講述故事。這有助于挑戰主流權威敘事,探索不同社會層面的多元經驗和觀點。
引入口述檔案和底層視角可以給予那些在主流文學作品中常常被忽視的群體更多的代表性和存在感。通過展現社會底層群體的故事,文學作品可以提供一個更廣泛、更多元的視野,展示不同生活經歷和文化背景的獨特性。例如蘇珊·奧爾琳的《親愛的圖書館》,這本非虛構作品以圖書館火災與洛杉磯市立圖書館的歷史為背景,深入探討了圖書館的文化意義和社會作用。作者利用口述檔案,采訪了廣泛的人物,包括圖書館工作人員、志愿者和社區居民,其中一些人來自底層群體。通過他們的口述,作者揭示了他們對圖書館的熱愛和依賴,以及圖書館對社會底層群體提供的教育、機會和凝聚力。
口述檔案通常與口述傳統相關聯,通過記錄口頭傳統和個人經歷將歷史和文化傳承下來。在文學敘事中,作家可以借助口述檔案的元素來傳遞歷史記憶、民間故事和文化傳統,以保持文化的連續性和傳承。
通過與底層群體的對話和故事,作家可以傳達他們的聲音和體驗,使讀者更深入地理解他們的生活條件、情感與掙扎。這樣的敘述方式使文學作品更具鮮活性、包容性和觸動力,深入挖掘人類的普遍情感和共鳴。但使用口述檔案和底層視角時,作家需要謹慎處理,確保對底層群體的故事和經歷持尊重態度,并避免將其當作單一視角或陳述的工具。通過精心挑選和處理口述檔案的內容,并與其他敘事技巧和文學元素相結合,作家可以創造出令人難以忘懷和引人入勝的文學作品,呈現底層群體的故事和觀點。
在非虛構文學中,底層敘事視域是一種重要的應用手法,它關注社會中被邊緣化、被忽略的群體和他們的經歷。[6]這個視角讓讀者深入了解社會中存在的結構性不平衡現象,并以個人的視角展示他們的生活經歷和奮斗歷程。
《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書中的“蟻族”,是對“大學畢業生聚居群體”的典型概括。該群體高知、弱小、聚居,是繼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勢群體:他們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有的甚至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他們平均月收入低于兩千元,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合同;他們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九成屬于“80后”一代;他們主要聚居于城鄉接合部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弱小強者”,是鮮為人知的龐大群體。這本書是非虛構文學首次全方位披露底層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狀態、社會心理和精神訴求。“蟻族”構成一代人與一個時代的鏡像——折射出“80后”在中國社會急速轉型背景下的特定經歷、形象表征和思想狀態,他們切身感受著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對各種現實矛盾與困境有著直接而敏銳的感觸,因此也最深刻地體驗著這個時代共有的焦慮與期盼。
張培忠的《永遠在路上》,運用多維視角、立體的層面,通過報告文學、書信、日記、口述歷史、文學評論、現場圖片、筆記圖表、實物展示等進行聚焦、透視,全方位展示一位中國農民的一生。本書所呈現的是半個世紀前后的中國農村,特別是一位中國農民在山村、在底層,為了躲避貧困、解決溫飽而奔波不息、艱難前行的生活情狀,以及此前此后所經歷的滄桑巨變。這是一位農民的人生檔案,是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也是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
這些案例表明,底層敘事視域在非虛構文學中具有強大的力量,可以揭示相對弱勢群體的處境,并引起社會的關注和思考。它通過個人故事和觀察展示此類人群生活的不易,為那些無聲者發聲,推動社會變革和意識覺醒。這些作品不僅提供了見證歷史的渠道,也為普通人的經歷提供了平臺,讓我們理解并反思社會的問題和挑戰。
3 口述檔案與非虛構文學書寫的互現現象
口述檔案和非虛構文學書寫有一些共同特征和目標,盡管它們在形式和方法上可能有所不同。
口述檔案和非虛構文學書寫都致力于記錄真實的經歷和事件,以呈現事實和真相。它們都試圖通過事實性的敘述來傳達經歷者的真實感受和觀點。這兩種形式都關注人性和個人的生活經歷。它們試圖深入了解人類的情感、心理和行為,以揭示個人在特定環境和時代中的經歷和掙扎。口述檔案和非虛構文學書寫都試圖關注社會問題和百姓生活現象,以引起讀者的關注和社會的反思。 [7]它們旨在推動社會變革、呼吁關注百姓,并引發對社會問題的討論和行動。口述檔案和非虛構文學書寫都使用各種敘述技巧來吸引讀者,并以有力而引人入勝的方式呈現真實的經歷。這可能包括故事化的敘述、人物塑造、場景描寫和對話重現。這兩種形式都以個體的視角和經歷為基礎,試圖通過個體的故事來展示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它們通過深入了解和描繪個體的生活來傳達更大的社會意義。
梁鴻的《梁莊三部曲》是一部記錄中國底層人物生動故事的非虛構文學作品,其中就包含著許多精彩的口述檔案實例[8]。在《中國在梁莊》中,作者重點寫了五奶奶孫子的死亡,由此帶出了五奶奶內心的巨大傷痛以及環境破壞的問題。《出梁莊記》中,作者遠赴青島,采訪了五奶奶的兒子,讓我們看到五奶奶兒子的工作環境、生存狀態及孩子死亡所帶來的傷害。在《梁莊十年》中,作者寫了一位在村莊里面日常生活的五奶奶,這位五奶奶,樂觀、幽默、堅強。梁鴻的敘述隨著人物的訪談交流,變得輕松、自然,即使如第二章“丟失的女兒”這一相對沉重的話題,她也是用閑聊的方式來進入,非虛構文學中口述檔案的元素加入,使作者消融于其中,成為梁莊的一部分,梁莊里每個人的死亡、出生、離家、回家,都是她自己家人的事情,她懷著無限的依戀、擔心和深愛去書寫。
梁鴻寫出了鄉村在時代的變遷中,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梁莊人也在時代轉型背景下迎來各自截然不同的命運,張香葉、燕子、春靜、吳桂蘭、明太爺、五奶奶、少年陽陽等人物漸次出場。跟隨作者筆觸,我們看到懷揣夢想干事業的萬敏的困境,北漂梁安終返故鄉,也看到打工者學軍移民西班牙……他們的人生結局荒誕離奇,看似在意料之外卻又處于情理之中,讓人唏噓不已,閱讀起來,每每欲罷不能。《梁莊三部曲》寫出了時間長河中人類命運的渺小與復雜。
《梁莊三部曲》中的口述檔案記錄了底層人物的生活經歷,層層遞進、情節跌宕,既真實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底層人群的生存現狀,也賦予了小說文本更為深刻和真實的人性價值。口述檔案作為非虛構文學書寫的素材和資源具有巨大的價值。它們提供了真實故事和見證,讓非虛構作家能夠深入了解個人經歷和社會問題,并通過這些素材創作出引人入勝、有影響力的作品。
4 互現現象對底層敘事的多元化和社會意義的探討
口述檔案和非虛構文學書寫之間的互相影響和互現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對社會和文化有深遠的影響。
口述檔案記錄了個人和群體的經歷和故事,起到了保存歷史和記憶的作用。然而,這些檔案通常以口述形式存在,容易受時間、遺忘和挑戰的威脅。非虛構文學書寫通過將口述檔案轉化為可讀的作品,將這些珍貴的歷史和記憶永久地保存下來,讓后人能夠了解、學習和反思過去的經歷。口述檔案通常是直接記錄當事人的口頭表達。然而,這種形式可能受到語言、文化、社會背景等方面的限制。非虛構文學書寫通過藝術化的敘述和創作,賦予口述檔案更廣闊的表達空間,并能夠更好地展現講述者的聲音和主體性。這有助于讓當事人的故事得到更全面、深入和真實地呈現。口述檔案記錄了各種文化和社會背景下的經驗和見解。將這些口述檔案轉化為非虛構文學作品,能夠跨越語言、文化和地理的限制,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理解。[9-12]通過閱讀非虛構文學書寫,人們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其他文化和社群,拓寬視野,增進跨文化的溝通和對話。
口述檔案與非虛構文學可以為歷史提供珍貴的個人經歷和見證。通過對口述檔案的研究,結合非虛構文學的敘述技巧,可以還原和呈現歷史事件中被較為傳統歷史記錄所忽略或較少關注的個人視角和經歷,從而豐富歷史的多元性和全面性。口述檔案與非虛構文學可以為社會底層群體帶來發聲和平臺。通過記錄和呈現底層群體的生活經驗、掙扎和抗爭,可以加深對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現實問題的理解。這種研究有助于提升社會意識,推動社會更加公平正義,并促進社會變革。口述檔案與非虛構文學的互現研究不僅僅關乎文學領域,也涉及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這種跨學科的研究能夠拓寬學術研究的邊界,促進學科之間的對話和合作。它為學者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徑,可以從不同角度探索和理解社會現象和人類經驗。口述檔案與非虛構文學的結合突出了個體故事的力量和影響。個人故事可以引起讀者的共鳴和情感共振,讓讀者更好地理解人性、情感和人類經驗的復雜性。這種研究能夠突破抽象概念,通過具體個人的故事和經歷,使學術研究更加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體驗。
總之,這種互現關系通過生動的故事與人物、全面的社會景觀、個體與公共的關聯以及喚起情感共鳴與社會關懷等方面,豐富了文學作品的表現力和意義。它們為文學創作帶來了更多的深度、真實性和社會關懷,使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和關注社會的底層群體和問題。
參考文獻:
[1]張愛鳳,王璇.喜劇電影的底層敘事研究[J].電影新作,2020(01):110-113+131.
[2]孟健.自媒體非虛構平臺的底層敘事研究[D].廈門大學,2021.
[3]方華,譚必勇.用數據敘事:基于康考迪亞大學口述歷史和數字故事中心的個案研究[J].檔案管理,2023(03):24-27+31.
[4]曹欣愷,周林興.數字創意產業視角下紅色檔案文化價值躍升路徑[J].山西檔案,2023(04):62-71.
[5]趙彥昌,韓瑞鵬.基于檔案記憶觀的沈陽抗戰歷史文化名城建設研究[J].山西檔案,2022(05):128-133+149.
[6]陳世琪.新世紀女性作家底層“非虛構”文學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23.
[7]王路晨.寫在羊皮紙上的歷史[D].福建師范大學,2018.
[8]魯敏.當代小說寫作中的“非虛構”權重之魅[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08):39-80.
[9]柯翌嘉.作為創意寫作資源的平民自我書寫研究[D].上海大學,2018.
[10]顏涵,于英香.國家認同建構視域下檔案的多元價值及其實現路徑[J].山西檔案,2023(03):63-71.
[11]尚新麗,張麗玟,彭登輝.破壁與賦能:數字人文視域下鄉村檔案文化建設的多維共振[J].檔案管理,2022(04):5-8.
[12]徐擁軍,郭若涵,王興廣.中國參與世界記憶項目:理念、路徑與展望[J].檔案與建設,2022(01):11-18.
(作者單位:華北水利水電大學人文藝術教育中心 楊紫瑋,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來稿日期:2024-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