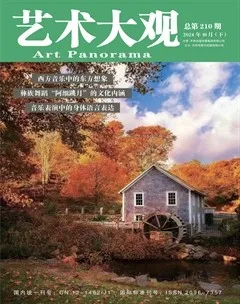“書畫同源”新解——以畫入書
摘要:“書畫同源”是中國畫寫意體系理論話語之一,縱觀前人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其源流、技法、歷史發(fā)展等方面的討論,很少有學者從“審美觀”的角度深入討論書畫背后所蘊含的共同審美邏輯。特別是大多數(shù)研究只是籠統(tǒng)認為“書畫同源”是傳統(tǒng)書畫“計白當黑”等創(chuàng)作原理的體現(xiàn),基本沒有涉及“書法”對“畫”的審美借鑒,也沒有細致地分析產(chǎn)生此結(jié)果的底層邏輯、美學原理等。因此,本文試圖從“以畫入書”式品評方式的角度對“書畫同源”這一命題做一闡釋,并聯(lián)系當今社會現(xiàn)狀深度挖掘中國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在當代人精神家園建設中的意義。
關(guān)鍵詞:書畫同源;審美觀;以畫入書
一、“以畫入書”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水墨”作為中國書畫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一直備受青睞,藝術(shù)家對它的討論也不絕于耳。比如,現(xiàn)當代有不少藝術(shù)家嘗試運用控制變量法解構(gòu)書畫要素,呈現(xiàn)了探索書畫本質(zhì)的多種形式的藝術(shù)作品。但當藝術(shù)表達的載體不再是漢字或者水墨時,觀者卻常常會對它是否還屬于中國書畫的范疇生出疑惑,同時也很難對這個作品產(chǎn)生獨屬于中國書畫的情感共鳴,這時反而更傾向于將它看作另一個獨立的藝術(shù)類型。在中國書畫傳統(tǒng)理論方面,雖然“書畫同源”的品評理論由來已久,但我們在評論具體的作品時通常還是將“書”“畫”當作兩個不同的領(lǐng)域,即使在評論寫意畫時會提及用筆有“篆籀氣”,但從來不會以看畫的方式品論書法。以上現(xiàn)象揭示了“書”“畫”割裂的現(xiàn)狀,也說明了再次討論“書畫同源”的必要性是勢不可擋的。但在此,筆者將不再贅述“以書入畫”的必要性,而是論證“以畫入書”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將繪畫的評論方式運用到書法中似乎會有損書法的獨立性,被質(zhì)疑將書法作品“圖像化”以及忽略了書法最重要的載體——漢字的作用。但筆者在此想討論的并非“畫學書法”一類的特定風格類型,而是想深入探索“以畫入書”的可能性并且論證其合理性。
二、“以畫入書”和“畫學書法”的區(qū)別
張亞圣在《碑學與帖學之外的視覺革命:畫學書法研究》中提出了“畫學書法”的定義,“所謂‘畫學書’,即將繪畫中的筆墨觀念和造型技巧等滲透到書法的創(chuàng)作中,有別于傳統(tǒng)‘書家書’的概念,又與學者熟知的‘畫家書’在源流上和‘以畫入書’的深入程度上迥然有別。同時,‘畫學書’并不顛覆傳統(tǒng)書法的守則,甚至對藝術(shù)家的繪畫水平也有著不同一般的要求。[1]”換句話說,就是將漢字視為純粹的圖像,由此以“造型意趣”為導向進行漢字創(chuàng)作變形,文中主要論述了“畫學書”的法度問題,詳細地說即筆法、字法、章法和墨法,但對“畫學書法”的精神內(nèi)核和實操性的探討仍然不夠深入,私以為張亞圣對“以畫入書”技法的討論過于浮于表面。因為從“書法同法”的角度來說,在這幾個方面書畫的關(guān)聯(lián)性只是自然發(fā)展中書畫技法符合邏輯的應用,所以,筆者認為據(jù)此將“畫學書法”作為獨立于“帖學書法”和“碑學書法”以外的書法體系是不夠嚴謹?shù)摹5@也確實為筆者討論“以書入畫”的可能性提供了一條可參考的路徑。不過,筆者提出的“以畫入書”不僅包括了適當融入繪畫的造型意趣,更重要的是厘清繪畫與書法更為本質(zhì)的審美觀的相同之處,尤其是寫意畫和書法的審美邏輯關(guān)聯(lián)。據(jù)此,也可以為“以畫入書”的合理性提供論據(jù)。
葛兆光提出,“語言文字是把面前這個世界呈現(xiàn)給我們看的一套話語系統(tǒng),每一種語言和文字都以一種既定的方式來描述和劃分宇宙,使生活在這套話語中的人們在學會語言文字時就自然地接受了它所呈現(xiàn)的世界[2]”。又由于中國古代書畫家身份的高度重合,所以我們可以預想到中國書畫的“審美觀”是同樣源于中國古代思想的思維模式的產(chǎn)生的必然成果。
三、“以畫入書”的實際運用
在書法中,“線”的表達總難免受到字形的局限,“以畫入書”往往只能止步于基于同種書畫工具的技法經(jīng)驗影響。可是,相對技法,畫的“意境”之美才是它藝術(shù)氣質(zhì)的核心,因此,討論“以畫入書”的可行性必將解決如何將“畫境”轉(zhuǎn)化為“書境”這一重難點。
一方面,把控書畫中的象形因素比例。值得注意的是,象形因素的比例判斷并不是指計算字形的保留程度,而是考量在改變字形的同時對“勢”的保留程度。“以畫入書”最忌將書法中的漢字視為純粹圖像,即完全摒棄字形結(jié)構(gòu),丟棄筆順承接順序,只注重“字”的外觀形狀。只注意外觀形狀會造成脫離“勢”的結(jié)果,而“勢”卻是構(gòu)成書法節(jié)奏韻律的主要手段,沒有“勢”的存在,書法就喪失了整體的邏輯性和表現(xiàn)“氣韻”的必要條件,最后徹底淪為“圖畫”。比如,“少字數(shù)派”①就陷入了過度取“象”而毫無“書勢”的誤區(qū)。北宋鄭樵亦提出:“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畫取多,書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畫也。不可畫則無其書矣。然書窮能變,故畫雖取多而得算常少,書雖取少而得算常多。六書也者,皆象形之變也。[3]”可見,“物象”的增加不是“以書入畫”的進取之道,過度濫用反而會降低書法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另一方面,探索書畫中“符號”承載情感的可行性。首先,我們需要確定“符號”的具體含義。20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曾經(jīng)提出將語言符號視為能指和所指的結(jié)合[4]。“能指”即語言符號的稱謂,“所指”即符號表達的含義。但筆者這里的“符號”并非此意,而是指書畫家情感載體,這個載體沒有具體形象,而是抽象意識的具象化。
四、“以書入畫”中“符號”的運用邏輯
我們需要通過探討書畫家運用“符號”的底層邏輯來證明“書畫同源”在“以畫入書”中的理論可行性。
(一)“符號”在書畫中的表現(xiàn)形式不同
“符號”表現(xiàn)在書法中就是用高度提煉簡化后的抽象點畫符號為載體,以筆勢映帶為邏輯進行藝術(shù)表現(xiàn);而在山水畫中就是依托畫家心意、審美去構(gòu)建山石結(jié)構(gòu)及組合。
(二)書畫藝術(shù)理論來源具有高度統(tǒng)一性
書法作品的“章法”與中國畫的布局邏輯往往高度重疊,如“計白當黑”“密不透風,疏可走馬”“陰陽相生”等,理論來源基本不出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的范疇。在古代書論中也有直接提到書畫審美相同之處的例子,如劉熙載曾提出“書宜平正,不宜欹側(cè)。古人或偏以欹側(cè)勝者,暗中必有撥轉(zhuǎn)機關(guān)者也。畫訣有‘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豈可執(zhí)一石一木論之?[5]”而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還有一大原因為中國古代文人對“八雅”的推崇,這
也直接導致了古代書畫家和文人身份的高度重合性,同時
也為書畫藝術(shù)審美的統(tǒng)一性奠定了現(xiàn)實基礎(chǔ)。
從第二點提出的現(xiàn)象似乎就可以斷定“書畫同源”的根本原因,可是這個邏輯成立的前提是創(chuàng)作者個人性情是藝術(shù)作品表現(xiàn)的邏輯起點而非社會思潮。但這個前提成立與否是存疑的,還需要再進行仔細推敲。而要想確定書畫家創(chuàng)作思維的底層邏輯就要嘗試找到此邏輯的起點,所以我們首先要厘清社會思潮和人的因果關(guān)系。也就是說,究竟是人決定了社會思潮從而誕生了符合“人”的審美的藝術(shù)作品,還是社會思潮孕育了相似的人從而通過“人”這個客觀載體創(chuàng)作出了相符的藝術(shù)作品?這聽起來似乎是個類似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荒謬爭論,但其實對厘清書畫誕生的本源來說是至關(guān)重要的。如果從書畫品評標準來說似乎是第一種,自魏晉人物品評說興起時,書畫作品的優(yōu)劣評比標準既包括了作品所用技巧的生疏、取法格調(diào)的高低,還包括作者的人品性情,甚至宋朝時期人們還將書畫家的個人修養(yǎng)納入考核標準。但從藝術(shù)的起源的角度分析又似乎是第二種。在遠古時期,人類社會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統(tǒng)治階層,先民們對器物的裝飾行為動機更多是審美本能等,發(fā)展至封建社會,“禮樂文化”的誕生讓藝術(shù)作品染上了“階級色彩”,藝術(shù)作品的作用自此便不僅是表現(xiàn)對美的追求,更是階級區(qū)分的象征,除了純粹的禮器,平時使用的功能性器具也多帶有象征身份的作用。從這種變化來看,似乎是社會的發(fā)展推動了藝術(shù)作品誕生動因的改變。可是得出這個結(jié)論的前提是,從遠古到封建社會的發(fā)展歷程中先民也始終與我們一樣主觀地將那些器物歸為“藝術(shù)作品”。但這顯然是不對的,因為在遠古時期,先民眼中的大部分東西,無論是器物還是書畫,往往是實用性遠大于審美作用的。并且,因為社會制度變革的節(jié)點要早于書畫獨立的時間點,而在書畫獨立之前也確實有許多雖然并非以審美為目的去主觀生產(chǎn)但又確實具有藝術(shù)價值的作品,所以會導致我們產(chǎn)生似乎應該由社會制度變革的時間點來界定書畫審美觀發(fā)展的轉(zhuǎn)變點的錯覺。但其實不然,社會制度的變革和藝術(shù)制度的演變并非嚴格的同步轉(zhuǎn)變,故筆者大膽猜測,書畫在成為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藝術(shù)類別之前的創(chuàng)作動因是“人”對美的本能追求,當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達到社會經(jīng)濟基礎(chǔ)足以支撐特地創(chuàng)造只具有純粹審美作用的藝術(shù)品后,藝術(shù)作品的發(fā)展和變革更多是由于社會思潮的推動。
(三)“符號”具有表達完整情感的承載力
從藝術(shù)表現(xiàn)力來說,書法和文人山水畫的整體視覺效果呈現(xiàn)從本質(zhì)上來講都是對“點、線、面”的審美布局。所以,當我們在欣賞書法和文人山水畫時不會首先注重文本的可識性或者山石的寫實程度,反而將“氣韻”“意境”的表現(xiàn)當作評判的首要標準。比如,徐渭在《草書詩卷》中完全打破字體結(jié)構(gòu),不強調(diào)行氣和上下字的筆勢連貫,而是將白紙當作整體安排呈現(xiàn)出獨特的藝術(shù)面貌。即使作品文本的可識性不高,但不可否認它是一件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事實上,我們在觀賞草書作品時,往往還需要聯(lián)系上下文來確定某個字具體的寫法,但絕不會將狂草與圖畫畫上等號。這不僅是因為線條的質(zhì)量、章法的安排、書家的情感會賦予“符號”獨一無二的表達,也是因為書法中所有線條的走向都是符合“書勢”這一底層邏輯的。同理,我們也不會將文人山水畫和真實景色去亦步亦趨地一一對應。
以上問題既是“以畫入書”的實施思路,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以畫入書”的合理性。總的來說,“線”同時作為書法和寫意山水畫的重要表現(xiàn)元素,是奠定書畫審美觀具有相通性的基礎(chǔ)。同時,利用“符號”表情達意的相同的藝術(shù)形式和書畫家同樣的思想文化內(nèi)核又再次推動形成了具有相近品評標準的中國書畫審美觀。據(jù)此,采用“以畫入書”式評論視角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五、結(jié)束語
“書畫同源”作為經(jīng)典的中國古代藝術(shù)理論的價值不僅是“書畫同體”和“書畫同法”兩個方面的,更是在探究中國式藝術(shù)審美觀方面的。中國式審美觀的研究意義既體現(xiàn)在剖析中國書畫審美的底層邏輯,找到中國書畫的本質(zhì)特征和核心藝術(shù)魅力,打破“書”“畫”兩個領(lǐng)域的創(chuàng)作壁壘,從而構(gòu)建更為完整中國書畫創(chuàng)作理論體系,也在謀求中國書畫審美觀與現(xiàn)代藝術(shù)思想的最大公約數(shù),在保持中國書畫核心精神的前提下,推動它進行新的演變,同時找到中國書畫在現(xiàn)代化背景下的有效傳承路徑。畢竟,被束之高閣的“陽春白雪”永遠不能擁有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動力,書法和山水畫作為極具中國特色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必須根植在日常生活中才能煥發(fā)出它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做到契合人民的精神需求才能真正地融入民族的骨血,成為永不衰竭且能代代相傳的藝術(shù)種類。
參考文獻:
[1]張亞圣.帖學與碑學之外的視覺革命:畫學書法研究[D].上海大學,2016.
[2]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3]鄭樵.通志二十略(上)[M].北京:中華書局,1995.
[4]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5]劉熙載.藝概[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6.
基金項目: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shù)學重大項目“中國畫寫意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2ZD15)子課題“中國畫寫意的理論范疇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楊夢月(2000-),女,重慶人,碩士研究生在讀,從事國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