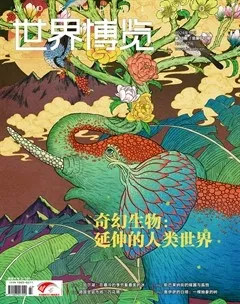洛伊斯的戰斗:一場長達14年的女性抗爭


洛伊斯·簡森(Lois Jenson)出生于1948年。高中畢業后,她被一個在聚會上認識的男人強暴,次年生下了一個男孩。1969年,她與高中同學又生下了一個女兒。單身女性要照顧好兩個幼兒,談何容易。經過一番痛苦的抉擇后,她將女兒送給了其他家庭收養。
一次偶然的機會,洛伊斯從客戶那里了解到埃弗萊斯鐵燧巖公司(以下簡稱埃弗萊斯礦)正在招聘女工,每小時工資5.5美元,有醫療保險,而且,在礦上工作30年后,就能領到頗為可觀的退休金。洛伊斯立刻被打動了。
其實,埃弗萊斯礦本來是不招女性的,這里工作環境臟亂,噪音很大,基本都是體力活。1974年4月,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司法部、勞動部與九大鋼鐵公司簽署了一份協議,要求鋼鐵公司為一直遭受歧視的女性和少數族群賠償3000萬美元,并把20%的工作機會提供給他們。因此,埃弗萊斯礦才開始招聘女性。
1975年2月25日,洛伊斯提交了求職申請,經過簡單的體檢后被錄用了。她想不到的是,她走向的是男性的叢林,一個讓她陷入夢魘的修羅場。

無處不在的性騷擾
去礦場工作后,洛伊斯發現骯臟下流的文字與圖畫無處不在。辦公室里的色情雜志、衛生間和浴室墻壁上的色情圖畫……甚至有的圖畫旁還標注了她或者其他女礦工的名字,這一切都讓她極度不適。更過分的是男礦工們持續不斷的騷擾和猥褻。
她患上了創傷后應激障礙,不時夢到可怕的性騷擾。在這將近10年的時間里,盡管有過多次辭職的想法,但生活所迫,洛伊斯最終還是放棄了。可以想見,在這個對女性十分“險惡”的工作環境中,洛伊斯不會是唯一的受害者,很多女性都遭受過或輕或重、或多或少的性騷擾。
1984年10月5日,洛伊斯給明尼蘇達州人權部寄了信。政府經過長時間的調查后,于1987年1月確認洛伊斯的指控屬實。為促成和解,政府要求埃弗萊斯礦制定防止性騷擾的方案,還罰款6000美元,裁決給予洛伊斯5000美元的精神損害賠償。公司雖然同意制定相關政策,卻以洛伊斯仍在礦上工作為由,拒絕支付罰款和精神損害賠償。雙方遲遲協商不下,案件便被轉到了政府的律師事務所——明尼蘇達州律師事務所,被分配給與洛伊斯同歲的女律師海倫·魯本斯坦。
海倫震驚于礦上普遍存在的性騷擾,認為該案或許可以集團訴訟的方式提起。洛伊斯對此表示十分贊同,但當她打電話給其他女性商討此事時,她們紛紛以各種事由推脫了,只有帕特·科斯馬施、米歇爾·麥思茨、黛安·霍奇三人趕了過來。這其中,在接下來的漫長而艱難的訴訟中,只有帕特真正堅持了下來,與洛伊斯堅定地站在一起。帕特同樣是位單身母親,要養育五個孩子,但與其他女性不同的是,帕特身材高大,性格直爽,好打抱不平,也樂于助人。可以說是礦上最有威信的女性。
海倫真心同情且相信這些女性,為此案作了大量調查和準備。但1987年10月,海倫撤出此案。隨后她給洛伊斯推薦了專門處理就業歧視案件的優秀律師保羅·斯普倫格爾,這一選擇無疑是歪打正著,因為當時保羅已經是美國“最成功、最受原告歡迎的就業歧視案律師”之一了。
保羅以前雖代理過個人性騷擾案,但這樣大規模的性騷擾還沒遇到過,他認為該案可以提起性騷擾集團訴訟,一旦成功,該案可能成為里程碑式的案件,自己的職業生涯也會增添濃墨重彩的一筆。不過,正是因為沒有先例,想要提起集團訴訟困難重重。
“險象環生”的審判
1988年8月15日,洛伊斯和帕特向明尼蘇達州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負責這個案件的是詹姆斯·羅森鮑姆法官,在他的主持下,1991年5月13日至6月3日,雙方進行了一場長達兩周的聽證會,主要就是否將該案作為集團訴訟和是否頒發禁令要求埃弗萊斯礦采取措施停止性騷擾行為而展開。原告方圍繞集團訴訟的條件論述,被告則試圖證明埃弗萊斯礦沒有性騷擾問題,而是將其淡化為男礦工無聊的色情玩笑和個別人的惡趣味。值得一提的是,有三位女礦工站在了被告方,證明礦山不存在所謂的性騷擾。她們作偽證,主要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1991年12月16日,羅森鮑姆法官宣布了他的裁決:集團訴訟資格通過,禁令救濟請求被駁回。盡管有喜有憂,但對原告來說,這已是巨大的勝利,畢竟這是美國法院的第一起性騷擾集團訴訟案,它確認了雇主應就惡意的工作環境而向所有雇員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而且,這個裁決還極大地改變了雙方的力量對比。出于巨額賠償的誘惑(或許還有個人意識的覺醒),很多女礦工紛紛加入原告,甚至包括原來為被告作證的三位女性。
1992年12月17日,接過該案的理查德·凱爾法官對其繼續審理,以確定雙方的責任。1993年5月14日,凱爾法官宣布判決結果,不僅確認了惡意工作環境的存在,還同意簽發禁令,下一階段將審理賠償數額問題。原告方可謂大獲全勝,不禁歡欣鼓舞,但她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竟是又一輪噩夢的開始。
對一些損害賠償數額計算比較復雜或者耗時較長的案子,法院可以指定退休法官、會計師等特別專家負責案件聽證會的主持、案件的審理等。由于凱爾法官太過繁忙,便把案件交給了退休的聯邦地方法官帕特里克·麥克納爾蒂審理。經過將近一年的調查、質詢、采集證人證言后,案件進行了開庭審理。在審理過程中,麥克納爾蒂放棄了法官的中立立場,甚至突破了一位法官的底線。在雙方辯論過程中,他明顯偏袒被告方,表達了鮮明的厭女態度。更嚴重的是,他竟然允許被告律師在公開的法庭上肆意詢問女礦工們的隱私。這也是被告律師的策略,通過公開隱私,極限施壓,讓她們歇斯底里,進而逼迫她們放棄訴訟。此外,他們還試圖向法院證明,女礦工們現在的精神狀況與埃弗萊斯礦無關,而是她們家庭和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所導致。他們達到了目的,面對嚴酷無情的質證,這些女礦工就像被公開處刑一般,再次“經歷”了痛苦的性騷擾,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殘,用洛伊斯的話來講,“我的感覺就像是正裸體坐在證人席上,法庭的氣氛和埃弗萊斯礦非常相似,我就像是一個罪犯,正在等待審判。”不僅是女礦工們,原告律師也被法官的無視和對方律師卑鄙的質證打敗了。庭審過程中,他們如坐針氈,如芒刺背,陷入絕望之中,甚至產生了放棄抵抗的想法,早早打算上訴。1996年3月28日,毫不意外,麥克納爾蒂作出了對女礦工們十分不利的判決。在這份長達416頁的報告中,他對女性展露了毫不掩飾的惡意,認為她們善于撒謊和演戲,訴訟的目的就是為了高額賠償,因此判給她們的賠償金額低得驚人。最致命的是,他把舉證責任分配給了原告,也即,原告需要證明她們所遭受的身體、心理和精神上的損害是由性騷擾而不是她們以前的經歷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這份臭名昭著的判決無異于給這些女性的訴訟判處了死刑。

奮力前行的孤勇者
帕特已于1994年11月7日去世。在悲觀的情緒中,再一次,洛伊斯又成了眾矢之的,女礦工們紛紛冷落她、孤立她,責怪是她將她們拖入了痛苦的深淵。但保羅卻看到了希望,這份判決是如此的錯誤百出,為提起上訴提供了強有力的理由。經過充足的準備后,1997年3月10日,原告上訴至聯邦第八巡回上訴法院。1997年10月21日,案件再次開庭審理,負責該案的三位法官都屬于民主黨陣營,十分看重公民權利。1997年12月5日,結果出來了,對于原告來說,判決振奮人心,它完全否定了麥克納爾蒂的結論,命令組成陪審團重新審判,還對麥克納爾蒂本人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評和嘲諷:“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勸說美國人盡量少用我們的法庭,那么在本案中,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如果正義是我們的追求,公民們必須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對女礦工們的處境,法官們也感同身受:“顯然,埃弗萊斯礦對待婦女一直冷酷無情,并一直存在著性騷擾,而婦女們因此遭受的精神痛苦也顯而易見。這些非人道的做法傷害了每位原告的情感及精神,她們蒙受了不可挽回的羞辱。盡管金錢損害賠償不足以彌補對她們的傷害,也不能使她們恢復到受損害之前的狀態,但卻可以確立一個先例——在工作場所,這種惡意是不能被容忍的。”
埃弗萊斯礦不愿服輸,繼續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1998年6月被駁回。案件又回到聯邦第八巡回上訴法院,經過難纏的拉鋸戰,雙方最終達成了和解協議。對女礦工們來說,這頗有幾分無奈。案件已經持續了十幾年,她們——尤其是洛伊斯——為此案遍體鱗傷,心力交瘁,和解也算是體面地退出。最終和解方案還可以接受,埃弗萊斯礦總共支付十五位原告350萬美元,洛伊斯的最多,得到100萬美元的賠償,最少的也拿到了5萬美元。
盡管該案是以和解收尾,但并不妨礙其成為美國司法進程中的里程碑案件。制度的變革、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需要洛伊斯和帕特這樣的孤勇者。有時,他(她)們的行動或許只是出于維護自身權利,但在客觀上往往會產生溢出效應,惠及千千萬萬個你我。我想說的是,也許有時我們做不到那樣奮不顧身,甚至連聲援的勇氣也沒有,那就安靜地做個搭便車的人吧,但千萬不要成為那個開倒車的人。
(責編:劉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