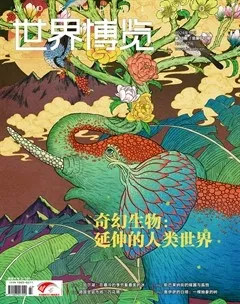斯巴萊納街的喧囂與孤獨


布拉格市中心的斯巴萊納街,和伏爾塔瓦河平行,北口與民族大街交叉,南口通向查理廣場。捷克作家赫拉巴爾在《過于喧囂的孤獨》中寫道:“在斯巴萊納街人們從不停步,全都急匆匆從民族大街趕往查理廣場或者反過來……”
今天也是如此。南來北往的電車,“哐當哐當”地停下又交錯著出發。步道上從來不缺趕路的人。透過咖啡館玻璃窗,有人悠然自得,有人咂舌道:“1杯咖啡都95克朗了,這是什么天價!”
街道上的靈感
斯巴萊納街和民族大街的交叉路口,矗立著一座方方正正的功能主義建筑——名為MAJ(五月)的商業樓。2024年5月初,人們驚訝地發現,大樓墻面上,“飛”來兩只巨型“蝴蝶”,紗翼般的翅膀一開一合,蝴蝶的軀干,竟是戰斗機機身,機頭螺旋槳在緩緩轉動。正值紀念二戰結束79年之際,捷克藝術家大衛·切爾尼說他創作這件裝置,向英國皇家空軍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戰斗機飛行員致敬。
附近還有一件大衛·切爾尼的佳作。緊挨著五月商場南側有一幢商廈QUADRIO,從斯巴萊納街穿過商廈,32560499c62741d476872ee361e5f3d8259958237668ea500e1d2a30a9bc30b2總會看到那片空場上站著幾十人圍成一圈,呆望著中間的不銹鋼卡夫卡頭像。這件頭像用了40噸鋼,有10米高,特別之處在于42層橫切片會按照各自的方向轉動,轉動之間,頭像形狀錯亂,然后,在某一個時間點,歸位復原,如此循環往復。



穿越商廈返回斯巴萊納街向南,右手邊有一間特別好看的舊書店。再往前走,左手邊是捷克保險公司大樓,有近200年歷史。繼續向南,一幢不起眼的白色辦公樓,底商的墻面刷成粉紅色。左手邊是一間辦公用品社,經營復印、刻章,右手邊是一間寵物商店。中間兩扇對開大門,木框木格鑲著玻璃,門牌紅號79,藍號10。左側的門柱上,有一塊銅牌,銅牌上印刻著捷克作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的頭像,文字寫道:“這棟樓曾經是廢品收購站。1954年到1959年間,捷克著名作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曾在這里作為廢舊紙張打包工工作,并獲得《過于喧囂的孤獨》一書的靈感。”
打包工的獨白
我諦聽這座五層樓房——我們廢紙收購站就在這座樓房里……我聽見抽水馬桶的沖水聲……我聽見了水泥地下面老鼠的叫喊和哀號,在首都布拉格所有的下水道里兩個鼠族在進行著瘋狂的戰斗,爭奪城市里所有下水道和陰溝的統治權。天道不仁慈,在我的上面和在我的下面,生活也不仁慈,我心里也不。
這是一位名叫漢嘉的打包工的獨白。漢嘉35年如一日,在廢品收購站的地下室里,用壓力機處理運來的各種各樣的廢紙和書籍。在毀掉書籍的工作中,他無意間獲得了學識,“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很難分辨哪些思想來自自己的大腦,哪些來自書本”。
打包廢紙包的時候,漢嘉總會秘密地在里面特意放一本經典著作,還會把要銷毀的名畫復制品裹在外面,使之成為具有個性的廢紙包。母親去世后,漢嘉在火葬場等待焚化,他自我介紹說:“我是一個以同樣方式處理書本的人。”在他眼里,書有生命。他同叔本華、黑格爾、薩特、加繆、耶穌、老子等人神交已久。
漢嘉利用職務之便,撿回家幾噸重的書,堆滿了儲藏室、雜物間、廚房、食品間、廁所、過道,以及睡房的天頂。睡床上方的隔板,架著兩噸重的書,隨時有可能坍塌,如同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還幫著美學教授淘書,借此賺取額外收入。他也幫教堂司事淘書,豐富司事先生的圖書收藏。司事先生做事的圣三一教堂,與廢品收購站只有幾步之隔。


如今,我們先在教堂邊看到一尊石雕,一人多高的基座上站立著圣達代烏斯,他頭上有個金屬圓圈,手里舉著耶穌圣像,腳邊左右各一個小天使。漢嘉曾無數次路過這里,停留歇息,祈禱圣達代烏斯顯靈。圣三一教堂內部的氣氛是明快的,進門迎面一個小小的透明隔間,里面有個彩色塑料滑梯,還有一些童書,穹頂上巴洛克風格的宗教畫絢麗多彩。
漢嘉在地下室打包,每日與鼠族相伴,諦聽鼠族的戰爭,而他隨便一鏟就把一窩剛剛半睜開眼的嬰幼兒小老鼠鏟進打包機無情碾壓,一個卑微的打包工對老鼠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但這些耗子都有事后立刻遺忘的特點”,老鼠的生存之道,和其他生物一樣,“哪里有耗子,哪里就有耗子窩,幾個月后便會出現一個耗子聚居點,不出半年就成了一個耗子村,然后按照幾何進程一年以后發展為一座小城市”。
老打包工漢嘉的生活里,還有如同一只小貓的茨岡小姑娘(茨岡人,又稱羅姆人、吉普賽人,主要分布在歐洲);美麗的但總是走“屎”運被人恥笑的曼倩卡;在鐵路上干了一輩子的舅舅,退休以后還在自家花園里裝了信號塔;對著漢嘉咆哮的、喜歡女孩的主任;兩個穿青綠色裙子和紅裙子的茨岡女人。
跟著赫拉巴爾的漢嘉,我們穿過電車往來的道路,站到一棟建筑前面,頭頂上方,一只鐵錨鑲在立面墻上。小說中,漢嘉到這里打啤酒,推門而入,“站在售酒柜臺旁也像在夢中一樣,神思不屬地解開外衣扣子摸錢付賬,卻不料一只耗子從我的外衣里躥了出來”。
漢嘉以為“這份工作將永遠這個樣子干下去,這臺機器將隨我一起退休”,“然而,同我全部夢想截然相反的事情發生了”。年輕的社會主義突擊隊員來了,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習慣了舊節奏的人無所適從,而巨型壓力機氣勢如虹地“摧毀著面前一切擋住去路的東西”。
我看到整個布拉格連同我自己、我所有的思想、我讀過的所有的書,我整個的一生都壓在這個包里,不比一個小耗子更有價值的一生……
作家的命運
赫拉巴爾被認為是20世紀最優秀的捷克作家之一。他小學、中學成績不好,21歲通過國考拿到中學畢業證書。1946年,拿到查理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赫拉巴爾做過很多職業,賣保險、賣旅行產品,在煉鋼廠、廢紙回收站工作,還在劇院擔任舞臺工作人員。他的小說創作主要集中在20世紀60年代,他49歲之后。他常常描寫“時代垃圾堆上”的小人物,政治困境和道德模糊性是他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主題。那些信手拈來、輕描淡寫的背后,常常一針見血、直戳人心。
《過于喧囂的孤獨》是一部每次閱讀都令人感受到新的觸動的故事。在斯巴萊納街上走一趟,“從民族大街趕往查理廣場或者反過來”,人生情境里細碎流光的幸福,面對外部世界的無奈,社會變遷對個體的碾壓,不同族群或物種之間的傷害,在書里的書里,小人物的生活里、愿望里、臆想里,隨處可見。而“天道不仁慈”,鼠與鼠,人與鼠,人與人,每每令人意識到書中所言,它在“告訴我迄今我尚不了解的有關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我也領悟了耶穌那句冷酷的話語是什么意義:我來不是送和平,而是劍”。

小說結尾,漢嘉走出工作了35年的斯巴萊納街,走到查理廣場,又莫名地走回去,“沉思著開了收購站后門的鎖”。“為什么老子說誕生是退出,死亡是進入呢?”他自己跨進打包廢紙的槽里,“開始跨進一個我還從未去過的世界”,似夢似真。
赫拉巴爾曾說:“我為《過于喧囂的孤獨》而活著,并為它而推遲了我的死亡。”這部書于1976年7月完稿,1989年底正式出版。1997年,赫拉巴爾即將83歲之際,在布羅夫卡醫院住院,據說是因為推窗喂鳥不慎墜樓。他的離去,成為不解之謎。
什么也不記得了,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聽不見,因為我也許已經到過天堂里百花園的中心。
(責編:李玉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