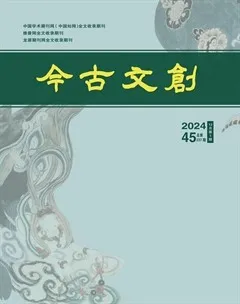明中期贛南地區的社會失序與政區調整
【摘要】明中期是贛南政區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由于嚴重的社會動亂,官方著手進行政區調整。這一舉措加快了贛南地區社會秩序的恢復,鞏固了明王朝對贛南的政治控制,促進了贛南的經濟開發和社會變遷,最終保障了國家安全,維護了國家統一。通過研究明中期贛南政區調整的社會背景、具體過程及其意義,可以加深對該地社會發展的認識,并為地方治理提供歷史借鑒。
【關鍵詞】明中期;贛南地區;社會失序;政區調整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45-0077-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19
政區是國家依據人口分布、經濟狀況、自然條件、歷史傳統等因素而劃分的地域單位和組織形式,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延續性。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統治者亦會將政區調整作為一種治理手段加以運用,從而對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明中期①時,贛南地區②陷入了混亂失序的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官方亦適時對當地政區做出調整,以期穩定社會秩序,強化政治控制。以往的政區研究多為通史性的綜合論述,對贛南的政區演進多是置于江西政區發展史當中去考量,容易忽略贛南社會情況的特殊性。③贛南地處東南腹地,介乎中原與嶺南之間,為贛閩粵湘四省往來要沖,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尤其是,隨著大庾嶺通道的開鑿,贛南一舉成為南北交通的聯結樞紐和戰略要地,適應了唐宋以來江南地區的迅速開發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這一時代大趨勢。④這使得明中期贛南地區的動亂與政區調整,不僅事關贛南社會的治理和發展,更關乎國家戰略安全。
一、山河無定:贛南地區的社會失序
明中期時,明朝由盛轉衰,統治階層日益腐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贛南地區也出現了諸如土地兼并、賦役繁重、流民增多等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以至于民變四起,勢成燎原,社會秩序極度混亂,這其中有一些地區的社會動亂尤為嚴重。
橫水、桶岡地區。該地地處大庾、上猶、南康三縣交界,眾山璧立,路險徑僻。正德初年,謝志珊、藍天鳳等自稱“盤皇子孫”,并利用畬族民間流傳祖先盤瓠傳說的“寶印畫像”進行宣傳活動,在橫水、桶岡地區率眾起義,設官封號,立寨八十四座,并和其他起義軍相互聯絡,勢力綿延贛閩湘三省,堅持了十余年。[1]
安遠黃鄉地區。這一地區多高山大谷,接嶺連峰,有“盜區”之稱,其間橫亙有綿延三百余里的大帽山,正德以前如張仕錦、何積玉等人皆“恃險憑高,巢窟其中”,后葉芳自廣東程鄉入境,沿途吸納其他起義軍,“有眾七千,分為七哨,自號滿總,言滿有其眾也”[2]。萬歷四年,葉芳之孫葉楷又于當地招兵買馬,征糧籌款,勢力“延袤三百余里,田地盡其占據,黨與二三萬人,四季輪班,四出劫掠,流毒江西閩廣地方,難以盡數”[3]。
龍南下歷、高砂地區。這一地區臨近廣東和平縣,亦是山高林密之地。嘉靖三十六年,鄉民賴清規于下歷地區起義。賴清規本為平民,曾隨征三浰有功,善為人解紛息斗,常受縣官委用,后因郡卒索賄無度而聚眾起義,勢力遍及信豐、龍南、安遠三縣,并且“合岑岡賊李文彪、高砂賊謝允樟,號三巢,而清規為雄,嘯聚十年”[4]。
通過以上內容,并結合其他相關文獻記載,我們可以對明中期贛南動亂的發生特點進行總結。第一,動亂的發生頻率較高,尤以正德、嘉靖兩朝為甚。據相關數據統計,從洪武(1368-1398年)至康熙(1662-1722年)這355年中,贛南地區的動亂合計142次,其中明中期(正統至嘉靖)51次,占1/3強。而正德、嘉靖兩朝計35次,又占明中期動亂的2/3強。[5]第二,動亂的參與人數較多。這一時期,如葉芳、葉楷、賴清規等人發動的起義皆在數千余人以上,同時,在起義發生時還出現了當地民眾為之通風報信的情形,說明起義的爆發是得到了底層百姓的支持的。如橫水、桶岡起義時,王陽明就發現“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鳥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系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6]。第三,動亂的持續時間較長。從個體上看,如謝志珊、賴清規等人發起的起義都是堅持了十余年才被平定;從總體上看,贛南地區的起義此起彼伏地縱貫了整個明中期。第四,動亂對贛南地區的破壞程度是最為嚴重的。由于贛南地處東南腹地之中心要沖,這種極為優越的地理區位條件亦使其成為各方起義軍、官軍往來的必經之地,使得贛南的社會動蕩無論在持續時間上還是在破壞力上都遠超周邊地區。第五,動亂呈現出了地域上的集中性和影響上的廣泛性。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到,起義的發生有其策源地和中心。同時,贛閩粵湘毗鄰區在地域環境上山水相連,而各省官員卻無越境管轄權,面對起義軍時多采取推諉觀望的態度,有鑒于此,起義軍常常在政治力量薄弱的邊界山區輾轉作戰,相互聯絡,聲勢相通,使得起義的影響范圍極廣。如橫水、桶岡地區的謝志珊,浰頭地區的池仲容,就曾與大庾的陳曰能、樂昌的高快馬等人聯合采取軍事行動,使得起義的影響力遍及贛粵兩省。[7]第六,動亂呈現出了多族群流民共同參與的色彩。如橫水、桶岡等處起義的畬人就是早年因干旱和饑荒從廣東、湖廣遷入的,并被政府安置于此,長期以來以砍山耕作為生。[8]對此,黃志繁等人認為,“流民”常與“土著”形成概念對應,是指因居住時間不長、沒有本地戶籍而不被當地社會接受的人群,在官方管理體系中具有極強的不穩定性。[9]饒偉新則認為贛南流民或為躲避繁重賦役而脫籍的“逋負之徒”,或為未受教化的“蠻夷”,且兩者往往相互關聯,難以劃分界線。[10]總之,明中期贛南社會極度失序,動亂發生有其特點和規律,這為官方的社會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二、因時而變:贛南地區的政區調整
元末贛南分屬贛州、南安二路。贛州路下有贛、雩都、信豐、興國四縣與寧都、會昌二州,寧都州下有石城、安遠、龍南三縣,會昌州下有瑞金縣;南安路下有南康、大庾、永清三縣。乙巳年(1365),贛州、南安改路為府,州縣依舊。洪武初,降贛州府寧都、會昌2州為縣,與其下原有縣一起改隸于府;并將南安府的永清縣改名為上猶。[11]可見,明前期贛南地區只出現了少數政區級別調整和改名的情況,并未有大的數量上的變化。但至明中期時,贛南騷動,官方轉而從政區調整入手,新增了崇義、定南、長寧三縣,以重建社會秩序。
(一)崇義縣
崇義縣于正德十二年(1517)設立。這一地區原屬上猶縣,眾山璧立,與外界交流極為困難,故而號令難及。正德年間,橫水、桶岡地區爆發了以謝志珊、藍天鳳為首的起義,由于該地介乎三縣之中,加上山溪深阻的地理環境狀況,使得官方的鎮壓行動常常難以見效。
正德十二年,王陽明平定了謝志珊起義,監生楊仲貴認為,這一地區過去素為“盜區”,雖暫時戡平,但恐撤兵后殘余的起義人員重新聚集起來,故主張建立新縣以求長治久安。王陽明也認為應防亂于未發,通過眾建縣治來安定新民,推行王化,構建起良好的社會秩序:“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蕩,后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后,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為禮儀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于此。”[12]后王陽明委派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黃文鸑親往勘查,認為上猶縣的橫水地處三縣之中心,“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13]。最終析南康之尚德、隆平二里,上猶之崇義、雁湖、上堡三里,大庾之義安、鉛廠、聶都三里,置崇義縣,隸屬南安府。
(二)定南縣
定南縣于隆慶三年(1569)設立。這一地區向來地處邊遠,政教鮮及,民風獷悍,極難治理。嘉靖三十六年,下歷堡鄉民賴清規聚眾起義,與高砂謝允樟、岑崗李文彪互為奧援,這其中賴清規的勢力最為強盛。嘉靖四十五年,都御史吳百朋親督官兵進剿下歷地區,平定賴清規起義。為善后和長治久安考慮,吳百朋提請在當地設縣管理而未獲通過,但被準許在下歷“筑城建館,移置捕盜通判、主簿,統兵五百名,專一駐扎防守。其下歷巡司移于高砂蓮塘,亦筑土垣一座,添兵協防,以遏岑岡”[14]。
隆慶二年,張翀繼任南贛巡撫,再次強調增設縣治在安民、化俗、防亂等方面的作用,并懇請比照崇義設縣之先例,于下歷地區設置新縣,并委派贛州知府黃扆“親詣龍南下歷等處,將各應割地方逐一踏堪”,自己則“不避勞苦,親入各巢,備將民情土俗一一齊訪”[15],這為后來定南縣的析置提供了重要依據。最終析龍南之下歷、高砂、橫江三堡,安遠之伯洪、大石、小石三堡,信豐之潭慶半堡,置定南縣,隸贛州府。
(三)長寧縣
長寧縣(今尋烏縣)則于萬歷四年(1576)設立。該地原屬安遠,與廣東平遠、龍川、和平等地接壤,處贛粵兩省上游地區,多崇山峻嶺,此前如鄺子安、黎仲瑞、陳良玉、王霽壤、高安、陳士錦等人皆在這一地區發動起義,故早在正德五年時,該縣貢生林大綸就曾提請建立州治以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制,但因會議遷延,加之葉楷起義的爆發,錯失了設縣時機。萬歷四年,都御史江一麟平定葉楷起義,地方士紳再次提請仿照崇義、定南設縣之先例,認為:“然特一時之利,未為永久之規。須趁此機會,開設縣治,控制要沖,敷聲教而化導之。”[16]官方在聽取意見后著手析安遠黃鄉、雙橋、南橋、滋溪、石痕、八富、尋鄔、大墩、桂嶺、腰古、項山、勞田、水源、三標、石溪一十五堡與會昌長河一帶,置長寧縣,屬贛州府。
結合以上內容,從變動原因上看,首先,贛南政區的調整與當地重要的戰略地位有關。如贛州府“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陲,故裹耑一路之兵鈐,而外提二境之戎柄,其地重大”[17]。但明中期贛南社會的不穩定狀態卻阻礙了官方對這一戰略要區的控制。贛南山嶺縱橫的地理環境也常常導致縣域的政區中心偏處一地,地方政府對動亂山區的政治控制極為虛弱,故有必要對原有行政區劃進行調整。其次,贛南的政區調整與山區的經濟開發有關。自然地理環境是政區發展演進的基礎性影響因素,地形、氣候、土壤、水源等要素往往影響一地的開發序列和人口、聚落分布,相應的政區也常率先出現在經濟發達的平原、河谷地區,但隨著贛南經濟開發向山區縱深推進,自然環境對政區設置的影響也被逐漸削弱。
從變動規律上看,首先,新縣皆由多縣割置而成。一者,唐宋以來,贛南經濟開發速率增快,并進行了多次縣級政區增設。前期縣級政區數目較少,轄域較廣,以單縣析出為主,至明中期時,縣級政區劃分已較為細密,故不易出現單縣析出的情況。二者,明中期時贛南山區成為流民聚集地而得到極大開發,但也因此淪為動亂最為頻繁的地區。故無論從常規的經濟、人口因素出發,還是從應對動亂的角度來看,山區顯然更容易出現大的政區變動,而這些山區多處縣境邊界地區,故新縣皆為多縣割置而成。其次,新縣皆分布于動亂的中心地帶,且與社會動亂間表現出了一種前后相繼的時序特征,說明社會動亂作為社會環境變化的典型表征,對政區演進起著直接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直接的推動都是以特定的事件為契機出現的,但這些孤立事件卻都是明中期贛南社會極度失序的一個重要組成和側面反映,政區調整正是官方為應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在政治上做出的改變。而在維護地方的政治安全和有效統治這一需求下,官方會對贛南山區傾注更多的政治、經濟資源,從而提高當地的開發速率。再次,新縣的設立具有相對滯后性。一者,政區沿革本身就具有相對的延續性和穩定性。二者,新縣多處政區邊界地帶,這就意味設縣活動必然會受到相鄰府、縣的官員和百姓的關注,出于鄉土觀念、風俗習慣、社會治安等因素的考量,相關方往往會對置縣問題爭論不休。三者,成立新縣常常要經歷“前期勘察-地方提議-中央決定-具體實施”這樣一個繁瑣的過程。最后,在傳統政治體制運行下,統治者的個人能力和執政理念是影響政區調整的重要因素。這一時期,如王守仁、吳百朋、張翀等地方大員皆主張眾建縣治以杜漸防微,保境安民,從而推動了贛南政區變動。但我們亦不能忽略地方士紳和民眾對于新縣設立的訴求。張偉然認為,這種地方的“聲音”甚至可以直接影響上級決策。[18]結合上文可以看到,明中期以來贛南的政區調整大多是在起義平定后由地方士紳首先提議,再由巡撫上書通過的。
總之,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政區調整極具復雜性和困難性。但贛南作為戰略要地,對其政區進行調整以平息動亂,維護統治,是合乎現實需要,勢在必行的。
三、贛南政區調整的影響
隨著新縣設立,官方亦著手強化對動亂地區的控制和管理,從而達到了消弭動亂、穩定秩序的目的,并促進了贛南的社會發展,維護了國家統一。
(一)穩定秩序,推動發展
增建縣治的直接目的就是恢復地方秩序,預防動亂,鞏固統治。為此,官方首先會在動亂地區建立官署。如長寧縣:“贛撫江一麟檄知府葉夢熊、知縣沈文淵建今稱老縣堂。”[19]建立官署后,官方還會選派相應的行政官員對動亂區進行直接治理,但在人事配備上又與安定區有所差別,如王陽明認為新縣官員應當熟知捕盜安民之術和地方的民情土俗,從而保障地方事務的有序開展。[20]其次,官方常于新縣的交通要沖設立巡檢司,受轄于地方州縣,統領一定數量弓兵,稽往查來,打擊走私,于增強基層社會控制、消弭動亂都有著重要作用。如王陽明曾提出在崇義的長龍、上保、鉛廠等要害地方設立巡檢司,并對地方巡檢司的分布格局進行相應調整。[13]再次,官方還會在新縣修筑城池。如定南設縣時就曾遣員于高砂蓮塘鎮筑城鑿池,建成之后“城周圍三里有奇,凡四百四十丈,崇一丈有三尺,廣七尺。為雉堞七百八十,警鋪一十有六,城門三,東曰迎陽,西曰平成,南曰豐阜,各覆以樓,北向面山,南以開門。加砌一臺,亦覆樓一座,曰北樓。南門城內,舊有民塘,浚而深之為池”[21]。最終形成了一道以城墻為主體,結合護城河、雉堞、城門、警鋪、城樓等設施的系統防御工事。此外,官方還會在新縣駐扎大量兵力。如設崇義時王陽明曾主張派遣各隘隘夫駐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把守;其不系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余名之數”[6]。總之,這種直接的行政管理,堅固的防御工事,加上強大的兵力部署,可以極大地穩定地方社會的秩序。
隨著縣治的增設,地方社會的經濟也趨于恢復和發展。首先,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資源得以整合在一起并納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以定南縣為例,置縣初就從龍南、安遠、信豐三縣劃割了大量的田、地、陂、塘,并在后期通過清丈、新墾等方式使得官方掌握的田糧不斷增加。戶口亦從建縣初的“戶三百一十戶,口共一千八百五十五”,增長至乾隆四十四年時的“戶共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七戶,口共一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22]。其次,有利于賦役的征收。動亂平息后,大批流民也被國家重新納入戶籍管理,他們也需承擔起相應的賦役。因此,設立縣治后,官方往往會在當地對田賦徭役的征收標準進行重新額定,并在新縣推行里甲制度。曹樹基認為,里甲制度兼具賦役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職能,既有利于對封建社會的勞動力資源進行控制,又是重要的人口組織形式和政府基層組織。[23]故該法成為官方加強動亂地區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手段,促進了賦役的征收,同時還有著重要的政治象征意義,成為中原王朝在地方行使主權的重要表現。最后,為便于管控地方和政令的上傳下達,官方還會在新縣大力修建道路,這既打破了當地重嶺疊嶂、封閉險遠的地理格局,又加快了人員、物資的流動。尤其是隨著商品交換活動的興起,亦促進了鄉村集市的發展繁榮。如定南建縣之初尚未有墟市,以至于當地的貨產只能運至鄰縣進行貿易,道路險阻,安全難以保障。隨著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最終于萬歷十一年“立墟市于城隍廟前,僉立墟長,較定稱錘斗斛,厘戥丈尺,物價照時,每月以三、六、九日為期”[24]。
(二)宣揚政教,變風易俗
這一時期,官方著手在政治上加強對新縣的管理,一個重要的表現在于將保甲制度推行到了地方治理當中,這極大適應了贛南地區移民運動活躍、社會動亂頻繁的特殊環境。如王陽明認為,要想從根源上杜絕動亂的發生,單純依靠軍事鎮壓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崇義縣積極推行保甲性質的“十家牌法”,并遣官前往查審落實。此法以十家為一牌,將各家的丁口、籍貫、年齡、性別、職業詳注于牌,定時查驗,并行連坐之法,強制民眾相互監督,從而區分良莠、防微杜漸。[25]而此牌法推行后,亦能夠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產生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極大地強化了中原王朝對地方基層社會的控制力。黃志繁認為,明中期王陽明在贛南推行的保甲加鄉約的治理模式并沒有流于形式,而是具有極強的模式WyEb33cMe0SKqqXFGVuGqQgGP0uEvZm31L+8ai3lSgE=效應并為繼任者所沿襲。[26]同時,官方還著手在文化上加強對新縣民眾的教化。史載贛南地區“(百姓)質樸少文,水耕火耨,竭胼胝之力,食土壤之毛,且山深箐密,易于藏奸,民俗勁悍,任氣好斗”[27],說明自然環境不僅可以提供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而且能夠對民眾的行為、心理產生影響,而贛南這種民俗勁悍的社會風氣亦會給社會治理帶來極大的困難。而學校教育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在培養人才、教化民眾方面有著突出效果,從而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如崇義縣學為“王都御史守仁命南康縣丞舒富創建”[28];定南縣學則由“都御史張翀,知府黃扆建”[29]。但縣學的設立更多是為了應舉和講學,加之有人數限制,使其成了服務于少數人的精英教育,與多數普通民眾的聯系并不緊密。為普及教育,適應普通百姓的經濟狀況,官方又大力在新置縣推行社學教育。如定南“建學之初,設社學二處,一在城西,一在下歷城內”[30],加之地方官的后期增置、重修和定期巡查,使得社學教育得以推廣開來。最終,通過學校教育大大推動了儒學在新縣的傳播,促進了贛南儒家道德觀念和價值體系的構建,在潛移默化中使贛南民風由過去的民俗勁悍、任氣好斗轉變為了尚學好文、崇文重教,從而達到移風易俗之效。
(三)經略東南,維護統一
大庾嶺通道的開鑿,意義深遠。經濟上,大庾嶺通道自唐宋以后逐漸成為中原和嶺南間的主要溝通通道,并形成了繁榮的過境貿易,官方也得以獲得巨額的商稅收入,提高了贛南的交通、經濟地位。[31]而隨著大量物資通過該通道進行流通,東南與嶺南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也加深了,史載“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粗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馱,過北者日有數千”[32]。從中可見,嶺南、嶺北地區在物資產出和供應上存在著明顯的區別,這一方面導致了南北商隊規模和過關次數上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說明嶺南與嶺北間是存在著極強的經濟互補性的,而大庾嶺通道的存在無疑加強了區域間的經濟一體化。政治上,以往大運河的興修雖然起到了溝通南北的作用,但這種聯系更多局限于中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間,而隨著大庾嶺通道的開鑿,中原與東南的廣大腹地山區乃至嶺南地區間的交流往來變得更加緊密了,既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也保證了中原對東南乃至嶺南財富的控制,在經略東南、控扼嶺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軍事上,顧祖禹認為“嶺據南北之咽喉,為戰守必爭之地”[33]。但明中期以來,贛南大亂,與閩粵湘地區的起義遙相呼應,整個東南腹地的社會秩序極度混亂。統治者一方面擔心這種動亂影響到南方經濟核心區,動搖王朝統治,另一方面,長期的動亂使得南北交通運輸線時常被阻斷,威脅國家的經濟安全,削弱了中原王朝在東南直至嶺南的政治控制力。故隨著社會動亂的漸次戡平,官方著手在贛南地區進行政區調整,結合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其很大程度上是希冀通過維護地方的社會秩序來牢牢控制南北經濟線。這使得贛南政區調整的影響力已不單局限于贛南一地,而是事關對南方的政治軍事經略、南北商路的通暢、中外貿易的發展、國家統一的維護等方面的內容,牽一發而動全身,意義深遠。
總之,設置新縣是達到了應有的統治效果的,并使得明后期贛南社會保持了較長一段時間的穩定。正統至嘉靖年間,贛南的動亂總計51次,之后隆慶1次,萬歷4次,天啟2次,崇禎8次。[5]基本上達到了撥亂反正之效,為中原王朝穩定東南、控制嶺南、維護統一提供了保障。
四、結語
贛南地區戰略地位極高,但又長期處于中原王朝統治的邊緣地帶,治理不易,明中期時,贛南爆發了劇烈的社會動亂,威脅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安全。為此,官方著手在贛南創設新縣,專地專管,并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加強了對動亂地區的控制和管理,改善了當地的政治環境,達到了綏靖地方、宣傳政教、向化新民等效果。
總的來說,明中期贛南地區的社會動亂與政區調整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過程,反映了當時贛南地域社會的歷史進程和發展脈絡,呈現出了極強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既可以深化我們對明代歷史的認識,又可為相關研究提供極好的個案。這一時期,贛南政區變動多發生在原先山高地僻、經濟落后、王化未開之地,這種填補空白式的置縣模式說明,政區的實際控制是呈現出了一種由核心區向邊緣區,由河谷向山區,由虛向實的推進之勢,反映了贛南經濟開發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側影。同時,贛南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社會動亂也最為劇烈,但正是在這樣重要的區位條件下,贛南地區的政區調整及其治理才顯得尤為關鍵。
注釋:
①關于明中期的時間界定,學界一般認為正統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是明中期的開端,將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進行賦稅制度改革視為明中期的時間下限。參考南炳文、湯綱《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218頁。
②贛南地區,按現行行政區劃屬贛州市統轄,包括章貢、南康、贛縣3個市轄區,瑞金、龍南2個縣級市,興國、寧都、石城、安遠、尋烏、定南、全南、信豐、于都、會昌、大余、崇義、上猶13個縣,在明代時分屬于南安府、贛州府。
③關于贛南政區演進研究,可參考肖忠華、劉有鑫《江西古代的政區建置與歷史沿革(下)》,《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第42-47頁;吳啟琳《傳承與嬗變:明清贛南地方政治秩序與基層行政之演化》,復旦大學2011年學位論文;張磊《明清江西新設縣廳研究》,復旦大學2012年學位論文;郭茹霞《江西縣級政區的地名研究》,江西師范大學2021年學位論文。
④有關大庾嶺通道的歷史沿革及其在中國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相關研究,參考鄭文《梅關古驛道的興衰》,《江西歷史文物》1984年第2期,第69-73頁;胡水鳳《大庾嶺古道在中國交通史上的地位》,《宜春師專學報》1998年第6期,第36-40頁。有關大庾嶺通道開鑿對促進贛南經濟發展的研究,參考黃志繁《大庾嶺商路·山區市場·邊緣市場——清代贛南市場研究》,《南昌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第28-32頁;廖聲豐《清代贛關稅收的變化與大庾嶺商路的商品流通》,《歷史檔案》2001年第4期,第85-92頁。有關大庾嶺通道在溝通南北和促進中外貿易發展方面的研究,參考王元林《唐開元后的梅嶺道與中外商貿交流》,《暨南學報》2004年第1期,第128-133+142頁。
參考文獻:
[1](明)王守仁.橫水桶岡捷音疏[A]//(清)黃鳴珂修,石景芬纂.南安府志卷24·藝文七(清同治七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2113-2115.
[2](清)顧炎武撰,黃珅等校點.天下郡國利病書[A]//江西備錄·贛州府志·解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82.
[3](明)江一麟.平黃鄉疏[A]//(清)魏瀛等修,鐘音鴻等纂.贛州府志卷69·藝文志·明文(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1258.
[4](清)顧炎武撰,黃珅等校點.天下郡國利病書[A]//江西備錄·贛州府志·解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61.
[5]鄒春生.文化傳播與族群整合:宋明時期贛閩粵邊區的儒學實踐與客家族群的形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64.
[6](明)王守仁.立崇義縣治疏[A]//(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10·別錄二·奏疏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90.
[7](清)魏瀛等修,鐘音鴻等纂.贛州府志卷32·經政志·武事(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586.
[8](明)王守仁.立崇義縣治疏[A]//(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10·別錄二·奏疏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88-389.
[9]黃志繁,肖文評,周偉華.明清贛閩粵邊界毗鄰區生態、族群與“客家文化”:晚清客家族群認同建構的歷史背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34-35.
[10]饒偉新.明代贛南的社會動亂與閩粵移民的族群背景[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04):133-139.
[11]周振鶴主編,郭紅,靳潤成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130-131.
[12](明)王守仁.立崇義縣治疏[A]//(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10·別錄二·奏疏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90-391.
[13](明)王守仁.立崇義縣治疏[A]//(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10·別錄二·奏疏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89.
[14](明)張翀.建定南縣疏[A]//(清)魏瀛等修,鐘音鴻等纂.贛州府志卷68·藝文志·明文(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1249.
[15](明)張翀.建定南縣疏[A]//(清)魏瀛等修,鐘音鴻等纂.贛州府志卷68·藝文志·明文(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1249-1250.
[16](明)吳百朋.分建長寧縣疏[A]//(清)魏瀛等修鐘音鴻等纂.贛州府志卷67·藝文志·明文(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1229.
[17](清)顧炎武撰,黃珅等校點.天下郡國利病書[A]//江西備錄·形勝·贛州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23.
[18]張偉然.歸屬、表達、調整:小尺度區域的政治命運——以“南灣事件”為例[M].歷史地理(第2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2-193.
[19](清)沈镕經修,劉德姚纂.長寧縣志卷1·官署(清光緒二年修七年重訂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225.
[20](明)王守仁.再議崇義縣治疏[A]//(清)黃鳴珂修,石景芬纂.南安府志卷24·藝文七(清同治七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2143-2144.
[21](清)賴勛修,黃錫光纂.定南廳志卷1·城池志(清道光五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143-144.
[22](清)賴勛修,黃錫光纂.定南廳志卷3·貢賦·戶口(清道光五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256-257.
[23]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四卷·明時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58.
[24](清)賴勛修,黃錫光纂.定南廳志卷1·城池志·墟市(清道光五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150.
[25](明)王守仁.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A]//(清)黃鳴珂修,石景芬纂.南安府志卷25·藝文八(清同治七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2210-2214.
[26]黃志繁.鄉約與保甲:以明代贛南為中心的分析[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2).
[27](清)魏瀛等修,鐘音鴻等纂.贛州府志卷首,序(清同治十二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6.
[28](清)黃鳴珂修,石景芬纂.南安府志卷5·廟學(清同治七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313.
[29](清)賴勛修,黃錫光纂.定南廳志卷2·學校(清道光五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185.
[30](清)賴勛修,黃錫光纂.定南廳志卷2·學校·書院(清道光五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240.
[31]廖聲豐.清代贛關稅收的變化與大庾嶺商路的商品流通[J].歷史檔案,2001,(4).
[32](明)張弼.張弼均利記[A]//(清)顧炎武撰,黃珅等校點.天下郡國利病書·江西備錄·贛州府志·解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64.
[33](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5:3889.
作者簡介:
丁揚,男,江西于都人,中國史專業2022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歷史地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