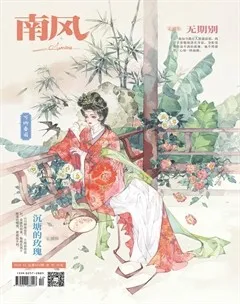一柱樓詩血案恩仇錄

想不到自己竟是這樣悲慘的身世,有著這血海深仇。玉讀五雷轟頂,心中翻江倒海,恨不得即刻身插雙翅,飛回故鄉,找到仇家報仇。
一
凌晨,一抹魚肚白綻現東方云層豁處,西天一眉冷月,二三顆星欲墜,山林間晨霧茫茫,風過處,濃霧四漫,正是東方欲曉之時,天地一片寂靜。
山谷深處一陣細碎的滴滴答答的馬蹄聲,風起霧散,一白衣少年,肩背一把寶劍,胯下一座騎,渾身雪白,從林間一團濃霧中逸出。那少年好不性急,剛上官道,就揚起馬鞭,懸空掄起一個鞭花,“叭叭”二聲,兩腿一夾馬肚,身子往下一銼,那馬兒霎時四腿撒野,像一道閃電,向千里之外的黃海邊疾駛而去。
二
寺院之夜,靜寂無聲,僧人清心寡欲,打坐念經。仲春四月的一晚,悟覺方丈將僧人玉讀叫至禪房靜室,說:“玉讀,你是我寺中俗家子弟,未曾讓你受戒,剃度,是因你塵根未斷,你本是徐家骨血,僅存的血脈。你現已長大成人,且學得一身武藝,為師今將你身世告知于你,你從此出山,如何行事,為師不可妄言,只是要你務必切記,到了地方,理應除惡行善,切不可枉殺無辜。
后日即清明,你速去父母墳前祭奠,以盡孝子之心,你的家鄉在黃海之濱的古茶鎮。為師贈你一把玉龍寶劍,給你一匹快馬,明晨你可趁早趕去。”
玉讀在寺中長成18歲,只知自己是一孤兒,被寺中方丈收養,教他武藝,今天聽方丈說起遠古茶樹,朦朧間,好像兒時曾在這棵樹下玩過尿泥之類的游戲。想不到自己竟是這樣悲慘的身世,有著這血海深仇。玉讀五雷轟頂,心中翻江倒海,恨不得即刻身插雙翅,飛回故鄉,找到仇家報仇。
玉讀一夜輾轉反側,不能入睡,三更剛響,即起身收拾,于山門外對方丈寢室對空三拜而別。
三
公元1778年中秋之夜,一輪明月從海上升起,斗轉星移,那明月高懸古茶樹梢。月華燦燦,清輝遍野,鎮上人家在院內呈上供月果品,闔家老小品茶賞月。
古茶鎮,位于黃海之濱,長江入海處,千年長江之水挾滔滔泥沙積聚成為陸地。鎮郊有一棵亭如華蓋,高大茂盛的古茶樹,茶樹已有三百多年的樹齡,古茶鎮名由此而來。鎮內長長短短寬寬窄窄大大小小的巷子縱橫交錯,首尾相連,有一條四鄉聞名的“叛房巷”。巷內有一老宅,系古鎮舉人徐天濤的宅院,院內有一古色古香的樓閣,樓前有一對赤字竹葉斑紋石鼓,雕刻精致。一柱樓構思精巧,匠心獨運,樓中心僅以一柱支之,眾梁紛架其上,樓梯筑于樓外,盤旋而上。以一柱為主體,故名:“一柱樓”。不知樓主是否以此樓自勉,一體撐天,獨立于天下為寓意,還是因此樓的形體故名而已。總之這叛房巷因這樓而聞名于世,而此樓因院主之建造,因院主的才華而聞名遐邇,流芳百世。
院主徐天濤出生于一個鄉親家庭,自小聰明好學。17歲參加童試,才華出眾,連闖縣試,府試,院試,為秀才。公元1738年,考中舉人。這一年對徐家來說足以光耀門庭,但也是讓徐天濤深為沮喪的一年。
清朝科場規定,中舉者答卷須送京城,由朝廷文臣禮部官員“磨勘”復查。這一年的試題是“君使臣,以禮”。徐文中“禮者君所自盡者”。這“自盡”二字,原義是以身作則的意思,卻被禮部官員認為“自盡”是對皇帝“君”的大不敬,“有譏諷朝廷之意”。取消徐天濤進士會試資格,并加以懲罰,永不錄用。徐天濤心灰意冷,拋棄功名利祿,就這樣清朝失去了一位富有才學的官員,但給中國的建筑留下了一座別具一格的樓臺。
讓徐天濤萬萬沒想到的是,在他死后的幾十年后,這座樓臺以及其詩作禍及子孫,給他的家族帶來了極其悲慘的災難,一時成為舉國上下聞之色變的文字獄冤案。
四
心灰意冷的徐天濤,從此在一柱樓中著書立說,邀集意趣相投之士登樓詩文唱和,品茶吟詩會友度日,倒也逍遙自在,徐天濤著作頗豐,名垂后世,光彩照人。
徐天濤在樓中寫下了《一柱樓編年詩》《一柱樓題詩》,一首《野菊詩》傳于后世,廣為流傳。詩中可以看出其心志和他的萬般感慨,詩曰:“平原極目盡成空,只見霜痕濕幾叢,自入秋來貞晚節,最無人處對西風,香傳老圃疏離外,影落斜暉淡月中,凡物茍能循本性,何妨蕭瑟寄蒿蓬。”
他是說:在廣闊平坦的原野上,我(徐天濤)極目遠望,一切草木都已凋謝了,只看到霜痕沾濕的幾叢野菊花,入秋以來,菊花能耐霜寒,保持節操,在人跡罕至的地方,迎著秋風抗爭著,看那破舊的園圃,稀疏的籬笆,菊花的香氣從那里傳出來,乍那暗淡的明亮,斜射的光芒,菊花的影子落在其間,萬事萬物如果能遵循它的本性,就算受到冷落,身在朝野,那又有什么關系呢?
五
這一年中秋夜,徐業成,在一柱樓宴請爺爺徐天濤的生前好友,同為舉人的沈昭和老人品茶賞月。席間談及爺爺的詩集,說父親徐懷鄉也是個監生,為追憶爺爺,為其揚名,在沈爺爺您的幫助下,刊刻了爺爺《一柱樓詩》著作。沈老先生由此說道,日前坊間誤傳這詩集中有諸多對當朝不敬之詞。
素與徐家交惡的當地惡霸陳浩,因徐業成的父親徐懷鄉,當年曾用2400兩白銀購買了陳浩堂兄的土地,現見徐家新喪,徐業成年弱不經事,欲以980兩銀贖回,被徐家拒絕。
公元1777年,清孝圣皇后病故,百姓不準剃發,這陳浩依然剃發,此事舉報官府,陳浩被罰500兩白銀,陳浩認為是徐懷鄉之告發,舊仇新恨,耿耿于懷。
三月前去揚州官衙告狀,舉報徐家藏有祖父的違禁文字,所好江蘇布政使陶易為官公正,愛其徐天濤詩文辭賦,看穿陳的小人本色,認為陳浩挾公義而泄私憤,想以此舉誣其田產,訴狀不準,處于刑罰,棍杖三十,關押一月。
兩人正在議論此事,突然管家徐忠奔上樓來,高聲叫道:“少爺,大事不好了。”徐業成連忙問道:“老管家,何事不好?快快說來。”“那皇帝佬兒聽信陳浩讒言,說老爺的詩集多有反清詩作,派兵前來,說不放走一個活口,是要株連九族,少爺,這徐家的天塌下了,這如何是好啊?”徐業成年少,父親新喪,剛主持家務,從未經歷過這樣險惡的事,一時慌張失措,毫無主張,只能坐以待斃。
沈照和見此說道:“徐公子事已至此,你趕緊帶你兒子玉讀逃命去吧。”徐業成料到死路一條,官府捉的要犯是他,他又能逃到何處?他想只有自己一命送上,看官府能否網開一面,免他全家活口。他說:“沈爺爺,你趕緊躲開,這事不能連累于你。”
沈照和說:“少爺,你此言差也,這詩集是我收集刊印成書,哪能脫得干系,我這一脫身,不通情理,還不讓眾人恥笑?我死后亦無臉面見你九泉下的爺爺,我和你爺爺同為舉人,又是生死之交,徐家有難,我當共擔,也罷,我一老朽,與你一同赴死罷了,也可贏得老夫身后一世清名。何況是惡人誣陷,到了官府衙門,我還可以分辨一二。
少爺,快叫管家徐忠帶你兒子逃命,尚可保得徐家這點血脈。”
此時官兵正在撞擊院子大門,眼看破門而入,徐業成叫徐忠帶玉讀沿院內夾墻暗道,從河堤岸一叢水草遮掩的出口逃離。河岸出口處有一只小船,徐忠趁著夜色,沿茶河轉入通揚運河,在江邊尋一船家,過了長江,再轉陸路,投奔浙江天臺國清寺。方丈與徐業成有一面之緣,方丈為人仗義,收留了玉讀,將其撫養,傳授武藝。
六
陳浩從牢中放回,仍不甘心。他得知江蘇學政劉墉到了揚州。尋得徐天濤的詩集,連夜趕去揚州府,遞上訴狀。
劉墉連夜密折上奏。此時皇上剛頒發圣旨,查繳“違礙書”之際。
皇上接到劉墉的奏折,龍顏大怒:下令速將徐家等所有牽連之人一舉拿下,決不輕繞,以儆效尤。
官兵撞開院門,沖進大院,抄了徐家,徐家闔家老小數十口,全被關押,關進大牢,只等秋后問斬。沈照和也未能幸免,只逃走老管家和徐玉讀。徐天濤,徐懷鄉父子早已身故,仍按大逆凌遲律,銼碎其尸。
七
玉讀一騎絕塵,一路向北,午夜時分趕到江沙渡口,無船可渡,江邊停留,天剛拂曉,玉讀睡夢中,聽得人聲言語,一個鯉魚打挺,騰身而起。江邊船家已將擺渡,玉讀牽馬上船,到了江北,已是通州府的地盤,已離古茶鎮不遠。兩個時辰路程,玉讀隱隱約約看到那古茶樹,想必那就是自己的衣胎之地了。
玉讀直奔鎮東頭,古茶樹下,不由想起兒時在樹下游玩的情景,往事依稀渾如夢,都是兒時一點記憶。想來父母的墳也在附近,玉讀四下尋找,果然在樹不遠之處,那古茶河的拐彎處,一叢蘆葦掩蓋的河邊有一座孤墳,墳低得與地面幾乎打平,墳前無石碑,這墳不愿讓人發現似的,墳前植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柏樹。
墳前點著三炷清香,四樣供品,尚有半扎紙錢未曾焚點,想必上墳的人,見有人來躲開。玉讀供上四樣鮮果茶點,在父母墳頭插上一束從天臺山上采來的山茶花,磕頭跪拜,想起自家天大的冤屈,不由失聲痛哭。玉讀哭了好久,這才住聲。看那墳前還未點化的紙錢,想想這祭奠之人,還會前來。
沒一會,他果然聽到不遠處有輕輕的腳步聲,玉讀趕緊腳尖一點,騰身而起,人隱于墳邊柏樹的綠葉之間。只見一老漢,一步一腳小心翼翼地撥開蘆葦,看了又看四周,確定無人時這才走到墳前,點燃紙錢。老漢低聲自語:少爺,方才嚇死老漢了,每年清明老漢都來祭奠你和少夫人,老爺老夫人,更是想能在清明節遇上小少爺,小少爺算來也一十八歲了,當年徐家得以留下這點血脈,也是徐家不幸中的萬幸。
這一去已有一十三年,我與悟覺大師的約定也是該赴約的時候了,我年年來此就是盼著能見小少爺的一面,今兒這墳前有人前來祭奠,可不知是不是小少爺?小少爺啊,你何時才能來你父母墳前祭奠啊?老漢說著說著,不由老淚縱橫,雙手將墳前那石板上的浮泥抹去,露出一幅細微的雕刻,一個石鼓的圖形,與徐家宅前的那一對石鼓圖案一模一樣,只不過是縮小了點而已。原來這是塊讓人不會察覺的石碑。
這老漢正是送他去天臺國清寺的老管家,徐忠老漢。玉讀從樹上飛身而下,一個箭步撲在徐忠老漢面前,連磕三個響頭,口中叫道:“徐家老爹,是玉讀孩兒不孝,今日才來父母墳前祭奠,父母地下有靈,孩兒一定要報徐家這血海深仇。”
冷不防地從天落下一個人來,嚇得老漢驚愕不已,見這少年似曾相識,看看又很陌生,想想莫非真是玉讀小少爺,又不敢貿然相認。這時玉讀從地上扶起徐忠老漢,說:“徐家老爹,我是玉讀啊,你看看,我真是玉讀啊。”
“玉讀?玉讀!你真是玉讀,是玉讀小少爺!”徐忠細細端詳,當年五歲,一童孩,眼前玉讀已是一英俊少年,玉樹臨風,眉宇之間,透著一股豪爽之氣,與老爺徐天濤神色有幾分相似。徐忠情不能自己,抱過玉讀大哭。
玉讀哽咽地低聲應道:“老爹,真的是我,玉讀。”“老天有眼,不絕我徐家血脈。悟覺大師也未食言,這徐家復興有望了。小少爺你可知道,當年我倆逃得性命,你才五歲,我把你送到天臺山國清寺,就為的是能留下徐家的這點血脈,為的是日后徐家能有翻身之日。當年我與悟覺大師相諾,他將你撫養成人,教你武功,十八歲送你出山,這一期間,不得向你透露半點身世,我也不得去天臺寺看望于你,不得打探你半點消息,以防官府捕快知曉。這十三年來老漢每天每時都在盼著你回家,今天見你,老漢死也無憾了,我徐忠終于可以報得老爺的知遇之恩。”
徐忠將徐家后事一一向玉讀道來,玉讀至此方知家中的悲慘遭遇。玉讀痛不欲生,立馬揮劍欲去砍下陳浩的狗頭,來墳前祭奠父母。徐忠攔下玉讀,說:“小少爺,不得魯莽,你初來乍到,不明情況,那陳浩也有幾分武功,身邊家丁保鏢眾多,你孤身一人,只能智取,你且在古茶鎮暫時住下,找一個謀生的行當,以遮人眼,再見機行事,到時我來幫你。”
八
古茶老街,商鋪林立,玉源昌南北貨商行,老字號的玉器店,劉復興的老酒樓,日常家用的老商鋪,顧家的老茶館,長安老客房,大大小小的店鋪,擠滿了整條街。
老街深巷,煙火人家,土著居民,端坐老茶館就著剛出爐的燒餅,慢啜細品明前茶,一口燒餅一口茶,滿嘴的芝麻香,口吐余香繞梁三日不絕,這是老茶客每日的早課。
三五老友,喝茶聊天,間或私下地說上幾句徐家的一柱樓詩案,感嘆世事難料,古茶鎮第一家族,中過舉人的徐家已是灰飛煙滅,如今陳家成為古茶鎮第一望族,家有萬貫錢財,良田萬畝。那年官司陳浩是贏家,扳倒徐家,堂兄賣給徐家的千畝良田也占為己有。
他家的深宅大院,前門臨街,后門出處即古茶河,高大的門樓,兩只威風凜凜的石獅子,氣勢壓人,院內庭院深深。分前院,中院,后院,院中花園假山,小橋流水,走廊回壁,曲徑通幽,宛如江南園林官宦私邸。
古茶鎮半條街都是他家房產,店鋪。陳浩還開得一家青樓,一樁甚是賺錢的買賣。只有他府門對面不遠處有一家不起眼的燒餅店,因其小,他沒想到兼并,這家姓李的浙江人做的燒餅實在好吃,他早上去自家茶館喝茶時,亦會叫李家送上幾個出爐的燒餅換換口味,品嘗品嘗。
那天中午,李氏燒餅店前走來一個衣服破舊,面色憔悴的少年。這少年饑色滿面,兩顆眼珠緊盯爐上賣剩下的兩只燒餅,咽著口水,在爐前徘徊,手掏著衣兜,又掏不出一文半鈔。
已是午飯時分,李掌柜呼兒媳婦共進午飯,見這少年這般窘樣,想必是囊中羞澀,多日未能飽腹了。
李老板為人忠厚,油然而生惻隱之心,見這少年外鄉人,倒有幾分憐惜,不由問道:“這位少年,是不是想買這燒餅?”那少年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摸了摸衣兜,轉身欲走。李老板上前一步,將那少年攔住,拉進店里,隨手遞上那爐上的兩個燒餅,說:“小伙子,我店也要打烊,這燒餅就送你吃吧。”
那少年遲疑了一下,禁不住肚腸咕咕直叫,伸手接過,來不及說聲謝字,狼吞虎咽,三口兩口大半個燒餅下了肚,只吃得口干舌燥,喉嚨冒煙,嗆得不輕。李掌柜端上一大碗水來,拖過一張條櫈讓其坐下,問起這少年何處人氏,為何到此?
那少年就著這一大碗水,吃完這兩個燒餅,緩了口氣,說道:“在下是浙江舟山人,姓余,名生。數日前隨父出海打魚,不料遭遇臺風,船翻落海,自己一人抱得一塊船板,在海上漂了一天一夜,才在黃海邊沙灘撈得一條活命,也不知父親死活。
身上已是身無分文,這兩天就近打個短工,混一口飯吃,掙些盤纏才能回鄉。今天無工可打,只得流浪街頭看能乞得一口飯食。所幸遇上掌柜心好,樂善好施,讓我得以溫飽,掌柜請受我一拜。”說著倒頭便拜,李掌柜連忙扶起,想了想,說:“余生,看你年少,如此不幸,海上打魚終究危險,不是長久之計。你不如跟我學得這門手藝,日后回到家鄉,也可混口飯吃。”玉讀一聽正合心意,連忙跪下,磕上三個響頭,嘴中喊道:師父在上,請受徒兒一拜。李老板見余生乖巧,心中也是十分歡喜。當下,叫余生洗漱收拾一番。余生換了一身粗織的家常布衣,洗盡臟污的面孔,倒是一表人才。
九
這玉讀在李家落戶,白天早起生爐,燒水,學著做燒餅的手藝,晚上則睡在店里,看守門戶,空閑時在街頭逛逛,走街串巷,實則暗探地形。
那一夜,月黑風高,街面烏燈熄火,玉讀蒙頭遮面,穿過小巷,去了自家的老宅。徐家大院已被官府查封多年,老宅破舊,野草叢生,一片荒疏。大門封閉,只落得個兩枚石鼓依然守著那兩扇銹跡斑斑的院門。
玉讀手撫石鼓,想起兒時趴在石鼓上和姐妹戲耍的情景,不由心中一陣酸楚。玉讀騰身一躍,越過院墻,沿木梯盤旋而上,登上一柱樓頂,全鎮一片烏黑,不見一點燈光,唯有那陳府燈火明亮,隱約聽見歌舞之聲,陳浩還在尋歡作樂,玉讀憤怒不已,揮劍在粉墻上寫下:“必殺陳賊,重振家業。”八個大字。
玉讀在店里干活,兩眼時時盯著對面陳府大門,打探陳浩的出入狀況。一天,陳浩叫李老漢送一爐燒餅去他家茶樓,李老漢趕緊提著食盒前去,玉讀連忙拉住,說:“師父,讓徒兒送去。”李老漢說:“徒兒,這陳老爺為人惡狠,你可不好應付,還是為師送去為好。”
“無妨,徒兒也想看看這陳大官人是何等模樣,也讓徒兒長長見識。”
“那你可得多加小心,不可多言,快去快回。”
“徒兒知曉。”玉讀拎起食盒一路小跑而去。
玉讀走上茶樓,陳浩見是一個面生的小二,有點生疑,不由問道:“你是何人,你家李老頭為何不來送燒餅?”玉讀低頭回道:“回大老爺的話,在下是李掌柜的遠房親戚,浙江舟山人氏,余姓。因家中貧困,故來他家,學個手藝混口飯吃,此時我家掌柜分不開身,故叫小的來送燒餅給大老爺您品嘗,不敢耽誤。”陳浩聽這小二一口浙江口音,也沒再問。
玉讀彎腰后退,眼角余光瞄了瞄陳浩。那陳浩生得肩寬體壯,兩道濃眉,圓環暴眼,一臉的落腮胡子,一副惡漢的兇樣。
玉讀剛轉身走人,突然聽到有人喊道:“徐家小少爺,留步。”玉讀一驚,喊他徐家小少爺?叫他不要走。莫非陳浩認出他來?玉讀強作鎮定,裝著不是叫他,一步跨過門去,那門口保鏢把刀一橫:“小二,聽到沒有,我家老爺叫你留步。”“喲,小的不知,小的以為老爺叫的旁人,原是你家老爺叫我。”玉讀轉身面向陳浩,問道:“老爺,又有何事吩咐小二?”
原來這陳浩總有一塊心病,則是當年逃走的徐家小少爺。心里擔憂當年斬草未能除根,萬一這徐家小少爺,長大成人,找他報仇,不可不防。這些年他一直四下打聽尋找徐家小少爺的下落,卻無任何音信。
剛才他看到這小二,有一種似曾相識又想不起是誰的感覺,這小二年紀也和徐家小少爺相仿,讓他有點生疑。不由他喊小二為徐家小少年,試探一下。陳浩說道:“小二,我是想問你今年多大年紀?”
“回老爺,小的今年已二十有二。”“那你可曾婚配?”“老家曾說了一門親,只是家中貧寒,只得拖到年底,看能否掙點銀子回家完親了。”“原來如此,那好,你且回罷。”
出得門去,玉讀驚出一身汗,心想好險,萬一被這老賊認出,這仇如何能報。看來這老賊心辣手狠,防范其嚴,出行都有保鏢家丁護著,不得近身,難以行刺,只有暗中智取了。
這天下午,玉讀聽得街坊閑談,說陳浩又搶了一少女,關在青樓逼其賣身接客。這女子性子剛烈,寧死不從。陳浩十分惱火,準備明晚親自上陣,為其開苞。這青樓新人進樓,如是少女,嫖客開苞,得付百兩嫖資,這是陳浩一筆不菲的進項。陳浩好色之徒,不少少女被他糟蹋。玉讀心想明晚確是個極好的機會。
十
當晚深夜,玉讀一身夜行服,潛入青樓,青樓已熄燈安息。唯有三樓最東首一間房里,尚有一絲燈光。玉讀即奔那房而去,玉讀隱身走廊檐下,透過梁柱間縫看到一個十五六歲樣子的少女,低聲抽泣,站在一張圓凳上,兩手往屋梁套一根白絲帶,把頭伸進絲帶。眼下救人要緊,玉讀用劍撥開門閂,推開房門,這時那女子已蹬倒圓凳,身懸梁上。玉讀上前一步,揮劍、帶斷、人墜。
玉讀雙手托起女孩。那女子緩了口氣,睜開眼睛,哭訴道:“官人,你這何苦,救我這苦命的人,還不如讓我一死干凈。”玉讀勸道:“你這小小年紀,世上的路還有多條,何必輕生。”“官人你有所不知,那陳浩老賊心狠手辣,我父生病去世,家中貧困,無力償付田糧租金,他逼我賣身,我誓死不從,他竟然要在明天夜里強暴于我,我豈能讓他污我清白之身,不如一死抵命。”
“不可,不可。”玉讀說道:“你這一死,那老賊毫毛不損,你我與那老賊都有新仇舊恨,你且助我殺了這老賊,我報了家仇,你也脫身,豈不更好。”玉讀在那女子耳邊低語:“明晚你可……”那女子點頭應允。
十一
斯夜,玉讀一身緊身短靠,蒙了面罩,來到青樓后院門口,足尖一點,三步二步躍過院墻,在墻上稍一借力,飛上那銀杏樹枝之巔,“吱”的一聲,這三彈三落,已落青樓三樓房頂,只等那女孩把陳浩灌醉,就好下手。不料陳浩行伍出身,行事精細,不肯多飲,只喝得微醺。
一時淫邪,強暴那女孩,女孩不從,又哪能抵抗得了,女孩上衣已被撕破。玉讀眼見那女孩子即將遭殃,撞開房門,一個箭步上前,一道劍光直指陳浩面門。陳浩大吃一驚,想不到這溫柔之鄉,花好月圓之夜,竟有行刺之人。
陳浩躲過劍鋒,抄起身邊的一張木椅抵擋,玉讀寶劍何等鋒利,削鐵如泥,一劍削得木椅四分五裂。陳浩赤手空拳和玉讀斗了幾個回合,招架不住,一個虛招,退到一邊,從那墻上取了那隨身的佩刀迎了上去。
一時二人你來我往,刀劍相擊,叮叮當當。那陳浩一身武藝,身手不凡,二人見招拆招,一時難分高下。此時陳浩只想脫身,虛晃一刀,奪門而逃,從樓上走廊一躍而下,玉讀緊隨飛身落地,兩人在大廳斗殺。
陳浩的兩個保鏢聞聲而來,掄刀就砍,玉讀面對三人毫無懼色,長劍抖動,一招“梅雪爭春”,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劍尖劍鋒齊用,劍尖是雪點,劍鋒乃梅枝,寒光點點,似片片雪花在那三人身邊飛舞。
四人你來我往,一時殺得難分難解,玉讀心想不可與其糾纏,還得速戰速決,賣個破綻,一黑衣保鏢貪功心切,不知是計,獨自把刀砍了過來,玉讀一個閃身,讓過,順勢一劍,一招“隨風擺柳”便削了那黑衣保鏢一條腿,那男子一聲慘叫,敗下陣去。
陳浩見勢不妙,轉身就往大門外逃去,玉讀緊追上前,一保鏢攔了上來,玉讀讓過身子,回手一鏢,那保鏢“卟”的一聲倒地不起。
這時陳浩逃到大街,向自家府院逃去。玉讀施展輕功,沿店鋪屋頂飛行,趕在陳浩府前攔住陳浩。陳浩見刺客蒙面,不由問道:“你是何人,為何殺我?”玉讀一聲冷笑,扯下蒙面,說道:“陳浩老賊,我是徐玉讀也,今日為我徐家大小數十條人命,來取你的狗頭,以報家仇。”陳浩大吃一驚,這小子竟是十三年前逃了性命的玉讀,恰是送燒餅的小二。
一場惡戰,陳浩使一把月牙寶刀,刀背上鑲有一串鐵環,實為暗器,舞時叮當作響,讓人眼花,不經意間環脫鐵鉤飛彈傷人。那刀厚背薄刃,烏黑锃亮,鋒利無比。玉讀使一把長劍,這劍看似細長綿軟,卻似拂塵,可刺可彈,刺時如針,彈時似鞭,這劍又如一支毛筆,橫側豎捺點劃,如狂草行書,筆走龍蛇,隨心如意,一旦發力,加以內功,這劍鋒電光石火,瞬息萬變。
玉讀自小在云臺山,碧霄宮內悟覺大師門下學得一手好劍法,練就童子功,悟覺大師親授內功秘訣,武藝高超。
二人你來我往,多少回合,不見高下,玉讀招招緊逼,陳浩見招拆招,一一化解。玉讀劍舞得梨花朵朵,雪花片片,寒星點點,陳浩刀刀黑氣騰騰,虎虎生風,上下呼應。一時白與黑,劍與刀交相斗法,纏在一起,那劍如靈蛇吐信,刀如黑龍噴焰。
玉讀憑一身童子功,纏著陳浩,步步緊逼。驀然騰空一躍,從最高處俯身揮劍,一招“仙人指路”直指陳浩眉心,陳浩一招“對空望月”刀護額前,手腕一抖,那鐵鉤上圓環脫鉤彈出,向玉讀胸前飛去。
不料玉讀是虛晃一劍,讓過那飛旋的鐵環,一個“千斤墜”,硬生生地從空中墜落,腳尖一點,向前一步,那長劍猶如靈蛇草上游走,竄至陳浩胯下,劍尖向上,直挑陳浩龍脈:寶貴疙瘩之處,陳浩后撤不及,情急這下,只得用刀架住玉讀的劍,趁勢借力身子向上一聳,已是離地三尺,躲過這一劍。
兩個高手,不差毫厘之間,不敢有半點分神。二人交戰,正在李老漢店樓之下,李老漢聽見聲響,在樓上看到二人格殺,見徒兒久久不能得手,情急之下,腳下恰有一只盛滿面粉的鐵筒,拎起鐵筒二話沒說,向陳浩頭頂夯下,那陳浩只顧應招,哪知背后樓上有人暗算,只覺得頭上一股風撲來,隨手用刀一擋,哐當一聲,那鐵筒被刀擋出丈外,不料擋翻的那一筒面粉迎頭潑下,好似漫天大雪紛紛而下,淋得陳浩滿頭滿臉,糊了兩眼,眼前一片模糊,只得把刀舞成一樹梨花,以護己身。
玉讀何等聰慧,手疾眼快,一個燕子掠水,人已飛于陳浩身后,回手一劍刺中陳浩后心,陳浩“啊”的一聲,當即倒地身亡。玉讀上前一劍削下陳浩的頭顱,雙手向樓上師父雙手一拱,低聲說道:師父保重,日后再相見。玉讀本想再去陳府殺人,想起悟覺大師曾吩咐,不可濫殺無辜。隨即轉身往父母墳墓奔去,那徐忠早已備馬等候,兩人用陳浩的人頭奠了玉讀父母,上馬離去,一路南行,向那天臺山而去。
十二
翌晨,官府聞信,查驗現場,在郊外河灘發現一墳前有陳浩的人頭,猜想是那徐家的唯一逃脫的玉讀回來報仇,張榜懸賞捉拿人犯。
時過二年,嘉慶當政,大赦天下,對徐氏《一柱樓詩》案,予以平反。玉讀和徐忠回歸故里。玉讀見過師父,感謝當年恩典。那李老漢見徒兒竟是徐家后人,心中更是歡喜,情愿將小女嫁給玉讀。玉讀見師妹長得越加美麗,十分喜歡,二人成婚。玉讀和岳父一起開店,店名為:《一柱樓燒餅店》以此紀念徐天濤祖父。日后玉讀多有子孫,開枝散葉,人丁興旺,徐家重振家業,又成為古茶鎮一大家族。徐家后代均有一家繼承祖業,一柱樓燒餅傳承至今。一柱樓燒餅店面墻上寫有這燒餅店的由來,一柱樓的家事。
如今一柱樓燒餅聞名遐邇,人們品嘗著這可口芳香的燒餅,聽導游講這一柱樓的故事。
責編: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