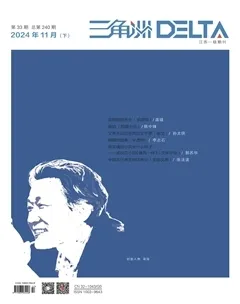瑞姑
1
瑞姑從盧莊回娘家是在1948年秋。
那年的秋天似乎特別濕冷,剛過中秋便是連續霜凍,沒有風,但涼意入骨,人們早早地穿上了夾棉衣。
一場寒雨之后,國共兩軍在河汊交錯的鬼頭街對壘。是役,瑞姑的丈夫盧吉生時任國軍“猛虎團”團長,茲為前部,守衛橋頭陣地,遲滯解放軍合圍通州城。大戰在即,解放軍“老虎團”政委盧恒生拿著喇叭挺立在陣地前喊話,他沒有做任何防備,因為對面是自己的堂哥和他率領的兄弟鄉黨。而且,敵對兩部在抗戰中曾經精誠合作、縱橫馳騁,是冮北平原上令倭寇聞風喪膽的“龍虎雙雄”。
但是,恒生還是被對方的冷槍擊倒了,再也沒有起來。
第二天,乃是多日陰霾之后的第一個晴天,天高云淡,暖陽當空。解放軍“老虎團”上下,氣氛卻顯得沉重和悲壯,陣前,他們收殮了政委的遺體,幾位首長為之執紼抬棺下葬。新墳落成,同樣是一群西鄉子弟兵腰扎白布,赤膊上陣,怒吼著沖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陷了敵陣。
吉生所部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斗志,一觸即潰,“猛虎團”成了“老鼠團”,頓作鳥獸散。
瑞姑得知丈夫與堂弟戰場對陣的消息,恐懼、悲哀和慚愧一直在內心盤桓不去,因為這兩人是發小、是族人,也曾是肩并肩的戰友,如若刀槍相見孰勝孰負都是悲劇。
然而,不該發生的事還是發生了!
戰役完勝后,解放軍首長仍然發出雷霆之怒,誓言要活捉匪團長為烈士報仇!
多少年來,瑞姑總在為丈夫擔驚受怕。這“殺頭的”時而杳無音信,時而死而復生。這次,多方打聽,他似乎又是逃脫了厄運。
瑞姑再次撐起了一線的希望!
江北很快解放了。盧莊的老宅成了解放軍渡江南征的總部。一時間,門前人來車往,絡繹不絕。人們對偏居一隅的“匪屬”瑞姑們當然沒了好臉色。冷落、怨恨和不屑的神情彌漫在瑞姑周圍,擠壓得她喘不過氣來。
此時,瑞姑想起了長江邊的娘家,她想去那兒靜靜地等待丈夫的音訊。
等待,等待,自從進了盧家,就一直在等待。
瑞姑內心常常泛起憋屈的酸楚。
2
江邊,原來只是一大片的灘涂。那里瘋長著蘆葦和此消彼長的蒲黃。從江堤上望去,遠處是亮晶晶的水,近處有一垛一垛的綠,季節更替,那些綠會漸變成黃色,爾后又會變成由蘆花起伏的霧白。
瑞姑的娘家就在江邊。
那里,江堤很高,腳下漸遠的江灘中有一泓清流脫穎而出,虎行龍游,直奔岸堤,在那里盤桓出半月形的深水潭,又擺尾東去,另辟蹊徑,匯入主流。
堤邊水潭就是小有名氣的水龍口。多少年了,不管是細流雕琢,還是大浪淘沙,這里的江堤都沒有潰塌或變形。傳說那下面是龍爪。由此,堤岸上的村落才得名為龍爪村。
龍爪村是江堤的后延,地勢高低有致,為長江沖沙成陸時的高沙土地貌,當地人稱之為“原”。原上散落有幾十戶人家,那片磚墻小瓦的房廬被綠樹掩映,露出屋脊兩頭如飛一樣的翹角。
母親離世時將一處小院留給了瑞姑。院前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樹,樹下有一眼雕欄古井。院子前排三間為穿堂門和左右廚房、庫房,后排為五架梁臥房和廳堂。院子不大,在不同的方位植有梅蘭竹菊,緊湊而且別致。
院子由娘家兄弟們幫忙收拾,正房給瑞姑母女倆居住,前屋左右分別安頓了和尚和他父母,忙碌了兩天才安頓下來。
瑞姑的女兒叫思思,正是總角年齡,寅虎年在縣城出生,那時的古城還在日寇的刀槍之下,被恐怖和血腥籠罩著。父親吉生得悉喜訊,潛入城內陪伴娘倆三天。據說,進城時很兇險,鬼子正懸賞拿他。在城門口兩個穿黑色制服的人幾乎要將吉生當嫌犯抓起來。恰巧吉生的荷包沒扎緊,忽然嘩嗶一下漏出了一串大洋,才被果斷地放進了城,臨走,那黑制服還不經意地說;“城里的石板路好久沒修了,當心。”
思思這名字是父親起的,因為他與瑞姑離多聚少,應該是一種情感的表白。
和尚和他父母已經伴隨瑞姑多年了。
和尚是瑞姑男人的發小,兒時,上樹下河,捉鳥摸魚,形影不離。早些年,盧家老爺被暗害,他們正值弱冠。吉生執意從軍。和尚三番五次要跟著去軍營,都被拒絕了。后來他終于明白了吉生的良苦用心,便一心一意地留了下來,在盧家大院幫著料理事務。
和尚對瑞姑母女的照應很是用心。自瑞姑孕期,就讓他父母搬進盧家服侍照料著,這次瑞姑回娘家靜養,他們當然伴隨左右。
鄉間的日子過得安靜而粗糙。漸漸地,瑞姑也開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的周遭境遇完全顛覆,富庶和優越成為過往,自食其力是每個人的正常生活。
盧莊的大宅在大軍渡江后進駐了土改工作隊,后來就改成了小學校。
那里,再也不能回去了。
和尚在心里長長地慨嘆著。瑞姑沉默不語,內心隱隱覺得對不起盧家。
亡命于孤島的反動派似乎緩過氣來,忽然叫囂反攻大陸,大陸的那些反動遺存也開始蠢蠢而動,妄圖里應外合。遙相呼應,大有卷土重來之意。于是,一場稱之為“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開始了。
聽了村頭喇叭里的循環廣播,瑞姑有些怕。那“殺頭的”丈夫一直杳無音信,外面傳聞他跑去了臺灣,最近上面又經常有人前來問話,讓人惶惶不可終日。尤其是那些與瑞姑幾乎一樣的“匪屬”,都被一一定性為“反革命”了,這非同小可的“帽子”足以讓人“永世不得翻身”。
“您是行善積德,必有福報,不會有事。”和尚心里也沒底,絮絮叨叨,語無倫次地安慰她。
和尚暗暗托人去打聽,有消息說,瑞姑的男人盧吉生是個血債累累的還鄉團反動派,原以為不知所終,沒有歸案,現在終于搞明白了,的確是逃去了臺灣!瑞姑就是“匪屬和地主婆”。
和尚很是沉重,而瑞姑卻暗暗地松了一口氣:那“殺頭的”沒死!
3
躲不過的一天不期而至。
那是在掌燈時分,區里來了幾個全副武裝的年輕人,砰砰砰地打門,門一開,便雄赳赳氣昂昂地魚貫而入,因為人多,擠得將院子里面的菜地踩成了一地雞毛。來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著瑞姑就要綁走,嚇得女兒拉著她的衣角大哭起來。
“小兄弟,我想換身衣服跟你們走。”瑞姑顯得很冷靜,其實換衣服是個借口,是想拖延時間。
“姑娘不怕,等下爺叔他們會過來的,聽話。”思思聽了娘的話,果然止住了哭聲,怯生生地偏到一邊。
那個領頭的有些面熟,瑞姑覺得是盧莊的鄉黨。他的聲音很大,說道:“可以,但可別耍花招呀,乖乖地跟我們走就免了捆綁的苦,還有,你不老實就帶你女兒走。”
“不會,我只是換身衣服。”
“一個國民黨反動派的家屬臭美什么。”同行者中有人提出異議,被那人給粗魯地擋了:“里外都是我們的人,她跑不了。”
從里屋出來時,瑞姑果然把自己整理得很清爽,正好和尚他們聞訊趕到,卑微地在一旁站著。瑞姑點了點頭,沒說話,只是看了看女兒,很快被人扭著出了門。
瑞姑的女兒踡縮在一邊瑟瑟發抖,和尚訥于言表,只是小聲地重復著:“沒事的,沒事的。”
他想,這簡單的撫慰也許能夠平復她幼小的心靈。
天亮了,和尚惴惴地出門打探情況,來來回回,最終,一位在區里跑腿的表親悄悄說,這次公審要鎮壓罪大惡極分子,據說與盧家有關聯,又說,瑞姑此去可能只是站臺“陪綁”。
和尚稍有安心,轉而又在揣測那要被“鎮壓”的盧家人,他是誰呢?真有些迷茫。
公審大會是在高莊東河南的一處剛平整好的荒墳地上開的。
那片地大約有三百來畝,四周長著稀稀疏疏的亂草和雜樹,中間卻是斑駁崎嶇的泥垛。西側不遠有一條小河擦邊而過,其實那不是一條河,是一段狹窄的斷壑。旱季,那里沒有水流,只是大地的一條裂縫。在雨季又成了一條湍急的河流,由此,人們稱那里叫裂河口。
裂河口不知何朝何年成了西鄉的一塊公共墓地,里面的尖墳土丘層層疊疊,夜幕降臨多有野狗猢獐出入,梅雨時節,天色漸暮,磷火便隨風出沒,綠光點點,被無形之手東拉西扯,著實讓人恐怖。
這次,區公所動員了上千人,人拉肩扛,十幾天就讓這里平整通達,還搭了簡易的臺子。
吩咐好爺娘,安頓了孩子,和尚早早往裂河口,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他拼了全身的力氣向前擠,想靠近瑞姑,告訴她別害怕,只是“陪綁”。但,硬擠到看到瑞姑的地方就再也不能向前了,和尚歇斯底里地揮手!心想,靠近了,瑞姑若見到自己,一定會心安一點點。
遠遠望去,臺上就端坐了幾個人,其中有個人站起身,用硬紙板卷成的喇叭喊了幾句話便押上了七八個人,其中有瑞姑,她頭頂著紙糊的高帽,兩邊還有幾條飄帶,單薄的身子被后面兩個女民兵撳得半彎著,如風雨飄搖中的白無常。
轉眼間,和尚猛然揉揉眼睛,伸著頭向前探著,那不是胡叔嗎?
胡叔沒了過去的精氣神,頭發和胡須稀稀疏疏,已全然白色,眉眼低垂,神情沮喪,長衫已經被撕破了,而且有些邋遢。
胡叔是盧家城里的管家,與盧家老爺子盧敬齋是叩頭兄弟,多少年了,一直在縣城為盧家照顧生意。
胡叔不是跑得沒影了嗎?連他兒女都不知道去向。怎么被抓了?前幾年,戰事頻頻的時候,和尚被瑞姑派去找過他,就是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臺上的人聲音忽然加大了,語速很慢,但鏗鏘有力、斬釘截鐵。臺下的人群激憤起來,高呼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口號,不自覺地向臺前涌,但很快被主持人制止。
只看見那些被宣判為“罪大極惡者們”被一群人簇擁著押了下來。和尚看到,胡叔則是被兩邊的人叉著,兩腳拖在地上,幾近騰空,人們如決堤洪水涌向臺后,緊接著便聽到“砰砰砰”的槍響,人群戛然而止后,又席卷回流。
瑞姑在那高高的臺上起初很恐懼,幾近昏厥過去,漸漸地,她又似乎被臺下群情激憤的呼號給喚醒了,她聽到了胡叔的名號,于是倔強地向兩邊扭頭,努力用余光搜索,卻什么也沒看見。
4
此前,瑞姑有些恨胡叔,盧家城里產業和上學的幾個子弟一直由他管著,每年還給送些用度。可在吉生兵敗逃亡后不久,他就沒了影,連個交待也沒有。
應該是胡叔卷走了不少錢,瑞姑一直這樣認為。
胡叔很慘,被人從背后打了好幾槍就是不死,臨了,還回過頭對那個打槍的民兵講了一句“要求快”才緩緩趴下。嚇得行刑者大驚失色,呆若木雞。
在和尚將胡叔的亡命故事敘述結束后,瑞姑卻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之中。
胡叔逃遁在杭州,在離西湖不遠的后街背巷開了個雜貨鋪,以為營生。剛開張時小店生意很繁忙,胡叔也還能兢兢業業。
漸漸地,他有些厭倦了。
在街上“淘”得一張通州制作的柞榛木搖椅,用核桃油擦得錚錚亮,冬天墊上狗皮褥子,夏天扣上藤席,側邊放個茶幾,用宜興紫砂壺泡上釅茶,躺上去搖一搖,再唱個茉莉花調調的小曲,抑揚頓挫,從里到外地自我陶醉。
如此這般的愜意,生意好差無所謂了。有的時候還干脆將店門關了,優哉游哉地去晚店逍遙聽曲兒,全然不顧買賣。
喝酒的毛病自然沒改,喝高了,老是講一句話:過去我比現在闊綽多了。人們覺得,這個人不只是過去闊綽,就是現在,每天吃吃喝喝,醉醉歪歪,就不能是一個窮出身。終于,胡叔被火眼金睛的人民群眾舉報出來,查了個水落石出。
和尚最后告訴端姑,那年胡叔不辭而別,是急急去上海與吉生匯合,他用帶去的金條打通了去臺灣的門路,但到了吳淞口才被告知只能有一人登上遠處的軍艦。
胡叔毫不猶豫地將吉生推上了駁船!
“殺頭的”又連累他人丟了性命。瑞姑長長嘆息,又在喃喃地念叨著:胡叔,胡叔。
5
從高莊裂河口刑場回到朱莊,瑞姑大病一場,她的頭一直被壓得很低,在黑壓壓的人群中當然不可能看到和尚,也不知自身的命運,死亡的威脅讓她瑟瑟發抖,幾近崩潰。瑞姑個把月都沒能起床,病殃殃了大半年。好在和尚父母的悉心照料才得以漸漸復原。
生活漸漸變得拮據狼狽,病疫和饑荒接踵而來。村里不停地有人離世。和尚的爺娘相繼全身浮腫,請村里的郎中來看,望聞問切多時,搖著頭走了。
果然,二老沒多久就離開了人世。
臨了,老母親與和尚斷斷續續講了兩件事。
他們說:“兒子,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你都四十多歲了,該找個媳婦了。”和尚“嗯嗯”兩聲,沒有點頭。
娘最后喘著氣說,東房地下有兩頭大缸,里面有些陳糧,夠你和瑞姑她們娘兒倆渡過難關。
爹娘真是神人。似乎算準的,后面兩三年,天大旱,人大干,民大饑,生活異常艱難,多年不見的餓殍重現。
深秋之夜,一場寒雨到來,嘩啦啦地澆下來,如七月驟雨,接著,一陣大風旋轉著推波助瀾,仿佛吹奏了一曲“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讓和尚住的前院房飛了頂,塌了墻,幸虧他跑得快,差一點被壓在里面。
和尚狼狽地裹著被子在瑞姑房前的屋檐下挨到了天明。
瑞姑開門時,見到了這狼狽的情形,心疼不已,說,你搬來后院房住吧。
和尚拒絕,瑞姑又說,你住西房,我和思思住東房,大家也好有個照應。言語之間思思拉著他進了門。
和尚無可奈何地點點頭,允了。
這樣,他們儼然成了一家人。生產隊的隊長和會計說,就把你們家的工分記在一起吧,年終一起結算分糧。
瑞姑有些猶豫,女兒思思爽快地說:“行!”
思思已經成年,在生產隊掙工分了,征求了瑞姑的意見,小學校的老師給她起了個很有時代感的名字:朱向紅,讓她隨了瑞姑的姓。
和尚無話可說。
龍爪村的人都覺得這樣做是順理成章的事。
6
1988年春,正是人間四月天。水龍口的江堤上開上來一輛轎車,走下來一位老者。
他靜靜地站立在江堤上,遠處,滾滾長江東逝水,白帆競發,百舸爭流。那里有一條九曲牽繞的細流,漫不經心地而來,直到腳下的水龍口,然后又擺尾而去,向東方穿過草甸,匯入主流。
在灘涂上自由行走的是風,初起時葦草搖曳,漸漸地便是綠陂瀲滟,再起時,又會狂飆突起,有如野馬浴河,縱橫馳騁,蔚為壯觀。
幾十年了,眼前的一切依然如故。
白發飄飄的老者就是瑞姑的丈夫:那個死里逃生的國民黨反動派團長。他來自臺灣。
遠遠地,瑞姑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身板挺拔,下鄂微微上翹,還是一副自信自負的模樣。
吉生也看到了瑞姑。一位鄉下老太太逶迤而來,個兒不高,身形單薄,頭上梳著一個盤起來的角子,走得輕快,像是飄過來的,眨眼間就來到了眼前。
四目相對,瑞姑幽怨彌漫,悲哀迸發。她狠狠地甩開了已然相握的雙手!
“叭”一個耳光,讓眼前這個刻骨銘心的“殺頭”向后打了一個踉蹌。
瑞姑被反作用力推倒到一邊,掙扎著,爬不起來,身后的那位農婦搶上一步,將她扶到一邊。
“父。”農婦扶好瑞姑,一下跪到吉生腳下。
吉生一點都沒反應過來,呆呆地立在一邊,不知所措。
還是跟上來的一位長者扶起了她。
“吉生兄,她是你女兒思思呀!”和尚認出了吉生,他的聲音有些顫抖。
吉生面對和尚時有些猶豫。
他不知道與他怎么說。他從熟識鄉黨那里知道,思思叫他爹,思思的兒子叫他爺爺。
吉生憋著,又想,自己離開四十年了,在高雄早就另有家室,沒有權利指責別人。
和尚感覺到了兩人的距離,他望著眼前這位發小,淡淡地說:“這些年你還記著我嗎?”
“記得,夢里還見你甩著胎毛辮子。”吉生緊握著他那粗糙的手。
和尚笑了,他慢慢脫去藍色的舌帽,露出了一綹白色的辮子。
和尚輕輕地拍著辮子,說,我們都老了,伢兒時記憶中的昨天就在眼前呀。
那辮子已經很細很小,濃縮成如小楷的筆尖,掛在后腦勺,有些顯得孤獨,又覺得很倔強。
吉生愣了一下,面對三人,沉默著,心中卻如電閃雷鳴般震撼。
瑞姑被思思扶到一邊,低頭啜泣。
和尚有些佝僂,滿臉的皺紋縱橫回轉,如爬滿的藤蔓。
吉生聽人說瑞姑母女與和尚在一起過了。但現在真沒想到……
吉生打小就知道,和尚之所以叫和尚,是因為出生時身體虛弱,爺娘去廟里拜佛求簽問道,師傅說收不住,寄廟可長一些。
和尚爺娘舍不得獨苗入廟苦修,才遵從指點,取名和尚,而且留下了一撮胎毛。師傅說那一撮胎毛等他娶親成家時必須剃去,否則,婚姻和人生都不得久長。
唉!為了瑞姑母女,他沒有婚姻,沒有向世俗解釋,而是默默地為了那心照不宣的諾言奉獻了一生。
吉生意識到,因為自己,親人和朋友們才有了這艱難甚至絕望的人生境遇。
父母的墓地就在小學校的西河邊,墳早就平了,沒了墓碑,周邊有一些棘枝,這是后人做的記號,它不會長大,還在鋤后復生。
恒生的墓地在縣城的烈士陵園中,那石碑高高矗立,鐫刻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題詞者是一位開國元帥。
在恒生的墓前,吉生久久靜穆,他的時空輾轉輪回,思緒追遠。那年打黑槍者是參謀長的親信,不過當天沒多久參謀長也被打了黑槍,有人告訴他那人是恒生的表兄。
7
公元1990年秋,時維霜降,天很藍,深邃無邊;云很淡,綿柔如絲。
在瑞姑家的牌桌上圍坐著幾位老翁,吉生就在其中,他已經是第二次回鄉了。
吉生垂垂老矣,稀疏的頭發業已全白,前額不再是平坦和寬闊,而是爬滿了歲月的“年輪”。在這桌上,他已經沉浸快一年了,只要不出門觀光,沒有舊友訪客,午時過后,他們幾個老哥們必然在此聚會。
瑞姑在一旁端茶遞水。有時也停頓下來,靜靜地在吉生的身后看牌。
那牌有一百零八張,坐下來便是四國三方,循環三人對決,一人歇“莊”。牌局之中的三位分別將牌掌在手中。在你來我往之中,排列組合,奧妙千變萬化,情趣不可言傳。
在牌端印有些人獸圖案,那是一些《西游記》《東游記》中的人物,那上面的白描,勾線靈動,恰似現如今的卡通,讓人看著很親切。將每張牌的人物串起來就是一段愛恨情仇的故事。
那牌是刻在吉生心里的,有如媽媽的味道。有時,他從中看到自己的人生,看到活著的死去的父親母親和弟弟妹妹的命運。人生的喜怒哀樂和悲歡離合都在其中。
有一天,牌局正酣,他后面來了一個女的,齊耳的短發,穿著藍色的小西裝,拿著公文包。她站在身后好久,甚至還為吉生支招。
吉生回頭看看說:“姑娘,你面生呀。”
“我們見過,我幫您辦過還鄉探親的手續。”她微笑著,很親切。
“你找我嗎,有事?”
“沒關系,等等再說。”被吉生稱為姑娘的來人是縣公安局的,因為吉生的探親時段早過了,他就是賴著不走。
牌局結束時,吉生說:“姑娘,我能不走嗎?”
被稱為姑娘的人四十多歲了,在西鄉長者對后輩女子的稱呼就是姑娘。她不說話,似乎在看牌,又像是在微笑。
吉生知道自己必須走了,又要遠走天涯,遠去異鄉。
公安局那姑娘找了一輛公車,說:“大爹呀,政府專車送您。”吉生很開心。
女兒思思望著父親的航班起跑爬高,如孤雁一般漸行漸遠,直至消失。
年邁的吉生,此去無回。走時,八十有八。
8
瑞姑年過百歲才離去,臨走,囑咐思思一定要按照吉生留下的地址去看一看。
兩年后,思思的兒子飛抵臺灣。
高雄的街區已經很舊了,低緩的樓宇連綿而去,遠處便是海天。阡陌交通的道路并不寬敞,不時有成群結隊的黑乎乎的摩托從綠色的信號燈前呼嘯而過,母親曾經告訴他,在這座城市有外公的另一個家,有盧家的血脈傳承。
思思的兒子知道,外祖父應該早已作古了,但年邁的母親絮絮叨叨,硬要他親臨高雄看一看,希望他能夠見到與母親同父異母的長輩。
但他沒有見到任何親切的面孔,也沒有聽到那些想要的溫馨言語,因為人去室空,音信渺茫。幾經尋訪,終是沒有結果。
惆悵和遺憾之中,他在那幢公寓的醒目處留言:
盧吉生,江蘇省如皋縣西鄉盧莊人,1948年離開大陸定居高雄,1988年還鄉探親,回臺灣高雄后斷絕音信,今親人尋訪,有其信息者懇望聯絡。
盧氏家人,歸去來兮。
很可惜,至今沒有信息。
作者簡介:
陳中鋒,男,1962年生,江蘇如皋人,蘇州大學中文系畢業。擔任中學語文教師10年,后在黨政機關工作30多年。已發表小說、散文20多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