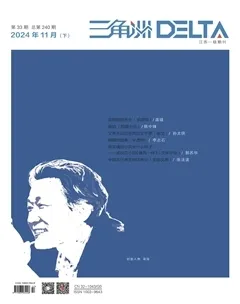鄉村圖書管理員
那時我的父親十七歲。趕往縣城圖書館的路崎嶇不平,也有點遠,來回足有十五公里,父親“鏘鏘”邁開大步,倒也不曾畏懼。路是堅實的,土地是廣袤的,生活是人們一步一步用腳丈量出來的。父親要去圖書館選書。選哪些書呢?什么類型的書大家會更喜歡呢?父親一路琢磨著,作為村圖書室管理員,他要盡到自己的責任。
新中國成立初,我國文盲比率高達80%,隨著全國“掃除文盲行動”的展開,這一比率大大降低。20世紀50年代后期,很多地方就開始克服困難著手建設圖書室以便人們閱讀了。那天村團支書拿來一個綠皮借書證,告訴我的父親讓他負責閱覽室書籍管理工作時,父親的第一念頭應該是,以后會有好多書可讀了。聽說父親小時候上學書讀得很好,我總是琢磨不透他后來退學的原因,一開始老覺得是因為父親年紀小吃不了在外上學的苦,到后來才明白他當時不能繼續讀書的原因很多。所以,父親接到這個任務時就決心要把這份工作干好。
父親帶著寫有村名的借書證第一次去到圖書館,看到那滿架的書籍時一定特別幸福。哪本都想借但又不能都借,就精選了二十幾本帶回來,寶貝一樣登記入柜,迎來了第一批讀者。他說:“那些工作人員現在也該很老了。”流水的光陰啊,現已物是人非。
父親把人們借閱過的書整理成兩摞,用繩子四面封好擔在肩上,就開始出發,走的應該是現在的山東路前身。一路西去,需要經過好幾條河流,碌碡溝河、沙墩河、香店河……那時候河上都沒有橋,平時流水潺潺只有幾塊高出水面的石頭供人通行。少年擔著書從河上經過,高大的身影映照在茫茫水面,冬去春來。“河水深且廣,風濤萬頃堪依”,書里記載的是歲月,腳下流淌的是少年對這方土地的熱愛。“河水積崢嶸,山雪晴索寞”,回首絲山舉目河山,山圍青黛四野遼遠,一路走來少年也當意氣風發。不是第一次去了,父親早先準備好了一個要借的書單。到了以后他把書交給工作人員讓他們查對書目,自己就重新去挑。
借到的書類型比較豐富,有大開本,也有小畫冊,先借的自然是一些早就有所了解的書。父親說那時也有說書人,在秦樓那里,他也曾去聽過故事。想那說書人“咣咣”敲過銅鑼,講《水滸》里那挑擔賣酒的漢子唱“九里山前古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楚漢梁山就都在那銅鑼的余聲里了。父親挑著書一路行走自然也會記起那些蓋世英雄,挑著《水滸》《三國》,就會覺得頗為英武,也并不管別人擔的是酒,他擔的是書。身高一米八的父親挺拔魁梧,有一年幾乎要成為一名海軍戰士了,最終又沒有去成。大開本《水滸》讓父親著迷也是有其道理的,現在父親想起讀《水滸》的日子,還仿佛意猶未盡似的。
另外古典的《三俠五義》《紅樓夢》、當代的《苦菜花》《烈火金鋼》等小說不一而足,小開本畫冊《岳飛傳》《李時珍》《林海雪原》等也有好多。我問父親看小畫冊多嗎?“有好書誰稀罕小畫冊?”父親不以為意的樣子。那書里的人生路千轉百回,父親擔著書走的卻是一條簡約樸素的鄉村小路。右肩累了換左肩,一個月兩三次,幾年時間就這樣來來回回,對一個少年來說寒來暑往真也算得上是餐風飲露了。
人們借了書就在簿子上做好登記。為便于管理,父親大致規定了借書周期,小冊子一般是兩天,厚本一般五六天,看不完的再來續借。如果到期還不來那就不能再借新書。人們大多很守規矩,看完了很快就還回來,在簿子上劃掉自己的名字,再借就重新登記。
也有例外,這天父親剛打開門準備整理一下書架,小新奶奶就跟來要借一本《林海雪原》。父親問上次借的呢,小新奶奶說沒看完,父親就很為難:“沒還上就不能借新書呢。”奶奶不舍棄,父親也堅持著,不承想沒一會兒小新奶奶就火冒三丈跳起腳來:“小新在家躺著,多看本書還不行了?”
父親這才記起小新生病在家,頓時紅了臉,就拿了《林海雪原》遞給小新奶奶。父親說這是唯一一次因為借書和社員產生的矛盾。
那時父親該有多糾結啊。很多時候我們都要面臨選擇,往左痛一分,往右也要痛一分,但又必須決斷。在矛盾中尋找平衡,年輕的父親也一定感到過壓力,也一定吃過不少苦頭。林語堂說過“近情的精神乃是中國文明的精華和她最好的方面”,人情與規則是一個復雜的辯題。面對著自己的鄉親,少年的妥協也是無可奈何。
這種選擇也算是四舍五入吧,那時的月色也冷清,我仿佛聽見那時的風一陣陣吹過屋頂,在昏暗的夜色里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
閱覽室設在大隊會議室的里屋,就是后來村中大社西邊的那一間商店。父親白天去技術隊勞動,只有晚上才打開閱覽室接待借書者。里面一張小床,晚上父親就住在這里守著這些書本。屋子里還有一張辦公桌,桌上配有一個罩子燈。說起罩子燈父親就眼睛閃亮,我清晰地感覺到那燈光曾如此長久地照徹了一個少年的世界。我甚至覺得在父親的眼里,那大概是世上最明亮的燈光了。盡管現在是不夜城,霓虹閃爍在每一片夜色里,隨時都會“花市燈如晝”,我仍然覺得在父親的眼里,那罩子燈的光亮無與倫比。
在20世紀的村子里罩子燈也是稀罕之物吧。所謂的罩子燈就是一種煤油燈上配一個圓玻璃罩子的燈,罩子遮著燈芯既能防風又相對衛生。那盞燈夜夜亮在閱覽室。生活的河流不停流淌,人們都會奔一盞燈而去。盡管有時離得還很遠,但畢竟那盞燈就亮在那里。一本書也許很薄很小,但捧在手里人們就會看到外面的世界,就會聽到外面的聲音。就算走不出去,你也會感知到這世界的溫度。對20世紀的普通百姓來說,這種閱讀尤其重要。拿過一本書有時也并不著急打開閱讀,它沉沉的,帶著墨香,自來就給人一種滿足。翻開書頁,聲音如此悅耳,那是一種舒緩的節奏。更別說那字里行間的光風霽月、柳綠花紅,人類歷史沉淀下來的智慧與美,就在這罩子燈下,它們被一一交到人們手中。
做圖書管理員是義務勞動,但父親樂在其中。父親說看書時間過得快啊,一晃就要天亮了。早先大家談及遇到問題要沉住氣,他來了一句“不可沽名學霸王”,當時我還奇怪老頭子都七十多歲了,竟然還能記著這么個句子,誰知道那時他有這段經歷。
來借書的大都是沒結婚的。結了婚就要忙于生計,基本上也顧不得看“閑書”了。還在上學的多是借小畫冊,不上學的多借厚本。小畫冊就是“文學小叢書”,這種書內容通俗,篇幅小又有插圖,很適合當時鄉村文化的傳播,俗稱“小書”,也被稱為“口袋書”。現在書越來越大,抱著讀起來倒也過癮,那時的口袋書幾乎都要成文物了。這些口袋書插畫精美,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那些密集的線條得傾注作者多少心血,能留存下來的也是很珍貴了。在當時,誰擁有一本小書那也是值得驕傲的一筆財富,所以閱覽室里的圖書總是很快就需要更新。
那時村子里人們物質生活還很貧乏,有人手捧一本書認真閱讀,或坐在田頭或蹲在樹下或靠在灶前,這種畫面是很溫馨的。不讀書,思想就會停止。街坊鄰居常說識文解字就通情理,講的就是這個簡單道理。這樣看來,年輕的父親挑著書擔走過的路,也算是一條汩汩流淌的文化細流了。
每到年底,父親都會匯總一下借閱信息去縣圖書館核對書目,哪些是社員借村里沒還的,哪些是村里借圖書館沒還的,都搞得清清楚楚。“勿以善小而不為”,水滴可以穿石,星火可以燎原,如果能一直把閱覽室開下去,那該多有意義。讓人嘆息的是,后來村里的閱覽室被取消,父親從此就不再去縣圖書館借書了。
作者簡介:
厲彩虹,高級教師,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日照市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