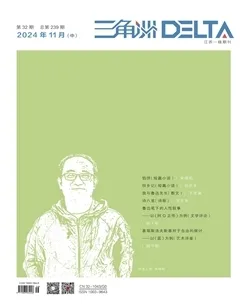回鄉記
所有回鄉的路,奔喪似乎成了路上唯一的主題。
——題記
一
回村的第三天下午,我在村口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他左手拎著一個旅行包,右手扛著一個鮮艷的大花圈,在疲憊地往前走。
近了,我喊了一聲三娃子,當時他就立在那里直愣神。我問三娃子:“你愣個啥呀,雖然十幾年沒見,但總不至于連發小都認不出來了吧?”誰知三娃子說:“不年不節的,你咋還突然回來了,這些年總打聽你,每次回來都見不到你,你說我能不驚訝嗎。”
我問三娃子:“你這是給誰扛的花圈,你家和我姑父也不沾親帶故啊?”我的話音還沒落地,三娃子的淚珠子就先掉了一地,原來,他爹昨晚過世了,接到他娘的電話后他就急著往回奔。
這事我還真不知道,得知我姑父去世的消息后,回村后的這三天我一直在十里八村給親戚們報喪,下午好容易都報完了,就跑到村口來溜達,沒想到遇見了三娃子。
“鎮上離村里這么遠,你咋還走著回來了呢?”我問道。三娃子馬上換了一張臉:“這幫窮鄉親,活該伊拉(他們)受窮,鄉里鄉親的,一點情面都不講,唔(我)都跟小貨車司機說了,阿拉(我們)是鄉親,唔老家就是這個村兒的,儂(你)不要宰客,可伊(他)一聽唔說上海話,非要朝唔要50塊錢。唔呸,在阿拉上海,這么一小段路程頂多也就20塊錢,如果坐公交車,兩塊錢就搞定了。”
我說:“都什么時候了,你還置這個氣干啥,趕緊回家吧。”這時,三娃子一臉痛苦的表情:“啊呀,唔的膀子酸死了,幫唔拿一下吧。”我去接三娃子左手的旅行包,誰知他卻把右手的花圈塞給了我。在我們老家,這是習俗,只要是奔喪,都得帶個花圈,以示對死者的哀悼和尊重。
剛走幾步,就遇到了我本家的一位親戚,他問我:“不是已經給你姑父買花圈了嗎,咋還又買了一個呢?”我說:“這是三娃子的,他爹昨晚沒了。”本家親戚很吃驚:“這么大的事,咋一點兒動靜都沒聽到呢?”親戚說著看了一眼三娃子:“這娃子不是在上海混嗎,大城市的生活那么滋潤,人咋還瘦成了這個樣子?”三娃子說:“唔不是在上海混,是在上海定居,儂沒去過上海,不知道上海的男人都是唔這個身材。”
本家親戚一搖頭,轉身走了。我對三娃子說:“回了村就別說你那上海話了,小心挨村里人罵啊。”三娃子嘴一撇:“唔說上海話已經習慣了,回到老家還真不適應。”我說:“課本兒里你又不是沒學過,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你這才走了十幾年,就連家鄉話都不會說了?”三娃子說:“會,但好歹唔是從上海回來的,村里人有的還不知道呢。”
“還說,知道了又有個屁用啊,除了你爹娘誰能沾上你的光。”我這么一說,三娃子就不再吱聲了。到了三娃子家院門口,本以為家里應該亂得一團糟,誰知卻靜悄悄的,一個人不出氣兒了,搞得全家人好像都不出氣兒了。我把花圈放到了院子里,正要走,三娃子他娘隔著玻璃叫我,雖然聲音很微弱,但我還是聽到了。
進了屋,三娃子他娘拉著我的手,鼻涕一把淚一把就哭了起來。偌大的院子,這才有了一點兒死了人該有的動靜。三娃子他娘說:“打小沒白和三娃子好,你咋還一起和三娃子回來幫忙料理他爹的后事了?”我一聽,三娃子他娘明顯是誤會了,于是我趕忙解釋說:“大娘,我也是剛在村口遇到了三娃子,我倆不在一個城市生活,我姑父死了,我和三娃子一樣,都是回來奔喪的。”
“哦,原來是這樣。”三娃子他娘聽明白了。聽明白了我也就該撤了,畢竟人家死了人,我一個外人待著也不合適。以前到三娃子家玩,很少和三娃子他娘說話,他爹倒是愛和我閑聊,聊我的學習,聊我家地里的收成,可現在那個愛聊的人沒了,除了對三娃子他娘說兩句安慰的話,實在是沒什么可聊的,且這個時候又不適合聊天。
我往外走,三娃子的大哥、二哥和兩個嫂子以及侄子、侄女們呼呼啦啦往里進,死氣沉沉的院子忽然就熱鬧了起來。
二
回到姑父家,天已經黑了,按照習俗,我上了一炷香,磕了三個頭。正要走,我爹從里屋出來了,對我說:“今晚幫著守靈吧,你姑說了,你姑父生前一直稀罕你,說你將來一定能考上大學,亡人的話已經應驗了,作為回報,你也該為他守一宿靈。”
本來我已經忙乎了三天,再說這守靈的理由也未免太過牽強,按照習俗,家里有兒子不是應該兒子守靈嗎,沒兒子的侄子就遞補,怎么輪也輪不到我這個妻侄子啊。
我爹說:“叫你守你就守,哪來那么多廢話呢,你姑父走了,你想讓你姑也跟著一起走啊?”我爹說這話明顯是心疼我姑,看來我姑是遇到了難事,否則這事兒我爹不會同意。
守就守唄,反正回來的目的就是奔喪,我姑父活著的時候的確對我好,但從來沒沾過我什么光。因為在外沒混出個什么名堂,所以我從沒給姑父花過錢,我平生第一次給他花錢,就是給他買了一個漂亮的大花圈,可惜他沒看著,能看著我也不會給他買,反正他沒有讓我給他花錢的命。
說起守靈,那可是一件重要的大事,但凡家里有兒子的,一般絕對不會讓別人去守靈,因為靈堂的香火整晚都不能滅,守靈的人一旦睡著了,耽誤了續香火,就意味著這個家今后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為了避免自己睡著了闖下大禍,整晚我幾乎一直在和亡靈念叨,希望姑父若在天有靈,能保佑我在城市里混出個名堂,那么下次再回來給某個親戚奔喪,也算是衣錦還鄉了。
我的愿望別人當然聽不到,第二天早晨大表哥和二表哥一過來,見靈堂里的香火燒得正旺,倆人都很滿意,但如果香火滅了,估計哥倆當場就會扒了我的皮不可。農村人自來不講究什么禮數,兩位表哥不僅對我辛苦了一宿沒有一句客套話,還又交給了我一項重要的任務:等姑父出殯后幫忙主持分割家產。
我趕緊回絕,說自己難當此大任,誰知他倆竟異口同聲地說:“誰讓你在家族里最有文化呢。”我不知道這是抬舉我呢,還是奚落我呢,一個有文化但沒在外邊混出什么名堂的人,一心回來奔喪,卻處處得不到他們的尊重,親人們都如此待我,何況那些沒有血緣關系的鄉親們呢。
回到家我想休息一會兒,誰知我姑正躺在炕上睡覺呢,都七十多歲的人了,按說睡覺應該很輕,居然還打起了呼嚕。我爹說:“你知道你姑和你姑父一輩子都沒感情,他倆這輩子在一起就做了兩件大事,生了兩個不孝的兒子。”
別看我爹沒啥文化,可看人看事卻很準,講起道理來也頭頭是道。爹的觀點我贊成,可我姑剛死了男人,怎么說在一個炕上也睡了幾十年,即便是幾十年來一直同床異夢,也不能這么高枕無憂,跟沒事兒人似的吧。
我爹說:“你姑天亮前剛瞇縫著,她發愁了一宿,我和你娘勸了她一宿。”我問愁啥,爹說:“當然是愁分割家產了,這件事對她來說,比你姑父死了還要讓她痛心。你姑說她料定兩個兒子誰也不會收留她,她的晚景比一條流浪狗還要凄慘,真是作孽!”我爹嘆了口氣。
“我看呀,”我爹猛吸了兩口香煙說,“以后誰再蹬腿兒了(死了),你也別回來奔喪了,這幫勢利眼,知道你在外邊混得不好,哪個也不待見你,熱臉貼人家冷屁股,還奔個啥喪啊,你和他們講血緣關系,他們只知道講金錢關系。沒錢,你就沒尊嚴,等我和你娘蹬腿兒了,到時你再回來吧。”
我說:“我不光是回來奔喪,主要是想看看你和我娘,奔喪是次要的。”“我知道,”爹說,“可是現在你看看,村里這幫出去的娃子,個個都幾年不回來一次,回來基本都是奔喪,其實你們也不容易,好歹心里還有爹娘,不像這幫白眼兒狼,天天在眼跟前兒喂著,一旦沒了肉就翻臉不認人。你看看老胡家,老胡一蹬腿兒,村里的兩個兒子誰也不聞不問,就等著老三從上海回來發喪呢,據說連身壽衣都沒人買,比你姑父還慘呢。”
爹一說起老胡家,我感覺應該去燒炷香,畢竟我和三娃子好了一場。
三
到了三娃子家,比昨晚可熱鬧多了。“我給你寄的錢呢,”三娃子哭著問他娘,“怎么連身壽衣都不給我爹買?”三娃子他娘只顧著哭,不吱聲。他大嫂說:“買再好的壽衣到頭來不都得燒了,就這么火化了得了。”
“放屁,”三娃子紅著眼說,“不是你親爹你就不給穿新衣服了,你的良心都讓狗吃了?”“怎么和你大嫂說話呢!”三娃子的大哥一看老婆受了氣,馬上就撲過來要打三娃子,被我一把抱住了。我說:“大哥別這樣,三娃子話糙理不糙,他這是心疼你爹,好歹老人家受了一輩子苦,走了怎么也該穿身新衣服吧。”
三娃子的大哥消了氣,我讓三娃子帶我到靈堂燒了一炷香,然后我對三娃子說:“給鎮上的壽衣店打個電話,加個路費就送貨上門,速度還快,你爹不能總擱著呀,按照習俗,天黑前得盡快火化。”
壽衣很快就送過來了,三娃子嫌貴,又拿出上海人說話的腔調和人家討價還價。我說:“快點兒付錢吧,討價還價也不看是什么時候,還讓不讓你爹在九泉之下瞑目了。”三娃子咬著牙說:“等唔娘蹬腿兒了,唔再也不回這破地方了,都說葉落思歸,等唔老了,把骨灰灑在黃浦江喂魚,也不會葬在這破地方。唔呸,唔呸,唔呸呸呸。”
“哼,不回來更好,免得我家娃子將來給你燒紙呢!”三娃子的大嫂看不慣三娃子這副上海人的姿態,拿話挖苦三娃子。三娃子懶得理她,忙著給他爹穿壽衣。因為人已經僵硬了,壽衣不得不用剪刀剪開然后再縫上,整個過程,大概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在整個穿壽衣的過程中,除了三娃子他娘幫三娃子搭把手,其他人一直都在旁邊圍觀,包括三娃子那幾個蹦蹦跳跳玩得不亦樂乎的侄子和侄女,好像躺著的那個人不是他們的爺爺。
這種場面看著真是讓人心酸,有好幾次我的眼眶里都充盈著淚水,但沒敢讓淚珠子掉出來。在這種場合,我算什么,人家兒孫們一大片,唯獨我一個人掉眼淚,且既不沾親也不帶故,我不是給人家添亂嗎。我實在是待不下去了,確切地說是看不下去了,沒和三娃子打招呼,就識趣地偷偷溜了出來。
姑父家我是不想去了,兩個冷血的表哥和三娃子的兩個哥哥一樣,見了面兒也沒什么熱乎勁兒,沒準兒還得抓著我幫他們守靈呢。家我也不想回,村里除了一條條沒人喂的流浪狗,顯得很肅靜,仿佛村里沒死過人,又像是死了很多人。
年輕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剩下的就像我的兩個表哥和三娃子的兩個哥哥這樣的,不想賣苦力,就待在村里靠幾畝薄田勉強度日,而稀稀落落的老人們,就像秋天的樹上幾枚孤零零的葉子,只等著一陣秋風吹來,早早地回歸大地。回歸,從某種意義上講或許也算是一種幸福。
就像我姑父,從患病到離世,前后也就三個多月。三個多月,沒吃過一顆藥,也沒吃過一頓好飯,甚至到死都張著嘴巴,睜著眼睛,好像誰欠他一頓飯似的。我欠他,欠他曾經給過我的疼愛,而我,卻自私得從沒報答過他。或許他也從未奢求過我會報答他,就像他永遠也不會知道我給他買過一個漂亮的大花圈。
四
姑父出殯那天,場面還算隆重,我姑帶著兩個兒媳婦,象征性地哭了有半個多小時,她們究竟有沒有流淚,或者流了多少淚,我不知道,因為她們的臉都用一張紙簾擋著,紙簾是用麻繩穿好后,與頭上戴著的孝帽連在一起的,上面有幾個小窟窿可以透氣。
我不知道祖先們為什么要發明這樣一種孝帽,或許是給那些偽善的孝子賢孫們留一些顏面,也讓死去的人走的時候有一點尊嚴。但我分明能感受到那哭聲中的痛苦,有時候,不想去哭一個人可能遠比因為懷念去哭一個人內心更為痛苦。
哭只是葬禮上的一個環節,不能缺少,沒人哭,就不是一場完整的葬禮。我哭了,但沒人注意到,即使有人注意到了,誰會認為我是在真哭呢。何況,我哭也確實不是因為我有多么懷念我姑父,我好像是在哭自己沒有衣錦還鄉的榮光,不能給這些窮親戚們一些物質上的幫助,也像是在哭這個人情冷漠的時代。
葬禮結束后,中午12點,大表哥選了一個吉時,開始分割家產。姑父在世時,盡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土地做了一輩子知己,但到頭來貧瘠的土地還是負了他,沒給他帶來什么財富,家中僅有三間土窯,還是20世紀60年代碹的,如今窯頂因被螞蟻洞貫通,一到夏天就漏雨,基本已經不能再住人了,也就是說,我姑得盡早搬家。
由于現在農村人口驟減,加上為了保護耕地,因此政府已經不批宅基地了,誰家若是想蓋新房,就只能在原址上翻建。大表哥的兒子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他想把三間土窯要了,給兒子翻建新房。二表哥同意,但前提是大表哥需要給他補償一些錢。大表哥說一千,二表哥說不行。大表哥說:“當年碹這三間土窯也就花了三百塊錢,給你一千已經夠多了。”二表哥說:“當年豬肉幾毛錢一斤,現在幾毛錢連根兒豬毛都買不來,開什么國際玩笑,當你弟弟是白癡啊。”
就這樣,大表哥和二表哥一直爭執,我爹實在看不過眼了,就問他們:“你們的娘誰要?”我爹這一問,散發著火藥味兒的空氣突然凝固了。半晌,大表哥說:“我不要,我有兒子,負擔太重。”二表哥說:“我也不要,雖然我就倆閨女,但將來嫁人哪個不得準備嫁妝,嫁妝少了到婆家肯定會受氣。”
“我侄子的意見呢?”我姑問我,“你這倆表哥請你主持分割家產,可誰也不問你的意見。反正,我就聽我侄子的,我侄子有文化,你說怎么分就怎么分,我就信我侄子的話。”
“那我可說了啊。”我看了看倆表哥的表情。“說吧,”大表哥說,“但不能有私心,尤其是不能偏袒你姑。”偏袒?大表哥說出偏袒這個詞,我當時的感覺是他比我還有文化。我說:“我的意見是誰要這三間土窯就把我姑一起要了。”“我同意。”我剛說完我姑就立即表態。“我也同意。”我爹也跟著表態。“舅,你同意不算,這是我們家的事。”我大表嫂說。“照你這么說,我兒子還不是你們家的人呢,干嗎讓我兒子摻和你們家的事,走了,我們不管了。”
我爹說著,就下炕穿鞋拉著我要走,被我姑一把拽住了:“兄弟,你還想讓你姐活不,你們爺倆這一走,我只剩下一頭撞墻自個兒尋死了,還不如跟那個老東西一起走了呢,省得活受罪,作孽啊,作孽啊。”我姑說著哭了起來。
“好了,不要哭了,我讓一步,”二表哥說,“三間土窯和娘我都不要了,補償的錢我也不要了,這下行了吧。”誰知大表哥馬上接過話茬:“那可不行,就算娘和三間土窯都歸我,但娘得一塊兒養著,我一個人負擔不起。”“你還要不要臉了,”二表哥馬上激動起來,“敢情便宜都讓你占了,三間土窯歸你,你不給我補償錢,我還得和你一塊兒養娘,世上哪有這種道理!”
“我看你們都不要臉,”我姑說,“三間土窯給我留著,我哪兒也不去,哪天塌了就算感謝老天爺幫我把自個兒埋了,省得你們再搶這破窯。”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對我姑說:“姑你跟我走吧,我養你,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餓不死你。”我姑一聽,立時又嚎啕大哭起來,比我姑父死了哭得還凄慘:“丟人啊,自己生了兩個娃,到頭來還得讓侄子養老,我上輩子做了什么孽啊,到老了都不安生。”
我爹一聽來氣了:“你憑什么養你姑,我和你娘還指著你呢,再說了,這又不是咱家的事,走吧。”我爹拽著我就氣沖沖地回了家,回了家就把我一頓大罵,說當時如果我姑答應了,看我怎么收場。我說:“咋了,養就養唄,我姑總不能沒人管吧。”“沒人管村里人也不會笑話咱,”我爹說,“收拾東西明天趕緊給我回城去,記住,以后除了我和你娘蹬腿兒了,不許再回來給哪家親戚奔喪。”
五
第二天中午時分,我從鎮上剛回來,在村口又遇到了三娃子。我問:“你這是帶著你娘干啥去?”三娃子說:“回上海。”我說:“你爹不是還沒出殯嗎,怎么這么早就急著走呢?”三娃子說:“別提了,家里亂成一鍋粥了,我爹還沒出殯,兩個哥哥就要鬧著分割家產,他倆都搶房子,誰也不要我娘,我說我要,干脆我把我爹的骨灰也一塊兒要了,反正葬在這兒也沒人給他上墳,一個人孤苦伶仃的,以后我娘也會葬在上海,這個破地方我是再也不會回來了。”
三娃子說著,問我:“你這是又給誰買花圈去了?”我把嘴巴湊到三娃子的耳邊,悄聲說:“給我姑買的,她想我姑父想得不行,昨晚喝藥走了,你得看好你娘啊。”三娃子又是一愣神,接著點點頭,繼而問我:“鎮上離村里這么遠,你咋也把花圈扛回來了呢?”我說:“本來電話中和花圈店說好了是送貨上門,可誰知最近咱們這一帶死人太多,人家急著往別處送貨,非讓我到村口接貨。”
“哦,原來是這個樣子,那阿拉先走了啊,阿拉急著要趕火車,儂有機會去上海,唔帶儂好好玩玩。”還沒出村,三娃子又拿出了上海人的腔調,我擺了擺手,扛著花圈往我姑家走。
真是丟人,偏偏在這個地方又遇到了三娃子,前幾天我還有些奚落人家,沒想到今天我也如此落魄。三娃子不知道我姑和我姑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感情不和嗎?他不知道只要給錢,花圈店的老板都敢說能把花圈送到火星上嗎?他知道,可他卻絲毫沒有奚落我的意思,也難怪,他從骨子里已經把自己當成了上海人。
我姑的死在村里沒有掀起多大波瀾,村里還是像往常一樣肅靜,仿佛沒死過人,又像是死了很多人。本來我是要回城的,一大早大表哥急著跑到我家,說我姑昨晚喝藥走了,還得讓我幫他報喪、守靈。
從鎮上給我姑買完花圈,正準備租個小貨車回村,我才發現這樣的話回城的路費就不夠了,一個在自己的爹面前信誓旦旦要幫別人養娘的娃子,怎么有臉再伸手朝爹要回城的路費呢?
作者簡介:
孫慶豐,1977年4月出生,男,河北懷安人,現居河北省秦皇島市。魯迅文學院河北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有作品發表于《詩刊》《小說選刊》《青年文學》《時代文學》《啄木鳥》《飛天》等刊物,曾獲魯藜詩歌獎、梁斌小說獎、延安文學獎等獎項。著有詩集《春天的過錯》、短篇小說集《湛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