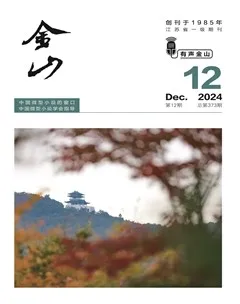以翻譯為媒,推動中西文明交流互鑒
由江蘇科技大學曾景婷教授主譯的戲劇經典專著《劍橋戲劇導演導論》(以下稱《導論》)于2023年9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共計32萬字。原著由國際知名學者克里斯托弗·因斯(Christopher Innes)和瑪麗亞·謝福特索娃(Maria Shevtsova)合作撰寫,是一部戲劇導演導論,由劍橋大學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是西方戲劇領域的權威之作。該著作的引入及其翻譯出版,依托了南京大學何成洲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當代歐美戲劇理論前沿問題研究”(2018-2022),是該項目的重要成果之一。根據何教授在總序中所言,翻譯該書的初衷是“鑒于西方戲劇與表演理論在理論上取得的豐碩成果,有必要進一步推動相關代表性著作的翻譯和研究工作……有計劃地翻譯一批有重大影響的西方戲劇理論文獻,不僅能服務于課題的研究,也能為我國的戲劇理論建設積累一份資源”。基于此,課題組在原文獻的選擇上采用了“經典性與前沿性”相結合的標準,即只翻譯那些既經得起歲月雕琢,又與時代脈搏緊密相依的作品。《導論》正是在這樣的契機中走進了課題組的視野,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歷經時間考驗而日久彌新的佳作,值得我們譯介學習。
《導論》出版后,受到了戲劇界人士高度評價。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碩士生導師石俊教授在譯著推介研討活動中高度贊揚了它的重要價值,提出“它填補了國內戲劇導演史論類譯著的空白,是一本具有標桿意義的譯著”,并認為“它能夠為戲劇專業人士、在校學生以及普通戲劇愛好者提供某些啟示。” 他還表示,《導論》已被列為該校戲劇專業研究生招生考試的必讀書目。此外,中國國家話劇院一級導演、2024 ATEC第七屆亞洲戲劇院校大學生戲劇展演評委會主席吳曉江專門寫信給曾景婷教授,高度評價了《導論》:“該書內容非常豐富、易讀生動,既有很好的研究學術價值,又給熱愛戲劇的人想一鼓作氣讀完的熱情。內容不僅重新解讀了大家熟知的導演藝術思想,也把焦點注視在當代的導演實踐案例上;當代戲劇導演的美學追求在譯者的譯筆下尤為鮮亮活潑。”由此可見,《導論》兼具專業性與知識性,一出版即得到了國內學者與研究者的高度關注與認可。
《導論》聚焦當代導演研究,“從表演、舞臺和導演三個維度來分析當代導演的前世與今生”,既展現出縱向發展史,又進行了橫向的鋪陳,是一部較為完備的導演史著作。它共有七章。其中,第一章追溯了導演的“歷史”,即當代導演的“史前”研究。它“縱向鉤沉出自古希臘以降西方戲劇導演的總體發展脈絡”,既為讀者理解當代導演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總體框架,同時也為讀者繪制了導演發展“地圖”,讀者只需按圖索驥,便可以對導演發展史了解得一清二楚。第二章及其以后的章節則聚焦于20世紀以降歐美的重要戲劇導演及其流派,分別從橫向視域探究了導演的作用、導演如何訓練演員、導演的不同分類等,不一而足。總而言之,《導論》既涉及總體概括性分析研究,又提供詳細的案例資料,展現出“視野宏大、例證翔實、分析細致、深入淺出”的典型特征。
《導論》的出版回應了當下有關20世紀戲劇研究一直受到國內外研究者關注的現狀,以及國內研究明顯落后于國外研究的困境。翻譯并引入該領域的權威著作,有助于國內研究者快速吸收西方的理論前沿,通過中西互鑒,構建中國戲劇研究話語體系。這也是中國學者提升自我、走向國際舞臺并有能力開啟中外戲劇理論對話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翻譯是中西學人相識、相知、互融、互知的重要方式。不論是引入西方的先進經驗與觀點,還是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都離不開翻譯的參與。國內外知名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王寧教授曾在訪談中“把翻譯研究置于更加宏大和系統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把翻譯的功能與多模態發展放在‘中華文化走出去’這樣一個大的國家戰略中審視”,并從“建設國家對外翻譯機制”“提升國際傳播能力”“新形勢下中國對外傳播的新挑戰、新任務和新進程”“翻譯助力多層次文明對話”“翻譯助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等方面提出高見。
譯者自古以來便承擔著“媒人”的角色。盡管在翻譯史上,譯者通常被描述為“戴著鐐銬跳舞”,言外之意,他居于作者之下,缺少主體地位,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論是翻譯這一行為,還是譯者這一角色,都無法被替代。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他們的地位和作用不但不會削弱,還會被不斷強化。
從這一視域下審視《導論》,我們發現,它的翻譯出版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案例。中西學人通過《導論》實現了對話與交流。假若不借助翻譯這一重要媒介,我們很難想象這一過程能夠如此順利實現。而縱觀《導論》的翻譯,我們發現該譯作具有行文流暢、閱讀體驗好、術語翻譯準確、嚴謹度高等特征。它既準確地傳達了原作者的思想,又在翻譯過程中增加了不少“譯者注”,有效降低了閱讀難度,幫助讀者更為輕松地理清文章的奇思妙想。
總之,《導論》的翻譯與出版既傳神地傳達了原文獻的精髓,又彌補了國內缺少有關導演類史論的遺憾,是學習戲劇不可或缺的一部重要的工具書,值得放在案頭常讀。同時,它還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成果,見證了中外戲劇研究者在導演史論上的執著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