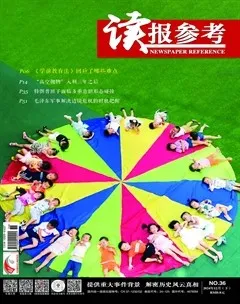“高空拋物”入刑三年之后
2021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高空拋物”作為刑事犯罪被正式寫入《刑法》。在三年多的具體實踐中,在沒有警方協助的情況下,如何找到拋物者?找到拋物者后,執法部門的處罰力度是否到位,是否引起公眾足夠的重視?如果找不到拋物者,又有多少人會選擇起訴整棟樓這一成本巨大的維權方式?城市高樓中的人們依舊被困在這些問題里。
天降油瓶
對劉曼妮(化名)來說,8月24日是一個至今想來依然心有余悸的日子。這天晚上,她和丈夫孫智豪(化名)像往常一樣,下樓散步遛狗,被從天而降的玻璃瓶砸中時,驚嚇比疼痛更早一步到來。很快,一種“火燒的感覺”從右腳傳來,劉曼妮開始大哭。當時,她懷有34周的身孕,肚子已經大得在正常走路時無法看到雙腳。
聽到哭聲后,孫智豪轉身看到坐在地上的妻子和散落的玻璃碎片,第一時間報了警。電話那頭,民警詢問是否需要救護車,孫智豪脫下妻子穿著的洞洞鞋查看傷情,發現鞋底已被鮮血浸滿。“第三根腳趾只剩下半截,第四根腳趾像炸開一樣,指甲已經沒有了。”孫智豪回憶。
在民警的推薦下,他們來到一家以骨科見長的醫院。一位骨科主任表示,正常人接骨后斷指的存活率只有三到五成。而對于孕婦來說,術后無法使用加速血液流通的藥物,直接清創縫合才是最保險的選擇。再加之,接骨手術起碼要做六七個小時,這是劉曼妮和腹中胎兒都難以承受的時長。
為了最大程度減小對胎兒的影響,醫生在劉曼妮的腳心打了一針局麻,為她進行了修復手術。“我現在看這個腳趾真的好丑,絕對不會再穿涼鞋。”劉曼妮至今依然沒有完全接受失去半截腳趾的事實。她事后才知道,砸中自己的是一個容量550毫升的芝麻香油瓶,瓶身上半部分完整,瓶底受到撞擊后完全炸開。
2023年11月,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張進帥、李金珂基于對136份刑事判決書的分析和考察,發表了一篇題為《高空拋物犯罪的特點、成因與治理對策》的論文。其中提及,我國高空拋物案件中犯罪人所拋擲的主要物品,正是“芝麻香油瓶”一類的生活垃圾。
鎖定拋物者
事發后的第二天,民警為劉曼妮和孫智豪做了筆錄,并調取了監控。然而,案發時是晚上,光線昏暗,孫智豪回憶,通過監控,只能看見一條從低樓層出現的白色拋物軌跡,無法確定拋物者所在樓層。很快,案件從鎮派出所被移交至縣公安局,由刑警大隊接手。嘗試多種方法無果,刑警決定通過DNA比對來鎖定拋物者。
這是一棟一梯四戶的32層住宅。孫智豪表示,根據芝麻香油瓶下落的軌跡,刑警鎖定了可疑樓層,并對可疑樓層每層的第四戶業主進行采樣。不到三天,孫智豪就被告知,拋物者已被抓獲。那天是9月2日,距離事發僅過去9天。然而,在更多高空拋物事件中,這樣的過程和結局并非常態。
胡江(化名)居住在湖北一處高層老小區的三樓。今年6月,一個玻璃瓶從他所在樓棟的18層被扔下,砸碎了他家露臺的玻璃和地板一角。安裝在露臺的防高空拋物攝像頭記錄了全過程,胡江很快找到了拋物者,但對方不承認。于是,胡江報警。在配合民警做筆錄、調監控、取物證后,胡江陷入了無盡的等待。此前,胡江已多次被高空拋物砸到,也曾報過警。“就過來看一下,說找不到哪一家,要去調查,后來都不了了之”,胡江無奈。幾次下來,他感覺民警對高空拋物“不是很想管”。
刑警秦海洋已從警三十余年。近年來,他持續關注與高空拋物相關的社會案件。他表示,一般情況下,民警到現場后會有基本判斷,分辨案件屬于“高空拋物”還是“高空墜物”,前者屬于刑事范圍,而后者系民事侵權。但現實是,大多數情況下,現場留存的證據并不充分,因此難以在“拋”和“墜”之間準確定性。秦海洋也坦言,不可否認一部分民警不想“多管閑事”。
2021年3月1日,“高空拋物”正式入刑。但法條明確,高空拋物罪的認定需要滿足一定的違法犯罪情節,包括行為人的動機、拋物場所、拋擲物的情況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在“高空拋物”入刑之前,2016-2018年,全國法院審結的高空拋物、墜物民事案件有1200多件,而受理的刑事案件只有31件,后者中有五成造成了受害者的死亡。
秦海洋表示,若某高空拋物行為被確定為刑事案件,正常的辦案流程為:出警、受案、完成正常的立案程序,此后才能進行刑事案件調查,提取證據;嫌疑人抓到后,再報捕起訴。而DNA的采集、公共監控的調取等環節,正是“提取證據”的重要手段。這解釋了為什么很多高空拋物案“去調查一下”后就不了了之。
成本
如今回想,劉曼妮和孫智豪都覺得,除了身體遭罪外,案件本身解決得十分順利,“警方積極主動完成了所有環節”。他們把重要的推動因素歸結為輿論壓力。
事發第二天晚上,看著因疼痛無法入睡的妻子,孫智豪在自己粉絲量甚少的社交平臺上記錄妻子的遭遇。“發生好多事,心里很煩,就是做一個心情的輸出口。”回憶發帖初衷,他沒有料到輿論將會發酵。隨后幾天,上門的民警除了告知案件進展外,另一個任務就是勸孫智豪刪帖。“比較擔憂,因為有太多高空拋物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孫智豪說。在民警的反復勸說下,他將帖子設置成“僅自己可見”。
等了一兩天沒有消息,孫智豪希望能在妻子生產前把這件事處理完,于是又把帖子改成“公開可見”。“輿論壓力還是會有的,可能慢慢被上層看到了,案子被轉到縣公安局。”孫智豪猜測。
對于多數不被看到的受害者來說,維權是一件顧慮重重且需要成本自負的事。在無法找到拋物者的情況下,受害者唯一能做的是以民事訴訟的方式起訴整棟樓,這意味著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時間很漫長,消耗的精力非常大,請律師又是一筆費用”,胡江的律師朋友認為“得不償失”。
“家人覺得搭這么多時間不值得,也不希望把鄰里關系鬧得太僵。”胡江說。因此,他也沒有在業主群里公開聲討拋物者。但他表示,如果受到了人身傷害,肯定會起訴。
歷時兩個半月拿到了賠償款后,胡江覺得拋物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其實我損失更大一些,地板損壞我都沒算,還花了很多時間,最后該賠償的也沒全部賠給我”。
曾有學者對當時裁判文書網上有記錄的26起高空拋物案件進行梳理,把高空拋物行為的原因主要分成情緒宣泄、圖方便和看管不當三種,其中為了情緒宣泄和圖方便的情況占了近三分之二。
直至現在,劉曼妮和孫智豪仍然想不明白,向他們扔下芝麻香油瓶的那人是出于何種動機。孫志豪也曾試圖詢問過警方有關拋物者更多的信息,警方的回應含糊不清,孫志豪便不再多問。對此,秦海洋解釋稱,在刑事案件中,一般公安機關只會告知基本案情、案件調查進展等信息,對個人信息的保密是為了保障嫌疑人的基本人權。
在胡江看來,雖然有了相關法律,但“能不能按法定罪又是另一說”,他覺得法律在其中更多起到的是一種威懾作用。維權過程中,他曾問過警方,什么情況下高空拋物才構成刑事犯罪,得到的回答是“非常嚴重”。進一步追問什么樣算“非常嚴重”,“他們也說不清楚”。
結合平時的工作經驗,秦海洋表示,“高空拋物”入《刑法》的時間尚短,在具體的認定層面存在很多模糊地帶,入罪標準就是其中之一。這是日后司法解釋可以進一步努力明確的方向。
(摘自《解放日報》朱雅文、陸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