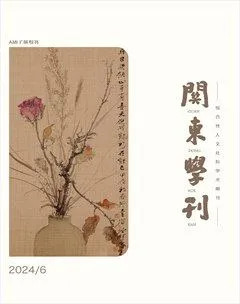當代中國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功能及其限度
[摘要]我國古代審判歷來就有“引經據典”的傳統,當代司法實踐也存在法官在裁判文書中援引古代典籍進行說理論證的現象。經驗觀察表明,“引經據典”在個案裁判中發揮著案件事實認定、修辭論證以及對爭議判決進行引導與糾偏等功能。“引經據典”作為一種積極修辭,能夠增強裁判的說服力與可接受性。為避免“道德裁判”取代“法律裁判”的情況,“引經據典”在司法裁判中應明確為功能上的“補充”而非“替代”。法官在裁判文書中“引經據典”需要遵循必要的限度,在依法裁判的基礎上保障經典論證的邏輯性與適當性。
[關鍵詞]司法裁判;“引經據典”;功能主義;裁判說理;法律修辭
[基金項目]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當代中國裁判文書說理中的‘引經據典’研究”(23YJC820060)。
[作者簡介]周曉帆(1994—),女,法學博士,山東科技大學文法學院講師(青島266590)。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經常在重要講話、報告中引用中國傳統古語與典故,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關于習近平總書記用典的相關摘錄,可參見人民日報評論部:《習近平用典》(第一輯、第二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年。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與文化自信。
劉戀:《習近平用典的特色和時代價值》,《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我國古代審判歷來有“引經據典”的傳統,審判官在判詞中引用先哲語錄或者儒家經典論述,實現審判解決糾紛以及教化民眾的功能。及至當代司法實踐,也有一些法官在裁判文書中引用儒家經典、諸子論述、傳統俗語典故等進行修辭論證,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比如,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在一起家庭房產糾紛案中,就在判決書中指出:“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百善孝為先’的優良傳統,儒家經典《孝經》中把‘孝’譽為‘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德之本’。”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2010)東民初字第00948號。相關報道認為,法官在裁判說理時“引經據典”具有創新意義,這一做法不僅顯現了法官的人文水平和個人修養,也有利于增強裁判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
張建偉:《〈孝經〉寫入判決書的法文化解讀》,《人民法院報》2010年7月23日,第5版;庾向榮:《〈孝經〉入判決體現法官智慧》,《人民法院報》2010年6月9日,第2版。
傳統經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價值理念上具有內在延續性。最高人民法院自2015年發布《關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若干意見》(法發〔2015〕14號)以來,先后發布了系列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型案例,其中不少案例采取了“引經據典”的修辭論證方式。
比如,2023年3月發布的典型案例,法院在“沙某某訴袁某某探望權糾紛案”的典型意義部分,就引用了“家和萬事興”“天倫之樂”等古語,論證在子女死亡的情況下,應允許喪子老人對孫子女進行隔代探望。在“李某與某電子商務公司勞動爭議案”中,法院引用了“百善孝為先”“孝親敬老”等古語,認為勞動者請假照看病危父親,用人單位應給予適當善意和包容。2022年發布的典型案例中,第一則物權保護糾紛案法院也直接引用了“百善孝為先,孝為德之本”的經典古語,指出祖母贈與孫子房產后有權繼續居住房屋。在某老舊小區加裝電梯案中,法院指出“崇德修睦、包容互讓是構建和諧鄰里關系的重要條件”,其中“崇德”“講信修睦”出自孔子在《禮記·禮運》中的論述。此外,2016年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法院也在弘揚價值觀部分引用了“遠親不如近鄰”“誠者,天之道也”等經典古語。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三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典型民事案例》,2023年3月1日,https://www.pkulaw.com/chl/eabdc266a0b69c39bdfb.html?keyword=核心價值觀amp;way=listView;《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典型民事案例》,2022年2月23日,https://www.pkulaw.com/chl/fdb64c89d87f5129bdfb.html?keyword=核心價值觀amp;way=listView;《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0起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典型案例》,2016年3月8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7612.html。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法〔2021〕21號),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近些年來,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現象得到學界的關注,有學者指出,“引經據典是一種契合中國人精神情感和思維模式的說理方式”
謝晶:《裁判文書“引經據典”的法理:方式、價值與限度》,《法制與社會發展》2020年第6期。。但也有質疑的聲音,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法律與道德相分離的形式法治要求,道德論證不能取代法律論證等。有研究指出:“判決書援引佶屈聱牙、生僻晦澀的古文典籍,這不僅無助于增強論證,反而造成了當事人的閱讀障礙。”
孫光寧:《判決理由的融貫性——從〈孝經〉判案說起》,《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孫海波:《裁判運用社會公共道德釋法說理的方法論》,《中國應用法學》2022年第2期;王聰:《我國司法判決說理修辭風格的塑造及其限度——基于相關裁判文書的經驗分析》,《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年第3期。整體而言,已有研究主要從傳統文化、法律史層面展開論述
謝晶:《新瓶舊酒:傳統文化融入司法的價值與路徑》,《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方月倫:《司法裁判援引傳統文化問題探析——基于132份生效裁判的實證分析》,《法治社會》2020年第2期。,對當代中國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現狀及功能缺乏進一步經驗分析及理論論證。
什么是經典?第一,一般來說,經典指具有典范性、權威性的著作。“經”字最早出現在青銅金文中,表示織布的意思。《說文解字》解釋:經,織也。而“典”就是“五帝之書”。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4頁。在歷史早期,由于書籍較少,因此書籍是寶貴的權威性的東西,隨著書籍的增多,為了突出重要的書籍,就有了“典”。第二,經典泛稱儒家經典。《莊子·天運篇》將《詩》《書》《禮》《樂》《易》《春秋》稱為“六經”。根據《辭海》對“經典”的釋義: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古代儒家經典,也泛指宗教的經書。
《辭海》編輯委員會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第3303頁。第三,經為常道。在中國古代,經實際上具有規范秩序的意思。《左傳·昭二十五年》有曰:夫禮,天之經也(注:經者,道之常)。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有曰:“經也者,恒久之至道。”所謂“經”,就是永恒不變、至高無上的道理。《周禮·天官·大宰》有曰:“以經邦國”(注:經,法也)。某種程度上說,“經”具有“法”的規范內涵。本文在寬泛意義上使用經典的概念,“引經據典”指引用古代權威典籍,既包括引用儒家經典中的表述、先哲語錄,也包括引用中國傳統古語、俗語。司法裁判“引經據典”,指法官在裁判說理時引用古代經典中的表述進行論證。在描述現狀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探究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功能定位及限度。
二、我國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現狀分析
作為社會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范式,功能主義強調“任何社會系統都是功能性實體,功能性決定著系統中的各種結構和過程相互依存”
[德]馬塔·格哈特:《帕森斯學術思想評傳》,李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3頁。。在研究方法上,功能主義關注研究對象的社會背景,注重經驗研究、實證研究方法的運用。
[美]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唐少杰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頁。具體在法學領域,功能主義研究以現實功能為分析對象,考察法律運行呈現的客觀效果。本文在裁判文書網的“本院認為”部分,選取常見的“禮記”“論語”“孝經”“弟子規”“詩經”“孔子”“孟子”“荀子”等典籍與人物名稱進行檢索。此外,筆者發現,當以“古語”“古人云”“古人有云”“老話說”“俗話說”等關鍵詞檢索時,獲取的文書樣本數量更多。在此說明的是,以上關鍵詞在裁判文書中較常出現,當選取《大學》《中庸》《尚書》《春秋》《周易》《道德經》《史記》《老子》《莊子》《韓非子》《墨子》等典籍與人物名稱作為關鍵詞檢索時,獲取的有效文書數量非常少,所以不在正文部分予以列明。經過人工篩選剔除無效與重復的引用,共計獲得1130份裁判文書。
(一)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整體特征
通過經驗分析,“引經據典”的裁判文書大致呈現出以下特征:其一,民事案件較常“引經據典”。在樣本案例中,民事案件最多(1055,93%),行政案件(29,3%)與刑事案件(24,2%)次之。之所以民事案件較常“引經據典”,一方面,民事案件強調當事人雙方的意思自治,法官不得拒絕裁判,因此民事案件本身數量最多。另一方面,民事案件涉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有關身份關系、人際交往的案件對于案件事實的認定較為復雜。所謂經,其實就是普遍適用的道理。經典所記載的道理,是不斷被傳承的扎根于中國人內心的價值觀,這種道德倫理觀念在民事糾紛中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因此,民事裁判領域是法官“引經據典”的主戰場。
其二,基層人民法院較常“引經據典”。樣本案例中,基層人民法院的案件最多(734,65%),中級人民法院次之(352,31%),高級人民法院較少(36,3%)。這表明,“引經據典”的修辭論證方式被基層法官廣泛使用。事實上,我國基層法院關于“法官后語”的實踐與“引經據典”在功能上存在相似之處,都屬于“倫理內容支持法律內容”,或者以“富情感、文學化的敘述”作為“修辭策略”
劉星:《判決書“附帶”:以中國基層司法“法官后語”實踐為主線》,《中國法學》2013年第1期。。或許有人會說,因為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數量最多,樣本裁判文書的比率自然高。筆者對北大法寶公布的案件總數做了統計,我國基層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數量占據案例總數的85%,而樣本案例65%的數據遠低于這一比例。所以,相較于我國案件數量的總體分布而言,“引經據典”在中級以上人民法院也具有一定應用空間。
其三,“引經據典”具有“各殊性”和“聚合性”。一方面,“引經據典”作為一種修辭方式體現為法官的個人特色。像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重慶市忠縣人民法院等法院的判決書就常常“引經據典”。另一方面,“引經據典”的案例呈現出一定“聚合性”。樣本中,廣東省(144)、河南省(101)與山東省(99)分別是獲取案例最多的省份。當然,我們不能據此得出裁判“引經據典”具有地域屬性的結論,因為通過觀察樣本,這些案例多為類似案例。在贍養糾紛、相鄰權糾紛、合同糾紛案件中,傳統經典中涉及“孝”“和”“信”等價值理念的經典表述常被援引。如重慶市某法院在多起贍養糾紛案件中就援引了《禮記》中對于“孝”的經典論述
可參見重慶市忠縣人民法院(2018)渝0233民初2557號;(2018)渝0233民初2649號;(2018)渝0233民初1940號;(2019)渝0233民初286號等判決書。,這反映了裁判文書“引經據典”受到法官個人裁判文書書寫風格的影響。
(二)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主要功能
在對已有裁判文書進行經驗分析后發現,法官在裁判文書中引用古代經典論述,大致具有事實認定、修辭論證及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補強論證幾方面功能,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對案件事實進行敘述與認定。事實認定是司法裁判的邏輯起點,無論是法律發現還是法律適用,都需要建立在事實認定的基礎上。法官在裁判中“引經據典”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對案件事實進行認定或者進行事實敘事。例如,在一起涉及中國傳統習俗——“份子錢”的案件中,法官引用了古代典籍對案件事實進行推定:“對于原告主張的人情往來費,實際上屬于親戚、朋友、鄰舍之間為婚、喪、壽宴等宴請隨的‘份子錢’,屬于民間傳統習俗。西漢·戴圣《禮記·曲禮上》記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說明按照這樣的習俗,份子錢是有進有出的,并不完全是支出,同時,原、被告都有自己的親戚、朋友或者共同的親戚朋友,很難分清‘份子錢’是為誰出的。”
云南省騰沖縣人民法院(2021)云0581民初3066號。該案中,法官通過“引經據典”表達觀點:按照我國傳統習俗,“份子錢”是有來有往的,并不是完全支出,也并不是個人性支出,因此對于人情往來費的訴求不予支持。
“引經據典”在民事案件特別是在婚姻家庭類案件中較常出現,因為這類案件涉及復雜的家庭倫理關系,案件事實較為復雜。以一起親兄弟房屋使用權糾紛案為例,原告利用了法律修辭,指出當時為了孝敬父母將承包地登記在了父親名下,原告才是實際的土地承包人,且房屋為原告所建,而被告則指出,涉案房屋一、二層均為被告出資所建。法官在裁判文書中指出:“本案原告拜平省和被告拜勝利是親兄弟,兄弟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幫助也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優良傳統,《弟子規》中有云:‘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哥哥要對弟弟友善、弟弟要對哥哥恭敬,兄弟和睦,才能家和萬事興。”
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2021)豫0883民初1965號。本案屬于親兄弟之間的房屋糾紛,且時間久遠,雙方均沒有確鑿證據證明自身主張的事實。法官認為,鑒于原被告雙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在共同使用該房屋,故判定該八間房屋是雙方共同建造,共同使用。審判實踐中,法律事實首先在當事人主張的基礎上展開,法官認定案件事實時需要說服當事人。在較為注重血緣親情的中國社會,結合古代典籍中的經典論述對案件事實進行敘述與判斷,更容易被當事人所接受。
第二,對判決理由進行積極修辭。我國法官在婚姻家庭類案件中常“引經據典”,比如在一些離婚糾紛案中,法官常引用“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一日夫妻百日恩”“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韌如絲,磐石無轉移”等古語俗語,論證“未能證明夫妻情感破裂”。
可參見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2015)豐民初字第10579號;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2015)豐民初字第06215號;山東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5)禹民初字第379號;山東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6)魯1482民初1760號;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2014)歷民初字第2237號民事等判決書。此外,法官在贍養繼承類案件中也常常“引經據典”,除了援引“百善孝為先”“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等民眾較為熟知的俗語,還有“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情”“萬愛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孝于親,子亦孝之。身既不孝,子何孝焉”“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孝子之養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等《禮記》《孝經》《詩經》這類儒家經典中的論述、典故。
可參見湖南省洞口縣人民法院(2014)洞民初字第1874號;重慶市北碚區人民法院(2021)渝0109民再18號;安徽省蚌埠市龍子湖區人民法院(2019)皖0302民初339號;重慶市北碚區人民法院(2021)渝0109民再18號民事等判決書。“引經據典”在這類案件中具有怎樣的功能呢?有學者指出,這類“引經據典”的判決書“目的是要引起相關主體在道德上的共鳴,道德話語在此類裁判中更多地發揮了一種修辭性的功能”
孫海波:《裁判運用社會公共道德釋法說理的方法論》,《中國應用法學》2022年第2期。。
修辭是一種為說服而進行的文字表達,一般來說,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較常在裁判文書中引用法律原則、法律諺語、法律學說等進行修辭。我國古代判詞雖然擅長“引經據典”,以文辭優美著稱,但自晚清法律移植之后主要學習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制運作模式,裁判文書追求嚴謹的三段論推理,說理較少,很少使用修辭。這種嚴謹簡練的裁判文書風格也引發了關于我國裁判文書說理不足的批評與反思。
胡云騰:《論裁判文書的說理》,《法律適用》2009年第3期;莊緒龍:《裁判文書“說理難”的現實語境與制度理性》,《法律適用》2015年第11期;凌斌:《法官如何說理:中國經驗與普遍原理》,《中國法學》2015年第5期。陳望道先生在《修辭學發凡》一書中將修辭技術分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其中,消極修辭語言平實,注重形式,而積極修辭強調意境與情感。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3—59頁。根據這一分類,“引經據典”屬于積極修辭。需要思考的是,司法裁判為什么需要“引經據典”來進行修辭?有研究指出,當下我們應該重視積極修辭對于裁判文書說理的作用,因為“在講究‘法理’和‘情理’相結合的裁判要求下,積極修辭具有其他法律論證方法所沒有的優勢功能”
鐘林燕:《論裁判文書說理的積極修辭及其限度》,《法學》2022年第3期。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謂“引經據典”不同于鐘文提及的援引學術理論和學者思想的做法,這一現象屬于在司法裁判中援引法律學說。關于法律學說的相關概念及司法運用,參見周曉帆:《法律學說的概念及相關用語辨析》,《法律方法》2022年第3期;周曉帆:《論法學通說在我國司法裁判中的應用——以裁判文書說理為視角》,《西部法學評論》2021年第6期。。雖然不能排除“裝飾性”修辭的情況,但是相較于專業抽象化的法言法語,引用傳統經典更契合民眾的一般價值觀念,更容易讓民眾理解與接受。
第三,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補充說明。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融入社會發展、融入日常生活”。自2018年與2020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別寫入憲法與民法典以來,我國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不少直接援引核心價值觀的裁判文書。功能主義以社會現實需求為導向,強調法律要實現特定的社會目標。觀察發現,“引經據典”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補強論證。例如,有相當數量的裁判文書引用了孔孟語錄、儒家經典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誠信”進行積極修辭。有法官在“本院認為”部分寫道:“誠信,即誠實信用,是做人之本,立業之基。孔子曰:民無信不立。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弟子規》說:凡出言,信為先。誠信,既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是公民基本道德準則,更是民事實體法律和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
遼寧省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鐵民二初字第00061號。類似援引儒家經典對誠信價值進行補充說明的案件還有不少,
可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終字第07324號、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法院(2018)魯0112民初1013號、四川省廣元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川08民終1070號、廣東省花都市人民法院(2021)粵0114民初13225號、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2021)京0115民初12966號等民事判決書。這反映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有研究分析認為,法官在適用民事習慣時往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統美德深度融合,并適當采取一些“文學化評述方式”
劉成安:《民法典時代民事習慣的司法適用——以援引〈民法典〉第10條的裁判文書為分析對象》,《法學論壇》2022年第3期。。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凝練,但核心價值觀表現為高度抽象凝練的價值語詞,法官在運用時往往將數個價值語詞并列引用,導致其對個案的說理論證效果不佳。比如,在一則排除妨害糾紛的上訴案中,法官運用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說理,并引用了“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但事實上,只有“友善”價值與本案較為契合。
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豫05民終4875號。由于價值文化上的共通性,傳統經典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補強論證功能。如在一些因鄰里關系產生的糾紛案件中,法官就常引用“遠親不如近鄰”“千金買屋,萬金買鄰”以及“六尺巷”的典故輔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說理。
可參見浙江省義烏市人民法院(2012)金義民初字第2293號;湖北省羅田縣人民法院(2013)鄂羅田鳳民一初字第00038號;安徽省廬江縣人民法院(2020)皖0124民初385號;黑龍江省林甸縣人民法院(2021)黑0623民初76號等判決書。目前,司法實踐中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案件越來越多,但如何將核心價值觀的論證與個案事實恰當融合仍須加強。較好的例子是,在同樣一則排除妨害糾紛上訴案中,法官在對相鄰關系進行解釋的基礎上,對案件事實輔助以孔子的論述進行修辭論證。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8民終2655號。總之,相較于單純列舉語詞,結合傳統典籍論述有助于闡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說明司法適用的原因。
三、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功能定位
功能主義研究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在實然層面,功能主義研究關注在特定社會環境中對某一項法律制度的功能進行解釋;在應然層面,功能主義研究包含對某一法律制度的實踐功能進行評價,以在理想狀態下對其進行功能定位。
勞東燕:《功能主義的刑法解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4—5頁。目前,司法“引經據典”的問題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但已有研究主要著眼于經驗分析與個案應用層面,司法“引經據典”是否具有正當性?換言之,“引經據典”在司法裁判中應當如何定位?這一問題需要從理論層面展開分析。
(一)對爭議判決進行引導與糾偏
依法裁判是司法的基本要求,但是在無法可依或者法律存在漏洞的情況下,傳統道德倫理能夠發揮對裁判的引導功能。以“江歌案”為例,根據現有的侵權責任法,法官很難追究劉鑫(劉暖曦)的侵權責任,但江歌受到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與劉鑫嚴重違背道義的行為存在一定關聯。考慮到若不追究劉鑫的法律責任將難以被社會大眾所接受,一、二審法院均做出劉鑫承擔侵權責任的判決。傳統道德倫理能夠引導裁判,原因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歷史文化上的延續性。在“北雁云依案”的裁判中,法官就結合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對于“姓”的文化認知,駁回了原告要求確認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絕為“北雁云依”辦理戶口登記行為違法的訴訟請求。該案還入選指導性案例,“裁判要點”指出:“公民選取或創設姓氏應當符合中華傳統文化和倫理觀念。”
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2010)歷行初字第4號裁判文書;指導案例89號:“北雁云依”訴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記案,https://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74112.html。
一些特殊情況下,嚴格依法裁判可能導致裁判不正義。一些具有社會影響的案件引起民眾的不滿,往往因為裁判結果與民眾的一般道德倫理觀念產生了偏差。以“于歡案”為例,孝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民眾對一審判決不滿的根本原因在于判決結果背離了民眾的一般倫理價值觀。二審法官充分考量了民眾對于“孝”“辱母”“復仇”的倫理認知,指出“于歡捅刺杜志潔等人時難免不帶有報復杜志潔辱母的情緒”,“杜志潔的辱母行為嚴重違法、褻瀆人倫,應當受到懲罰和譴責”等,對于歡在量刑上予以減輕處罰,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在“江蘇無錫冷凍胚胎案”中,由于法律并沒有對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予以明確規定,一審法院認為冷凍胚胎不能成為繼承標的,祖父母不能取得胚胎的所有權,判決引發了社會的爭議。二審充分考慮了倫理、情理因素,判決祖父母獲得胚胎的“監管權”與“處置權”。相關報道對二審判決結果表示了肯定,認為終審判決秉承了人文精神,展示了司法裁判對于生命、公民權利的充分尊重。
張寬明、鄭衛平:《無錫人體冷凍胚胎權屬糾紛案——老人享有子女遺留冷凍胚胎監管處置權》,《人民法院報》,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12/18/content_146973.htm,2023年3月19日。
一些情況下,傳統道德倫理能夠對裁判起到引導和糾偏功能,但是,這種影響僅限于法律存在漏洞或者裁判結果出現道德與法律嚴重沖突的情況。例如,“掏鳥窩案”與“趙春華非法持有槍支案”的一審判決雖然也引起了一定社會爭議,但二審法院在查明事實與法律的基礎上依舊認可了原審的定罪。
不同的是,考慮到社會危害性、主觀惡性等因素,法官在量刑上對后者予以從寬處罰。參見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新中刑一終字第128號;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津01刑終41號。總之,在案件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的案件中,傳統道德倫理不能影響案件的裁判結果。
(二)作為裁判說理的論據
質疑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觀點認為:其一,這類“以情動人的表達方式”與“崇高嚴肅的法律背道而馳”,“當事人拿到文采飛揚的判決書后卻不知所云”。其二,“引經據典”常表現為法官的道德說教,這種裁判方式容易“把法官的裁決者的角色異化為一位情理上的說教者,用法官的評價代替法律的評價”,混淆了法律與道德。戴璇:《司法判決書難以文學化》,《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就第一種觀點來說,這種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未免有些杞人憂天。正如有學者提到的,“我國的判決書離文學還遠著呢,更談不上判決書的‘文學化’了,而且這種觀點把我國普通公民的文化素質看得過低了,好像中國的社會大眾才剛脫離文盲”魏勝強:《當面說理、強化修辭與重點推進——關于提高我國判決書制作水平的思考》,《法律科學》2012年第5期。。
第二種觀點有參考價值,因此需要明確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功能定位:“引經據典”不是以道德判斷取代法律裁判,而是增強裁判說理。早在本世紀之初,蘇力教授就指出,中國的法官在司法裁判時常常借助西方法學理論、法律制度以及判例,而不是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來分析問題。
蘇力:《司法解釋、公共政策和最高法院——從最高法院有關“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釋切入》,《法學》2003年第8期。在裁判中“引經據典”,是一種結合中華傳統文化的說理論證方式。正如有研究指出:“因為‘經’、‘典’本身就是大眾公認的祖先們生活經驗的提煉和總結,也是古代圣賢的道德教誨,更是傳統文化的結晶。因此,借助判詞之‘引經據典’,司法權力從歷史傳統、道德和文化上獲得了正當性。”
陳煒強:《古代中國判詞之“引經據典”探析》,《上海政法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
司法裁判中,古代經典中的表述可以作為法官裁判說理的論據。比如,在張慶福、張殿凱訴朱振彪生命權糾紛案中,法院認定朱振彪的追趕行為是對張永煥逃逸行為的制止,屬于見義勇為,應予支持和鼓勵,不對肇事逃逸者張永煥的死亡承擔賠償責任。相關法官在對該案的案例評析中援引了《論語·為證》中的經典論述,“見義不為,無勇也”,“看到合乎道義的事,便勇敢地去做,甚至不顧個人安危,是大義。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屬于傳統的道德規范范疇”。
王佳、馬蓓蓓:《〈張慶福、張殿凱訴朱振彪生命權糾紛案〉的理解與參照》,《人民司法·案例》2021年第17期。司法裁判“引經據典”不僅是一種文學性的表述,更是援引經典當中的被民眾廣泛認同的價值理念進行裁判說理。
(三)增強裁判的說服力與可接受性
正如孫斯坦所言:“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不能避免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
CassR.Sunstein,LegalReasoningandPoliticalConflict,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21.既然司法道德考量難以避免,更應該追求論證的合理與充分。“引經據典”是一種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裁判說理方式,體現了我國裁判說理風格。比如,“冷凍胚胎案”的二審判決書指出:“白發人送黑發人,乃人生至悲之事,更何況暮年遽喪獨子、獨女!沈杰、劉曦意外死亡,其父母承歡膝下、縱享天倫之樂不再,‘失獨’之痛,非常人所能體味。而沈杰、劉曦遺留下來的胚胎,則成為雙方家族血脈的唯一載體,承載著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撫慰等人格利益。”
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錫民終字第01235號。“引經據典”增強裁判說服力與可接受性的原因在于:古代典籍中的先哲論述、傳統典故更貼近我國民眾的一般倫理價值觀。相較于抽象的法言法語,傳統道德話語更接近普通民眾的日常話語,更容易實現對話與交流。
實際上,“彰顯文采”是“引經據典”附帶的功能,“引經據典”的真正功能是增強裁判的說服力與可接受性。接受是一種心理上的認同,是內心對某種觀點的真誠接受,一份可接受的判決并不是單純依靠華麗的辭藻實現的。以“江歌案”為例,法官在判決書中肯定了江歌“扶危濟困”的“美德義行”,對劉鑫“背信負義”的行為進行譴責。
可參見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2019)魯0214民初9592號、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魯02民終1497號二審等民事判決書。有學者指出,正是這種“基于社會公共道德和主流意識形態價值相一致的審判立場,才是其判決獲得社會公眾普遍贊譽的主要原因”
魏治勛:《司法裁判的道德維度與法律方法——從江歌案民事一審判決的道德爭議切入》,《法律科學》2022年第5期。。相較于在判決書中引用《圣經》、“法諺”等西方話語,引用中國傳統經典進行說理與修辭,無論對當事人還是一般民眾來說都更符合文化認知,更容易讓人理解與接受。
四、當代中國司法裁判“引經據典”的限度
“引經據典”不僅是中國古代判詞特有的論證風格,也是中國古代審判特有的裁判方法。及至當代,立法層面對于傳統道德倫理的價值愈發重視,比如,202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納入“婚姻家庭編”,將家事法律關系集成化,并新增“優良家風”的內容。此外,像傳統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思想、誠信文化等傳統理念,民法典也對其進行了精神傳承。
蔣海松:《〈民法典〉傳統基因與民族特色的法理解析》,《現代法學》2022年第1期。前文研究表明,“引經據典”作為裁判說理的論據,具有對裁判進行引導與糾偏以及增強裁判說服力與可接受性的功能。但是,現代司法建立在以形式法治為基礎的裁判理論基礎之上,法官自由裁量特別是道德裁判需要嚴格規制,“引經據典”需要遵循必要的限度。
(一)裁判“引經據典”的內容限度
功能主義理論源于現實主義法學,相較于規范法學對形式與邏輯的關注,強調法律如何實現特定的功能。傳統經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司法裁判中恰當融合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可以發揮社會價值引領功能。正如有研究指出:“根植的優秀傳統文化具有親和感、說服力與普遍性,運用正面的典故、引據俗語均能起到較好的說服效果,實現法的社會導向效用。”
孫海龍:《“充分說理”如何得以實現——以行政裁判文書說理為考察對象》,《法律適用》2018年第21期。但是,我國歷史悠久,中華傳統文化中文明與糟粕并存。傳統經典是古代社會的產物,其中很多價值理念與追求已經與現代社會不相契合。像是等級制度分明、繁瑣禮儀、愚忠愚孝、女性地位低下等,在裁判文書中引用這類糟粕價值觀明顯不合時宜。應當明確,當代司法裁判“引經據典”強調吸收傳統文化中優秀的一面,被時代主流價值觀拋棄的糟粕文化需要摒棄。
法官在“引經據典”時應采取審慎的態度,對援引內容進行篩選。比如,傳統文化所強調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與現代法治追求的平等理念相違背。此外,在不同歷史階段,傳統美德的內涵和標準是不一樣的。在封建社會時期,“孝”的內涵是“父為子綱”,因此法律賦予父母對子女一定程度的懲罰權,而在當代社會中,“孝”的內涵被賦予一定平等色彩,強調“孝親敬老”“老有所養”。又如,在身份關系上,封建中國的家庭成員沒有婚姻自主權,婚姻不屬于個人私事,而是家庭大事,婚姻依據的是父母之命,而不是個人之意。這一點在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典型案例中,就明確了“子女受父母脅迫結婚可請求依法撤銷婚姻”的裁判觀點。因此,法官在裁判文書中“引經據典”時需要對經典的內容進行篩選,保障引用內容符合現代民主法治理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二)堅持以依法裁判為前提
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形式法治,裁判“引經據典”要堅持以依法裁判為前提。因此,法官要在正確適用法條的情況下“引經據典”。一定意義上說,“引經據典”與依法裁判并不矛盾:一方面,在司法裁判中,后果考量或者道德考量難以避免
孫海波:《論道德對法官裁判的影響》,《法制與社會發展》2022年第5期。,傳統經典可以作為后果考量的依據來源;另一方面,“引經據典”指援引古代經典論述輔助裁判說理,屬于一種“積極修辭”。換言之,古代經典論述在裁判中不是正式法源,而是法官進行裁判說理或修辭的論據。
總結來說,法官在裁判中“引經據典”需要注意:其一,準確適用法條是“引經據典”的前提。不同于古代“春秋決獄”“引經決獄”直接依據儒家道德倫理進行裁判的做法,傳統經典論述在當代不能作為裁判依據。在援引傳統經典論述的場景,法官需要注意法律推理過程以及文書寫作以正式法源作為裁判依據。其二,“說理”不能取代“釋法”。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近年來在強化裁判文書的釋法說理改革中,似乎出現一種過于強調‘說理’而弱化‘釋法’的現象或苗頭”
李友根:《論裁判文書的法條援引》,《中國應用法學》2022年第2期。。功能主義應建立在形式主義的基礎上,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功能主義解釋“處于一種戴著鐐銬跳舞的狀態”,“要在法律之內尋求社會效果”。
勞東燕:《功能主義刑法解釋論的方法與立場》,《政法論壇》2018年第2期。這要求法官在注重實現社會效果的同時,要堅持以依法裁判為前提,保障裁判依據的正確引用與恰當論證。
(三)遵循適當性與必要性原則
“引經據典”并不是我國司法裁判的普遍現象,而存在于特殊案件中。第一,裁判文書“引經據典”在民事案件特別是家事案件中較常出現,因為這類案件涉及家庭關系、人際交往等道德倫理爭議。第二,“引經據典”體現了法官的裁判文書書寫風格,具有個人特色。第三,“引經據典”在某些社會影響案件中存在適用空間,因為這些案件可能出現道德與法律沖突的情況。當前,我國裁判文書過于格式化、說理不足的問題亟待解決,在審判中恰當援引傳統經典論述可以增強裁判的說服力與可接受性。但應當明確,“引經據典”僅僅是對于裁判的修辭論證技巧與方法,不能取代法律適用及推理。在無需援引的場所“引經據典”不僅起不到增強說服力的效果,反而是“畫蛇添足”,損害司法的權威與公信力。
司法裁判追求法制度的安定性與法體系的融貫性。當前,我國較常出現法官“引經據典”進行道德教化或者彰顯文采而忽視“釋法”的情形。例如,在某二審案中,法官認為案件的客觀情況是初意投資,但實為借貸,因而對原審進行改判。在說理過程中,法官先后引用了《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規》以及《中庸》等經典論述,并且引用了林則徐語錄
浙江省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浙08民終686號。。從功能上來說,這些經典論述無助于案件的解決,有冗余之嫌。實踐中,即便法官援引了古代經典論述對判決進行修辭論證,仍需要重視法律推理的邏輯性、嚴謹性。既不能“信而不美”,也不能“美而不信”。因為“修辭的核心是論證,是意在實現合理性認同的推理,盡管較之形式推理,它具有文采修飾和情感調動因素,但這些都必須服務于所要論證的內容”
戴津偉:《法律修辭的功能及其隱患》,《求是學刊》2012年第3期。。總之,“引經據典”的前提是法條適用的準確,在確實需要援引古代經典論述修辭論證時,要保證法律推理過程的完整與嚴謹。
五、結語
在審判中援引先哲語錄、諸子論述,既是古代法官的判詞風格,也是傳統中國特有的司法審判方法。我國傳統典籍中蘊含著諸多關于道德倫理、行為規范的經典論斷,這些論斷至今仍對民眾的行為規范、法律認識發揮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近些年來,一些具有社會影響的案件嚴重損害了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這些案件之所以不被社會所接受,其重要原因在于判決結論與民眾的一般道德認知存在沖突。對于一些涉及傳統道德倫理的案件,法官往往需要綜合考量法、理、情等因素。古代典籍所蘊含的傳統哲理、倫理,更契合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法官在判決書中適當援引經典論述進行修辭論證,能夠增強裁判的說服力與可接受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凝練,針對當前核心價值觀在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裝飾性”引用、與案件事實結合不充分等問題,恰當結合傳統經典論述能夠增強核心價值觀論證的融貫性。當然,現代司法裁判不同于古代的情理審判,“引經據典”在功能上僅僅是一種“補充”而非“替代”,依法裁判是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法官引用傳統典籍論述時需要遵循必要的限度,避免“功能主義的論證壓倒規范主義的論證”
陳金釗:《實質法治思維路徑的風險及其矯正》,《清華法學》2012年第4期。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