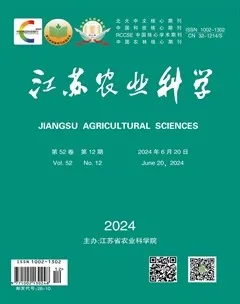土壤改良措施對參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








摘要:為探究土壤改良措施對參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篩選老參田土壤改良最優方案,進行大田種植土壤改良試驗,設置3個處理組,即棉隆土壤熏蒸組(A)、高錳酸鉀化學消毒組(B)、微生物菌肥組(C),并以未改良土壤為空白對照組(CK)。通過高通量測序技術分析不同處理方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變化,綜合評價不同參田土壤改良措施。結果表明,在12個改良參田土壤中共檢測537 766個細菌有效序列,701 028個真菌有效序列;土壤細菌在門分類水平上,改良組放線菌門、綠彎菌門、厚壁菌門等的相對豐度均大于空白對照組,土壤真菌在門分類水平上,被孢霉門的相對豐度明顯高于空白對照組。在微生物屬分類水平上,處理組有益菌芽孢桿菌屬、鞘氨醇單胞菌屬、熱酸菌屬、青霉菌、毛殼菌屬的相對豐度明顯高于空白對照組,而引起植物病害的鐮刀菌屬、芽枝霉屬在處理組中的相對豐度呈下降趨勢。空白對照組土壤中鞘氨醇單胞菌屬、熱酸菌屬的相對豐度高于處理組,在西洋參短期連作體系中,預測土壤中微生物可產生抵御病害的生防菌,維持植物正常生長。總之,在土壤改良措施中,3種處理方法都有利于有益菌和生防菌豐度的增加,土壤修復以C組最好,A組次之,B組效果較差。
關鍵詞:西洋參;高通量測序;土壤改良;連作障礙;微生物
中圖分類號:S567.5+30.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4)12-0261-08
西洋參(Panax quinquefolium L.),為五加科人參屬多年生草本植物,原產于北美洲,我國自1970年引種成功后,開始規模化種植。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我國已形成三大西洋參種植基地,主要分布在東北、華北、西北等地區[1]。連作的集約化、現代化農業生產模式是最常見的耕作制度,人參屬植物在種植過程中易產生嚴重的連作障礙,這極大地制約了西洋參產業的發展[2]。
目前,引起西洋參連作障礙的發生機制已基本明確。老參田土壤微生物群落失衡是導致西洋參再植過程中土傳病害發生的直接原因,而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結構組成是衡量參田土壤健康情況的重要指標[3]。研究表明,在西洋參連續種植土壤中,假單胞菌(Pseudomonas spp.)、芽孢桿菌(Bacillus)顯著減少,而引起植物根腐病的主要病原菌鐮刀菌(Fusarium)呈現增加的趨勢[4-6]。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與土壤理化性質、施肥方式、土壤質地等有關[7]。本研究通過高通量測序技術分析不同改良措施對老參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以期篩選出最佳改良方法以及土壤中抵抗連作障礙的優勢菌群,為西洋參連作障礙防治提供數據支持。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概況
試驗在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大水泊鎮大水泊村西洋參種植基地(37°10′N,122°13′E)進行,該地處于山東半島東部,年平均氣溫13 ℃,年平均降水量767.8 mm,種植方式主要以一年兩作(冬小麥、夏玉米)為主。供試土壤類型為沙質壤土。試驗用地為2020年10月收獲后的西洋參參田。
1.2 材料與試驗設計
供試西洋參種質由威海市文登傳福參業有限公司提供。供試藥劑98%棉隆微粒劑(土壤熏蒸劑)、高錳酸鉀(化學消毒)、微生物菌肥(有效活菌數≥2.0 億個/mL EM濃縮菌)均購自濟南兆龍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選取當年收獲西洋參的土壤作為試驗用地,在種植西洋參之前對土壤進行處理。試驗共設計4組,即棉隆土壤熏蒸組(A組)、高錳酸鉀化學消毒組(B組)、微生物菌肥組(C組)、采參后未作處理的土壤為空白對照組(CK)。A組藥劑施用量為30 g/m2,熏蒸劑施用完成后立即覆蓋塑料薄膜,密閉熏蒸 30 d 后,揭膜晾曬30 d。B組使用噴霧器將0.1%高錳酸鉀均勻噴于土壤表面,然后立即用塑料薄膜覆蓋密封,曝曬7 d。C組施用菌肥用量為 6 mL/m2,一次性施入西洋參種植壟內。每個處理3次重復,共12個小區,小區面積50 m2,每個小區間隔1 m緩沖區。除處理方式不同外,田間管理參照西洋參山東地區種植時間結合西洋參生長習性進行統一管理。
1.3 土壤樣品采集
土壤樣品于2021年10月,按照隨機、同質、多點混合的原則,用不銹鋼采樣器從耕作層(0~20 cm)采集,過2 mm網格后,去除土壤中石頭等雜質。每個處理組采集9份土壤樣品,混勻后,分別裝在3個無菌袋中,放在液氮中,-80 ℃ 保存。
1.4 土壤微生物PCR擴增與高通量測序
對土壤樣品基因組DNA進行抽提,利用1%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抽提DNA,檢測DNA完整性后,進行PCR擴增(TransStart Fastpfu DNA Polymerase),每個樣本3個重復,將同一樣本的PCR產物混合后,利用2%瓊脂糖凝膠進行電泳檢測,使用AxyPrepDNA凝膠回收試劑盒(AXYGEN公司)切膠回收PCR產物,并利用Tris-HCl進行洗脫;將同一樣本的PCR產物混合后用2%瓊脂糖凝膠進行電泳檢測,使用熒光定量計檢測提取的DNA濃度,當濃度檢測合格后,進入下一步基因文庫的構建。
以特異性引物338F(5′-ACTCCTACGGGAGGCAGCAG-3′)和806R(5′-GGACTACHVGGGTWTCTAAT-3′)對土壤細菌16S V3~V4區進行PCR擴增;選擇PCR擴增通用引物ITS1F和ITS2R(ITS1F:5′-CTTGGTCATTTAGAGGAAGTAA-3′;ITS2R:5′-GCTGCGTTCTTCATCGATGC-3′)對土壤真菌ITS區進行擴增。DNA片段的一端與引物堿基互補,以DNA片段為模板進行PCR合成;經過變性、退火,DNA片段的另一端隨機與附近的另外一個引物互補,形成“橋(bridge)”;經過PCR擴增,產生DNA簇;DNA擴增子線性化成為單鏈。加入改造過的DNA聚合酶和帶有4種熒光標記的dNTP,每次循環只合成1個堿基;用激光掃描反應板表面,讀取每條模板序列第1輪反應所聚合上去的核苷酸種類;將“熒光基團”和“終止基團”進行化學切割,恢復3′端黏性,繼續聚合第2個核苷酸;統計每輪收集到的熒光信號結果,獲知模板DNA片段的序列。構建MiSeq文庫將其用于Illumina MiSeq PE300平臺進行高通量測序。
1.5 數據分析
通過高通量測序得到的雙端序列經拼接與質控抽平得到優化序列,采用Usearch(http://www.drive5.com/usearch/)對優化序列進行OTU統計,對97%相似水平的用uparse(http://www.drive5.com/uparse/)與RDP Classifier(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進行OTU聚類、序列分類注釋;采用Mothur(https://www.mothur.org/wiki/Down)進行α多樣性分析[8];采用Qiime計算β多樣性距離矩陣,然后用R語言(version 3.3.1)繪制可視化樹狀圖。運用R語言配合vegan包進行數據多樣性分析;用PICRUST軟件進行土壤細菌功能預測[9]。
2 結果與分析
2.1 參田土壤細菌的組成及多樣性分析
運用16S RNA、ITS對改良土壤中的細菌、真菌進行測序,從12個土壤樣品中共獲得537 766個有效序列,平均長度為414 bp。在97%的高通量序列相似性水平上進行聚類,共檢測到2 759個OTU,其中C組的OTU數量高于其他3組(圖1-Ⅰ)。通過繪制土壤細菌稀釋曲線[10]發現,每個樣品的OTU稀釋曲線隨著讀取樣本量的增加趨近平緩,測序數據逐漸達到飽和(圖1-Ⅱ)。目前的測序量能夠覆蓋樣本中的絕大多數物種,測序數據可用于后續土壤細菌多樣性分析。由表1可知,3個處理組參田Shannon指數與CK相比數值均降低,C組的Simpson指數高于其他3組。與其他處理相比,CK組的Chao1指數和ACE指數較高,但B組處理土壤Chao指數和ACE指數較低。
基于Bray-Curtis距離進行分層聚類分析[11],結果(圖1-Ⅲ)顯示,樣品可劃分為4個高度聚集群,說明不同改良處理土壤樣品中的細菌群落比較相似。此外,A組、B組、CK組的細菌群落基本聚集,而C組的土壤樣品與其他組分離。基于OTU豐度的非度量多維尺度分析(NMDS)[12](stress=0.112)結果(圖1-Ⅳ)表明,A組、B組、CK組樣品高度相似并聚集,與C組的樣品明顯分離,與層次聚類分析的結果相似。
在97%的相似度水平上對測序土壤樣品OTU代表序列進行分類學分析,參田土壤在細菌序列中共分出34門、104綱、230目、365科、643屬、1 189 種。在門水平上,將相對豐度小于1%的土壤細菌歸于其他(others),共得到34個類群,在相對豐度排名前10的物種中,各組群落結構的豐富度差異明顯(圖2-Ⅰ),其中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ota,26.23%~39.06%)為4組土壤中的優勢菌門,其他優勢菌門依次為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10.62%~2.83%)、綠彎菌門(Chloroflexi,10.45%~17.08%)、酸桿菌門(Acidobacteriota,9.17%~15.48%)、厚壁菌門(Firmicutes,3.53%~13.92%)、芽單胞菌門(Gemmatimonadota,1.99%~4.56%)、Patescibacteria(1.48%~6.55%)、擬桿菌門(Bacteroidota,0.66%~4.98%)、WPS-2(0.56%~1.79%)、黏球菌門(Myxococcota,0.62%~1.09%),占各組序列的90%以上。其中3個土壤改良組的放線菌門、綠彎菌門、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均大于空白對照組,而變形菌門、Patescibacteria、擬桿菌門、WPS-2、黏球菌門的相對豐度在空白對照組土壤中高于其他3個處理組。
在屬水平上,共檢測到21個細菌屬(圖2-Ⅱ),平均相對豐度高于2%。由表2可知,CK組中norank_f__JG30-KF-AS9(3.96%)、Rhodanobacter(5.36%)、Candidatus_Solibacter(2.38%)、norank_f__norank_o__Saccharimonadales(2.37%)、norank_f__LWQ8(2.63%)、黏液桿菌屬(Mucilaginibacter,2.69%)等6個屬的相對豐度高于A、B、C組。A組中unclassified_o__Acidobacteriales(3.54%)、苔蘚桿菌屬(Bryobacter,2.23%)、Chujaibacter(3.32%)、orank_f__norank_o__Subgroup_2(2.05%)等4個屬的相對豐度較高。B組中norank_f__norank_o__Gaiellales(11.24%)、熱酸菌屬(Acidothermus,4.83%)、norank_f__Gemmatimonadacea(3.62%)、norank_f__SC-I-84(2.22%)、norank_f__norank_o__Elsterales(2.17%)、鏈霉菌屬(Streptomyces,2.01%)等6個屬的相對豐度較高。C組中節桿菌屬(Arthrobacter,11.80%)、芽孢桿菌屬(Bacillus,4.22%)、norank_f__norank_o__norank_c__KD4-96(2.73%)、鞘氨醇單胞菌(Sphingomonas,2.16%)、八疊球菌屬(Sporosarcina,2.88%)等5個屬的相對豐度較高。
2.2 改良參田土壤真菌的組成及多樣性分析
12個土壤樣品經過質量過濾后,共獲得 701 028 個真菌有效序列。真菌序列的平均長度為232 bp,在97%的高通量序列相似性水平上進行聚類,共獲得1 448個OTU,由圖3-Ⅰ可知,4組土壤真菌共享322個OTU,其中A組與空白對照組土壤真菌共享87個OTU,B組與空白對照組土壤真菌共享73個OTU,C組與空白對照組土壤真菌共享30個OTU。A組土壤真菌獨有142個OTU,B組土壤真菌獨有299個OTU,C組土壤真菌獨有91個OTU,CK組土壤真菌獨有93個OTU。基于OTU的所有樣品稀釋曲線均達到其漸近線(圖3-Ⅱ),表明本研究中產生的數據足以分析真菌多樣性。
α多樣性分析結果(表3)表明,與空白對照組相比,3個處理組參田土壤的Shannon指數相對較高。此外,空白對照組土壤的Simpson指數高于其他土壤,而A組、C組土壤中的ACE指數和Chao1指數低于CK組。分層聚類分析結果(圖3-Ⅲ)表明,A組、C組、CK組土壤樣品中的真菌群落更為相似且較為聚集,與B組中的真菌群落明顯分離。此外,在不同改良方法中,B組的參田土壤真菌群落成簇,與空白對照組土壤分離明顯,但B1、C3、CK2處理組土壤由于重現性差除外。基于OTU豐度進行NMDS(stress=0.081),結果(圖3-Ⅳ)表明,所有樣品分為4類。A組、C組、CK組的土壤樣品高度相似并聚集,與B組土壤樣品分離。這一結果與層次聚類分析結果相似。
老參田土壤真菌在門水平上,將相對豐度小于1%的土壤真菌歸于others,檢測到的參田土壤真菌涵蓋6個類群、14門、44綱、97目、205科、369屬、577種。在所有樣品中,子囊菌門(Ascomycota,48.50%~58.49%)的相對豐度最高(圖4-Ⅰ),其次是擔子菌門(Basidiomycota,25.16%~38.19%)、被孢霉門(Mortierellomycota,7.04%~17.9%)、unclassified_k__Fungi(1.48%~5.26%)、羅茲菌門(Rozellomycota,0.23%~1.87%)、壺菌門(Chytridiomycota,0.43%~1.05%)。A組子囊菌門的相對豐度高于其他3組,而unclassified_k__Fungi、羅茲菌門的相對豐度明顯低于其他3組。CK組擔子菌門的相對豐度高于其他各組。
在屬水平上,共檢測到25個真菌屬(圖4-Ⅱ、表4)。不同改良方法處理下土壤中優勢真菌群落的相對豐度不同,空白對照組土壤中有7個屬[Saitozyma、Hannaella、Neonectria、芽枝霉屬(Cladosporium)、附球霉屬(Epicoccum)、Tausonia、毛喙殼屬(Chaetomidium)]的相對豐度高于其他3個處理組。A組中Solicoccozyma、籃狀菌屬(Talaromyces)、Naganishia、鐮刀菌屬(Fusarium)、unclassified_o__Helotiales、unclassified_c__Sordariomycetes、Paraphaeosphaeria、Holtermanniella、毛殼菌屬(Chaetomium)、杯梗孢屬(Cyphellophora)的相對豐度均高于B組、C組、CK組。此外,被孢霉屬(Mortierella)、unclassified_k__Fungi、樹粉孢屬(Oidiodendron)、瓶毛殼屬(Lophotrichus)、unclassified_o__Trechisporales的相對豐度在B組中最高。青霉菌(Penicillium)、枝頂孢屬(Acremonium)、帚枝霉屬(Sarocladium)的相對豐度在C組中最高。
3 討論
土壤是微生物的生存環境,土壤微生物參與調節大部分的土壤活動,尤其在土壤養分的轉化和循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3-14]。在西洋參連作系統中,根系不斷向土壤中分泌相同類型的分泌物, 可能會促進某些微生物物種在土壤中定殖,最終引起土壤微生物多樣性降低[15]。從土壤α多樣性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土壤改良可以增加參田土壤中細菌和真菌的相對豐度和多樣性。 β多樣性分析(NMDS)結果再次驗證了不同土壤改良措施對參田土壤微生物菌群結構的影響。A組、B組、C組土壤中的細菌和真菌群落存在明顯差異,其中A組與CK組的土壤細菌、真菌群落結構相似度較高,說明土壤熏蒸在短時間內對土壤微生物有一定的滅活作用,隨著植物生長時間的延長,其作用隨著主要物質的分解而逐漸失效。
土壤改良可顯著改善參田土壤細菌和真菌群落結構。在細菌主要的21個屬中,C組芽孢桿菌屬的相對豐度顯著高于A組、B組和CK組,而芽孢桿菌是促進植物生長的細菌[4],它不僅對番茄病原菌尖孢鐮刀菌和番茄早疫病病菌具有抑制作用,還可產生吲哚-3-乙酸和其他促生長因子,促進離體植物生長[4]。B組、C組中的鞘氨醇單胞菌屬、熱酸菌屬的相對豐度明顯高于A組、CK組,其中鞘氨醇單胞菌屬細菌作為土壤中的生防菌,有助于抑制病原體入侵,而熱酸菌屬細菌可促進土壤中的微生物分解有機質、利用碳源[2]。對于真菌,所有處理中的優勢屬為青霉菌屬、Tausonia、毛殼菌屬、鐮刀菌屬、芽枝霉屬等,其中青霉菌屬、Tausonia、毛殼菌是具有生物防治效果的有益真菌[11],鐮刀菌屬、芽枝霉屬真菌是引起植物病害的主要植物病原菌[6]。鐮刀菌是被廣泛報道的主要土傳病害的病原菌,可引起西洋參褐色根腐病和枯萎病。由此可以看出,在土壤改良中,3種處理方法都有利于有益菌和生防菌相對豐度的增加,但各處理效果有所差異,其中C組最好,A組次之,B組效果較差,主要是由于C組用于改良土壤的微生物菌肥含有益生防菌,在西洋參再植過程中土壤中的青霉菌屬等的相對豐度增加,可促進土壤微生物修復。土壤微生物的能量代謝,特別是礦質養分代謝過程,對植物的生長極為關鍵。同時,參與碳循環的微生物需通過高能量的代謝途徑,獲得生長所需的營養物質[16]。
4 結論
西洋參連續再植經過土壤修復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有一定的影響,不同處理方式與空白組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對比空白組,在不同處理后的老參田土壤中試劑組細菌和真菌的多樣性指數相對較低。此外,不同處理方式短期處理連坐土壤西洋參再植后,處理組中潛在的植物病原真菌和有益細菌表現出協同增加的趨勢。相反,在不進行處理的土壤中連續種植西洋參后,土壤中的有益細菌和真菌數量有所減少,推測這2類微生物之間可能存在相互制約的關系。結合棉隆、高錳酸鉀化學屬性推測,大田試驗中棉隆土壤熏蒸、高錳酸鉀土壤消毒處理可能在土壤處理初期抑制或殺滅部分有害菌或有益菌,但隨著時間的延長試劑揮發或者分解,其抑菌效果逐漸減弱。微生物菌肥可補充土壤有益菌群,微生物菌肥可改善重茬土壤菌群結構及多樣性,結合檢測菌群豐度與空白組對比可推測隨著種植時間的延長需要持續補充菌群以維持再植西洋參正常生長。基于上述結果,推測再植后植物的生長可能取決于致病微生物和有益微生物之間的競爭。然而,致病菌和有益菌是否以及如何相互作用還需要進一步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1]Chen J,Zhou L T,Din I U,et al. Antagonistic activity of Trichoderma spp.against Fusarium oxysporum in rhizosphere of Radix pseudostellariae triggers the expression of host defense genes and improves its growth under long-term monoculture system[J].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2021,12:579920.
[2]孫子欣,蔡柏巖. 連作對土壤微生物菌群影響及修復研究進展[J]. 作物雜志,2022(6):7-13.
[3]Wu H M,Fang C X,Malacrinò A,et al. Editorial:rhizosphere conversation among the plant-plant microbiome-soil under consecutive monoculture regimes[J].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2022,13:1061427.
[4]Liu Q W,Wang S X,Li K,et al. Responses of soil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munities to the long-term monoculture of grapevine[J].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2021,105(18):7035-7050.
[5]Xu X J,Luo Q Y,Wei Q C,et al. The deterioration of agronomical traits of the continuous cropping of Stevia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ynamics of soil bacterial community[J].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2022,13:917000.
[6]劉麗娟,佟愛仔,秦佳梅. 天然闊葉林下不同年生人參根際微生物群落多樣性[J]. 吉林農業大學學報,2024,46(2):246-254.
[7]游浩宇,陳大剛,徐開未,等. 不同改良措施對獼猴桃園土壤理化性質變化的影響[J]. 四川農業大學學報,2022,40(6):826-837.
[8]楊艾華. 西洋參栽培過程中土壤微生物群落、養分和酶活性的變化及其相互關系[D]. 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7.
[9]劉亮亮. 強還原土壤消毒防控土傳病害效果及其微生物學機制研究[D]. 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9.
[10]Semenov M V,Krasnov G S,Semenov V M,et al. Does fresh farmyard manure introduce surviving microbes into soil or activate soil-borne microbiot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1,294:113018.[HJ2mm]
[11]聶揚眉,步連燕,陳文峰,等. 高量秸稈還田配施芽孢桿菌對沙化土壤細菌群落及肥力的影響[J]. 環境科學,2023,44(9):5176-5185.
[12]付寬寬,王小兵,汪曉麗,等. 不同改良措施對設施芹菜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J]. 中國瓜菜,202 5(8):42-49.
[13]朱 怡,吳永波,安玉亭. 基于高通量測序的禁牧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J]. 生態學報,2022,42(17):7137-7146.
[14]李榮飛,楊仕品,王愛華,等. 不同調控措施對草莓連作大棚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響[J]. 江蘇農業科學,2023,51(3):197-204.
[15]閆 寧,戰 宇,謝昊臻,等. 不同改土方式對連作人參生長發育的影響[J]. 江蘇農業科學,2022,50(6):120-125.
[16]孫鵬洲,羅珠珠,李玲玲,等. 黃土高原紫花苜蓿種植對土壤反硝化細菌群落的影響[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中英文),2023,31(1):67-78.
收稿日期:2023-07-13
基金項目:中央轉移支付項目(編號:202219);濟南市農業應用技術創新計劃(編號:CX202112);山東省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工程(編號:2022TSGC1059);山東省中醫藥科技發展計劃(編號:2021Q125);中央本級重大增減支項目(編號:2060302);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編號:2017YFC1701500、2017YFC1701502、2017YFC1701504)。
作者簡介:郭瑞齊(1989—),女,山東菏澤人,碩士,助理研究員,從事中藥質量與資源研究。E-mail:guoruiqi14@163.com。
通信作者:林慧彬,博士,研究員,從事中藥質量與資源研究。E-mail:linhuibin6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