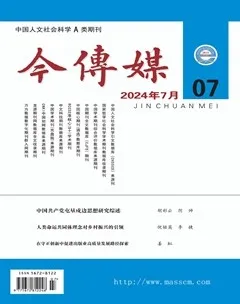在守正創新中促進出版業高質量發展路徑探索
摘 要:本文基于我國出版業主要成就和優良傳統的歷史考察,總結提煉出版業高質量發展中守正創新的歷史文化資源,在賡續優良傳統的同時,提出促進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旨在為新時代出版事業發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出版業高質量發展;守正創新;賡續傳統
中圖分類號:G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4)07-0072-04
出版業作為一種傳統且現代的文化產業,既是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陣地,又具有產業經濟的特點。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出版工作者既要賡續傳統出版業的優良傳統,又要緊跟時代發展,抓住新機遇,不斷開拓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堅持守正創新。對文化建設來說,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新時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須以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1]在守正創新中推進出版業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新時代出版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出版物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載體,我們要做好出版工作,堅守“兩個結合”根本要求,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
一、我國出版業主要成就和優良傳統的歷史考察
我國近現代出版業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創造了許多優良傳統,這些制度和傳統被當代出版業繼承和發揚。鴉片戰爭后,西方傳教士在我國通商口岸創建了一些出版機構,翻譯并印刷書籍,發行報刊。1897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立,此后,中國人自己創建的出版機構紛紛涌現。科舉制度廢除以后,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將編輯出版作為自己的事業,他們整理中華優秀典籍、翻譯西方圖書、編寫新式教科書。當時新書和雜志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傳播先進文化、開啟民智的作用,間接促進了民主革命的發生,推進歷史進程。近現代出版家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優良傳統,這些優良傳統是我們“守正”的重要歷史資源。
(一)出版者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近代中國處于內憂外患之中,當時的出版者具有強烈的救國意識,發行的出版物面向社會各階層成員,具有救亡圖存、啟迪民智的功能。例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創辦了強學會,將辦報紙列為“最要者四事”之一,不僅先后創辦了《清議報》《時務報》《知新報》《新民叢報》等報刊,還創建了大同譯書局、廣智書局等圖書出版機構,刊印了《大彼得變政考》《經世文新編》等書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辦,孫中山撰寫發刊詞,將同盟會的革命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即三民主義,主要撰稿人章炳麟、胡漢民、陳天華、宋教仁等皆為一時之選。可見,近代以來出版業的覆蓋面和影響力擴大到了全社會,成為宣傳新思想、新觀念的利器。這一時期,出版物是宣傳維新、救亡圖存的必要手段,也是傳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有效途徑。
(二)出版業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編輯、印刷、發行體系
我國古代書籍主要有官刻、私刻、坊刻三種。官刻是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行為,所刻之書多為儒家經典、史學著述、帝王御纂之書,主要目的是教化民眾、穩定封建統治秩序。私刻主要是為了宣傳個人作品,不以營利為追求。坊刻以營利為目的,所刻之書多為民間市場需要的讀物,屬于商業行為。但是,古代的坊刻與近現代的企業并不相同。我國具有產業化特征的出版企業始于近代開埠的通商口岸,以上海的企業最具代表性。1861年11月創刊的《上海新報》,系北華捷報館創辦,由字林洋行發行。1872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創辦《申報》、申昌書局、點石齋書局、圖書集成印書局等機構,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編輯、印刷、發行體系。清末至民國,全國采用石印技術的機構達上百家,其中較大的機構如同文書館,有石印機12架,雇工500人,規模很大[2]。商務印書館創辦以后,企業化運營的出版企業逐漸增多,我國出版產業進入大發展時期。近代以來,圖書報刊發行方式多樣化,主要包括門市銷售、組織發行網絡、預約征訂、寄售等,這些發行方式對于出版物的廣泛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出版企業內的體系完整,各環節相互配合,使出版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運營模式。這種模式被后來的新聞出版業所繼承,在全國報社和出版社中實行。
(三)編輯工作職業化、專業化
我國古代讀書人雖然也編輯過不少作品,但他們或是在治學之余編選書籍,這種偏重于編選,而不是編輯;或是出于自身工作需要,如翰林院編修從事史書纂修等,一旦升遷或調職,可能就不再從事相關工作。可以說,古代基本上沒有職業化的編輯。到了近現代,尤其是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很多讀書人通經致仕的道路沒有了,他們轉向現實,尋找既能用得上自己平生所學,又能賺取一定生活之資的職業。此時,恰逢新聞出版業大發展時期,專門從事寫作或編輯工作成為不少讀書人的選擇。有的人從事寫作,靠稿費生存;有的人從事編輯,靠工資生活;有的人既寫作又編輯,還有一些知識分子成為了職業編輯。
鄒韜奮的出版經歷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在上海圣經翰大學讀書期間為了掙學費和生活費,兼職寫稿、做家庭教師、在厚生紗廠和上海紗布交易所工作等,后來兼職擔任英文教員和編輯,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編輯股主任,編輯了6種職業教育叢書和3種其他譯著。1925年10月,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了《生活》周刊,起初王志莘擔任主編,鄒韜奮只是時常幫助寫些文章。一年后,王志莘投身于銀行業,才由鄒韜奮擔任《生活》周刊主編,這是他正式從事新聞出版業的開始。鄒韜奮同時兼任《時事新報》秘書主任,主編該報副刊《人生》。隨著《生活》周刊業務迅速發展,他才辭去《時事新報》和《人生》的工作。此后,在鄒韜奮的主持下,《生活》周刊成為深受讀者歡迎的知名雜志,每期發行量由他剛接手時的2800份到1933年達到了15萬5000份,打破了當時中國雜志的發行紀錄[3]。由兼職到專職,進而取得顯著成就,這就是編輯工作職業化的優勢。
此外,編輯工作專業化也是近代出版業的突出特點。1903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成立,張元濟擔任所長,并聘請了一批專業人才。例如,聘請高夢旦擔任國文部主任,蔣維喬、莊俞等任國文編輯,杜亞泉為數理部主任,同時還聘請了不少留學回來的專業人士以及國內的大學畢業生,形成了強大的專業編輯陣容,為高品質出版物的翻譯、編輯、校對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此后,其他出版機構也逐漸重視引進專業人才,促進了我國出版業的大發展。
(四)著作權保護被納入法律
我國古代作者和出版機構的著作權沒有得到完善的法律保護,雖然不少書印有“版權所有,翻印(刻)必究”字樣,但是,流通性較好的圖書基本上都存在被他人或其他機構刻印情況。近代以來,教會出版機構開始注重版權保護,較早接觸西學的知識分子也顯現出著作權保護意識。1903年,嚴復翻譯了愛德華·甄克斯的《社會通詮》,在與商務印書館簽訂的出版合同中第一次從法律意義上明確了作者與出版機構的權利和義務,在我國著作權保護史上具有一定意義。1906年,清政府頒布了《大清印刷物專律》,開啟了我國保護出版物的法律先河。1910年,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的版權法《大清著作權律》,雖然該律頒布不久后清政府就滅亡了,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但為我國版權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15年,北洋政府頒布了《著作權法》,1916年又頒布了《著作權法注冊程序及規費施行細則》,對《著作權法》進行補充和細化。1928年,《中華民國著作權法》頒布,該法在《大清著作權律》的基礎上進行了修訂和完善,成為我國現代著作權法的重要代表之一。1930年,《中華民國著作權法施行細則》頒布,對《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的各項規定進行了細化和解釋,是著作權法實施的重要保障。1944年,《修正著作權法案》頒布,旨在保護視聽作品的著作權。以上法律構成了晚清民國時期著作權法的主要框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著作權保護逐漸走上正軌。
(五)為作者發放稿酬
近代以來,我國報刊業和圖書業的稿酬制度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早期報紙刊發作者的文章,作者是要向報館付費的;到了19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免費為作者刊登稿件的現象;1884年,《點石齋畫報》公開征集圖畫,給能夠入選刊登的作品每幅兩元的“酬筆”,這是近代報刊界首次給作者支付稿酬,也是我國稿酬制度的開始。1902年11月,梁啟超創辦我國第一份近代小說雜志《新小說》,此前半個月,先在《新民叢報》第十九號上刊布《新小說社征文啟》,將來稿分為自著本和譯本兩種,每種分為甲、乙、丙三等“潤格”,共六等,開啟了小說類雜志給作者發放稿酬的先河[4]。其后,《小說林》《小說月報》等雜志及《申報》《新聞報》等報紙開始發放稿酬,越來越多的報刊為作者發放稿酬。稿酬成為許多文人收入的主要來源,一些知名作家依靠優渥的稿酬改善了生活,可謂近現代出版業繁榮的一個重要側面。
二、在繼承優良傳統中進行創新的路徑探索
我國出版業是一種傳統文化產業。當前出版技術更新迭代快、讀者品味多元化,因此,在守住傳統出版陣地的同時,要適應新的社會形勢,煥發新的生機,進行高質量發展。如何在繼承出版業的優良傳統中進行創新,本文認為要把握以下方面:
(一)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敏銳的判斷力找準選題、做精內容
我國近代出版工作者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將出版物當作“武器”,推動了革命進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將出版行業納入宣傳事業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出版的目的就是給全社會輸送精神文化產品,因此,出版工作者要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堅持正確的出版導向,堅持“內容為王”,在選題和內容上真正下功夫,在繼承中創新。
當前,主題出版是各出版單位的工作重點,往往圍繞重大活動、重大事件、重要時間節點等展開策劃,客觀上容易出現熱點過于集中等問題。為了有效避免主題出版類選題過于集中、內容同質化的現象,出版工作者要不斷提高判斷力和敏銳度,選好切入角度,找準書寫對象,進而把內容做精。
(二)尊重作者,深入挖掘作者潛力
在我國近現代出版史上,編輯與作者良性互動的例子非常多,老一代出版人為我們樹立了好榜樣。例如,出版家范用先生與作者之間的互動就被傳為佳話。范用先生離休后,從2005年開始編輯整理他與作者、朋友之間的通信,選取了兩千多封內容優質的信件,編輯成書,取名《存牘輯覽》。“這些入選信件里披露了《傅雷家書》的來龍去脈,《讀書》雜志的光彩與坎坷,《珠還記幸》題目的來由;保留了《隨想錄》《懶尋舊夢錄》《干校六記》《云夢斷憶》《鄭超麟回憶錄》《一氓題跋》《聶紺弩雜文集》《編輯憶舊》《讀書隨筆》《語文閑談》《北京乎》……一大批書背后有趣或曲折的故事……是文化史、出版史的一個側面縮影。”[5]尊重作者,充分挖掘作者的個人經歷、創作成果,能夠幫助編輯找到好選題、造就好書。各領域的學術大家,不僅學術作品引人注目,其人生經歷與人際交往也非常豐富,他們的回憶錄、口述作品、傳記等往往也是優質的出版素材。因此,出版工作者要充分尊重作者,根據每個作者的思想與經歷中的閃光點,找到其可塑之處,進而可能挖掘出意想不到的優質選題。現在不少圖書編輯喜歡坐在辦公室里等作者來稿。事實上,一些作者來稿可能存在諸如結構不合理、內容有缺陷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可能源于作者在寫作之前沒有思考清楚,也沒有事先與圖書編輯溝通過。如果編輯在作者寫作之前就參與圖書的策劃工作,幫忙審讀書稿框架、把關主要內容,幫助作者規避一些潛在的問題,那么作者會少做“無用功”,節省時間精力,更充分地釋放出自己在相關領域的潛力,寫出更加優質的書稿。
(三)履職盡責,樹立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
出版是一個細致的工作,出版從業者投入多少時間精力,其結果往往不一樣。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才更有可能出版精品圖書。例如,人民出版社曾經出了兩代“校對王”。第一代是白以坦,他校對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鄧小平文選》等重要著作,憑借出版校對事業的出色成就,榮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稱號。第二代是吳海平,他為《鄧小平文選》《惲代英全集》等重要圖書糾錯。吳海平曾說,出版工作“你花不花物力、人工,裁量權其實在自己,憑的是良心。”踐行工匠精神,既是出版工作的內在要求,也是出版事業精神傳承的一種表現。因此,出版工作者要以嚴謹細致的工作風格,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才有可能打造出能夠傳世的優秀圖書。
(四)傳承出版品牌的優勢,守好出版基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6]一部作品要成為無愧于時代的偉大作品,不僅需要作者篤定恒心、傾注心血,又需要出版者慧眼識珠、傳承創新。近代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出版一大批流傳后世的優秀作品,與一代又一代作者的矢志不渝、上下求索有關,也與一代又一代出版人不斷深耕、形成品牌的深厚積淀分不開。從出版角度來看,我國擁有傳承百年的“老店”,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也有黨的宣傳事業的光榮傳承者和守護者,例如,人民出版社及各地方人民出版社。從類型上來說,擁有社科類、科技類、教育類、少兒類、文藝類、美術類、古籍類、大學類以及各部委直屬的各種專業類出版社。每一家出版單位都有自己的專業分工和出版特長,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出版品牌。傳承并發展好這些優秀的出版品牌,是當代出版工作者守正創新的重要根基。
三、結 語
當今的出版工作者,在傳承好優秀出版歷史文化傳統的同時,要不斷探索出版的多種形式,如有聲書、電子書、多媒體出版物等,也可以進行跨界合作,與電影、電視、游戲等多個產業合作,以各種創新型出版物及文化衍生品滿足讀者的多元需求。出版物具有較高社會價值和文化內涵才是受讀者追捧的關鍵所在,因此,出版工作者要在提高出版物的水平上多下功夫。
出版是人類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出版物是文化的具體表征。作為新時代的出版者,我們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深刻理解“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沿著出版前輩開拓的事業繼續向前走,在守正中創新,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實現出版業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 郝振省主編.中國近代編輯出版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
[3] 穆欣.鄒韜奮[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
[4] 郭浩帆.近代稿酬略談[J].文史知識,2000(11).
[5] 汪家明.范用:為書籍的一生[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
[6]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李慕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