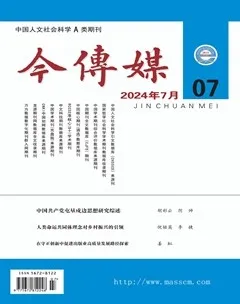無名處有“聲”——《無名》聲音設計分析
摘 要:“超級商業片”《無名》在聲音的氛圍營造、聲音敘事和聲音景觀的構建上呈現出強烈的類型片風格,以建立復雜的語言環境和設計別具巧思的聲畫沖突來沖破類型之藩籬,留下導演獨特的個人美學印記。本文以電影聲音為研究方向,結合工業聲音制作與觀眾聲音感知的視角,從“類型之聲”與“作者之聲”兩個角度對電影《無名》中的聲音設計進行深入解讀,旨在探尋這部商業與藝術共謀、鮮血與詩意共融的電影的聲音魅力。
關鍵詞:《無名》;聲音設計;作者電影
中圖分類號:J9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4)07-0088-04
一、引 言
2023年,電影《無名》帶著“超級商業片”[1]的標簽進入春節電影市場,以其諜戰懸疑的題材與獨特的美學風格,不僅展現了對革命先輩的崇敬與謳歌,還呈現出導演程耳浪漫、獨特的“作者腔調”,體現了藝術與商業融合的自覺實踐。因此,本文聚焦《無名》的聲音設計,解讀電影聲音中的“商業面向”與“作者立場”;基于電影聲音的多義性和復雜性,使用音樂分析方式解析該電影音樂的內部構造;從工業聲音制作和觀眾聲音感知的視角,探究該電影聲音制作技術以及聲音對觀眾心理感知的引導方式。
二、“類型”的聲音
(一)聲音的氛圍營造
1.聲音作為符號帶來危機感和懸念
電影聲音具有典型的符號特征,既能參與表層的故事敘事,又能言說深層的人物情感與故事內涵。《無名》作為一部諜戰懸疑類影片,“危險”和“懸疑”是電影氣氛渲染的核心,因此,一些約定俗成的聲音符號被放置于特定場面中,起到烘托和暗示的作用。
《無名》中出現了大量的雨聲與雷聲音效,這些通過“后期音效制作(SFXRecordist)”處理的聲音被設置在各類危機場面中。一方面,雜亂的雨聲配合沉重的悶雷聲,聽感壓抑,能使觀眾產生焦躁、不安甚至恐懼的情緒。導演將廣州被日軍轟炸、葉先生與日本兵互毆、方小姐被王隊長跟蹤并殺害等情節設置在雷雨天,以暗示未知但極為危險的結果。雷雨聲的加入為電影構建了更為逼真的險境,快節奏的雨聲襯托出打斗的酣暢淋漓,進一步引導觀眾感知人物所處的危急處境。另一方面,諜戰片中的懸念制造通常呈現出不斷累加、量化的趨勢,持續出現的大雨聲與悶雷聲為后續驚險的情節埋下伏筆。當方小姐在夜晚被王隊長跟蹤時,雷雨聲暗示了方小姐即將因身份暴露而慘遭不幸;當日軍高層在雷雨天接到公爵死亡的消息時,一陣悶雷聲緊接剛落的話音響起,暗示接下來的血雨腥風;“珍珠港事件”發生后,日軍行走在瓢潑大雨中,悶雷聲再次出現,暗示日本即將兵敗。“雷雨聲”作為一個危險符號貫穿電影始終,渲染與暗示各類危機情節。
2.聲音營造神秘懸疑的氛圍
為配合“懸念”氛圍的渲染,電影常常通過特殊的音樂設計引起觀眾“緊張”“不安”“恐懼”的心理感知。《無名》中,在何主任身份暴露后的飯局上,五位分屬三個不同陣營、各自間存在不同敵友關系的角色,以笑意掩飾內心的不安與殺意,可謂“訣別一餐”。起初,五人口蜜腹劍地相互試探,此時導演選擇了一首旋律、音域都在線譜中低聲部的曲子,曲子開端采用銅管類樂器的極低聲部配合同音反復的旋律線,引導觀眾進入一種低沉、懸疑的氛圍中。隨后,伴隨唐部長的一聲“表哥”以及王隊長對葉先生的坦白,一切有關身份與真相的掩飾在片刻間被擊碎,五人之間正式“兵戎相見”,此時伴奏中的低音提琴伴隨鼓聲進入并成為主奏,低聲部采用分解和弦式織體,以不協和音程關系的旋律進行,音樂如一張黑暗的網籠罩著整個場景,與文本內容相呼應,給觀眾帶來不安、恐懼的感受,渲染出暗流涌動的懸疑氣氛。
此外,電影還會為典型空間設計特定的聲音,來烘托特殊的環境氛圍。諜戰懸疑電影中經常出現代表反派勢力權力中心的場所,比如,在《無名》中一座黑暗幽閉的建筑是汪偽政府的“辦事中心”,監牢、詢問室、惡犬籠等危險符號充斥于這個環境中。該空間內的對話聲、犬吠聲、腳步聲都經過混音處理,總體呈現出低頻較重、混響時間較長、混響量較大、直混較小的聲音特點,而聲音信號又在房間特有的聲學環境中產生反射聲,形成空蕩的空間回響,使觀眾對聲源所在空間產生四壁蕭然、神秘陰森的主觀印象。
(二)聲音的敘事
1.聽點敘事
學者詹姆斯·拉斯特拉在《閱讀、寫作和表現聲音》中提出了“聽點”的理論概念,認為“主觀聽點(Pointofaudition)”就像主觀視點一樣,代表一種劇情中的體驗,通常表示某個角色的聽覺感受”[2]。目前,大部分電影聲音都是以主客觀聽點結合的形式出現,在聽點轉換的輔助下,視覺畫面的引導作用增強,產生更好的戲劇效果。聽點轉換還能參與敘事,在推動劇情發展的同時,有效營造故事所需的情調氛圍。在《無名》開頭,洪亮的電話鈴聲打破了葉先生與王隊長輕松的聊天氛圍,隨后鈴聲伴隨著畫面由車內轉向海邊,最終畫面再切回到電話所在的空間,同一條聲音信息連接三組鏡頭、三個場景,不同角色的聽點轉換讓聲音直接參與了魔方化敘事。電話鈴聲也闡釋了葉先生與王隊長坐車去往何處、兩人又為何會出現于海灘之上,以“日本公爵遇刺”一事連接起三個不同時空的片段,整體上用聽點組接、解釋鏡頭,既敘事又傳情。
而在廣州被日軍轟炸的劇情中,聽點轉換帶來的敘事力量更為明顯。最初,日本飛行員收聽的天氣情況與午餐信息是主觀聽點,傳遞出安逸愜意的氣氛;隨后,鏡頭切到地面廢墟中的流浪狗(代表無法進入防空洞的難民),聽點也隨之切換到流浪狗所聽到的清晰的防空警報聲;最后,蜷縮在防空洞中的人們在鏡頭中出現,聲場與聽感發生變化,聽點又切換為防空洞內難民的主觀聽點,警報聲變得悠遠而渾濁。從技術角度看,這種聲音效果是通過后期聲音制作時拉低音量,并對混響和聲反射進行控制達到的,契合防空洞中的聲學特性。三組聽點轉換以簡潔高效的轉場方式呈現了事件的進展,成為敘事的引導因素,展現出廣州城內三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狀況,構成了鮮明的對比蒙太奇,也使觀眾感受到強烈的悲憫與諷刺。
2.聲音的景觀與主導動機構建
聲音景觀由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組合而成,前者以自然音響為主,后者以人類社會中各類人造音響為主。特定的場景音響能強調聲音景觀的特點,并通過建立場景主導動機的方式賦予該景觀獨特的氣質。《無名》的聲音制作團隊將固定聲音放置于固定場景,以聲音構建起不同空間的景觀樣式與主導動機。
環境聲是形成場景氣氛并定位其空間位置的聲音,也稱為地域聲,它們的連續性能夠幫助我們識別一個具體的場所[3]。“和室”是日本傳統的室內空間,其作為用餐場所多次出現在電影中,并且每次出現都伴隨著日本藝伎演唱的和歌,隱喻該場所處于日方力量控制之下。隨著聲音與畫面以某種固定搭配連續多次出現,和歌成為和室鮮明的音樂標簽,形成了主導動機,成為影片中和室場景即將出現的音響信號,各方勢力在和室中的暗自角逐也將在觀眾的預料中如期上演。
《無名》中伴隨上海這座城市出現的背景音樂來自一家舞廳,舞廳內的交響樂由大提琴伴奏,小提琴主奏。在大提琴的低音伴奏下,小提琴以C大調與四分之三拍的節奏型為基礎,配合連弓與跳弓的手法,演奏出輕快的旋律,展現出舞廳優雅、安逸的聲音景觀。該段音樂也出現在展示上海城市風景的空鏡頭中,導演通過以小見大的手法,以一個小舞廳的聲音景觀隱喻上海這座“孤島”因外國勢力盤踞而免于戰火、偏安一隅的城市現狀。“風平浪靜”的上海便于地下黨員掩飾身份,人員身份復雜的舞廳是地下黨員刺殺敵人的絕佳場所,每一次舞廳畫面都與上述弦樂捆綁出現,場景的主導動機不斷得到強化,使觀眾能迅速、準確地識別該場所并沉浸在舞廳特殊的氛圍之中。
三、“作者”的聲音
若程耳導演七年前執導的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像一壇好酒,越放越香,那《無名》則如暢銷飲品般“開蓋即飲”[4]。在如今的主流電影市場中,“商業性”受到追捧。面對競爭激烈的春節檔,《無名》不僅在宣發階段就貼上了“超級商業片”的特殊標簽,眾多商業元素也被添置到劇本中。雖然《無名》呈現出明顯的商業傾向,但其中的聲音設計卻以“作者”之聲呈現出鮮明的個人風格,顯示出導演對于自身風格的堅守以及通過獨特風格沖破類型桎梏的自覺實踐。
(一)“他/她”者之聲
1.方言的使用
《無名》的導演在采訪中提出,“方言是一個城市的魂魄,是我們不應該去放棄的東西,我們盡可能讓戲中人都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去說話,因為生活中我們就是這樣的”[5]。《無名》延續了《羅曼蒂克消亡史》大篇幅使用上海方言的特點,這與導演在上海多年的居住經歷直接相關,使用上海方言是其電影中鮮明的“作者元素”。電影開場就是使用上海話的人物對白,在開頭幾秒內就交代了故事的發生地———上海,而后續上海方言的大量使用逐漸構建起上海的人文景觀,增加了在地性與真實感。
方言能為陌生雙方建立起對話空間,推動故事進展。在影片結尾,當葉先生來到王隊長家人在香港經營的餐館時,起初雙方僅僅是顧客與店家的陌生關系,而當葉先生用上海方言說了“謝謝”后,王隊長的母親立刻流露出遇見同鄉的欣喜,兩人的對話隨之開啟。方言成為幾位同鄉在異地他鄉相識的紐帶,不僅開啟了雙方的對話空間,也聯系起二人事關血債的復雜關系,狹窄空間內充斥著巨大的情感張力。觀眾可以解讀出王隊長母親對兒子的思念,葉先生對過去恩怨搖擺不定的糾結以及逐漸釋懷、選擇放下的善意。除此之外,導演還在電影中加入廣東方言、普通話和日語,豐富了語言種類,高度契合當時上海多方勢力盤根交錯的真實情況,合理而不突兀。
2.復雜語言環境下的身份構建
在《無名》中,各位主演被要求根據角色身份背景使用相應的語言語種,以此定位角色的陣營。其中,隸屬汪偽政府、國民黨的人物大部分使用上海方言,例如王隊長、江小姐與前期的葉先生,這符合當時汪偽政府在上海培養了大量當地特工的史實,也隱喻著這些勢力僅僅達到地方規模;日本軍人使用日語對白;身為共產黨員的何主任、陳小姐、方小姐、后期的葉先生等人物則采用普通話對白,作為我國通用現代標準漢語的普通話也隱喻著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三方陣營通過不同的語種對白,以直觀的聽覺感受被有效區分,形成了獨有的聲音形象,并以對白建構起人物的主導動機。當不同陣營的人物進行對話時,二至三種語種的復雜語言環境也增強了身份感與真實感。
電影中葉先生在不同情節先后使用了上海話、日語、普通話,安排同一人物在有限時間內使用多種語言是較為冒險的決定,不僅讓演員本身產生負擔,也容易造成觀眾聽感的混亂。然而,葉先生極度復雜的政治身份恰好為多語種對白的運用提供了合理性,他的語言始終伴隨著身份進行轉換。起初,作為汪偽政府爪牙的葉先生,使用汪偽政府的聲音標簽———上海方言;隨著他取代何主任成為臥底于日本軍官身邊的“一把手”,開始用日語和日本軍官對話;而在與何主任秘密交流的情節中,兩人使用普通話,此時的觀眾才了解了葉先生的真實身份———共產黨員。因此,葉先生使用三種語言的設定并沒有帶來聽感的混亂,而是符合劇情的“神來之筆”。
(二)“它”者之聲
在《無名》中,部分特定場景內出現了動物的特寫鏡頭。在貼合劇情表達特殊視覺效果的同時,動物的“它”者之聲常被用來隱晦地傳達某種內涵。電影前中段,當日軍殘暴地坑殺無辜勞工時,影片情緒在音畫的共同渲染下顯得非常沉重。通常導演會在低沉的情節后選擇轉場至其他平淡段落,以此安撫觀眾情緒、控制電影節奏,但在《無名》中,導演選擇銜接一個日軍的主觀鏡頭———一只勞工養的小羊在門外叫了一聲,潔白的它站在光明之中無辜、純潔,給觀眾以救贖的希望。正當觀眾以為悲傷的氣氛即將消散時,殘忍的鏡頭在下一秒出現———一鍋滿滿當當的白煮羊肉正被日本士兵蠶食,其中一人甚至說道:“在來中國前,我從沒吃過羊肉。”更為直白諷刺的悲傷再次向觀眾涌來。小羊在鏡頭中的叫聲響亮卻無力,日本士兵從前沒吃過羊肉的言論暗指日本因物資匱乏而發動侵華戰爭,羊的叫聲代表著勞工們的吶喊,代表著當時中國百姓的吶喊,他們因極度的痛恨而選擇放聲對抗。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戰爭中民族獨立最堅定的維護者,真正傾聽到了群眾的聲音,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種種暴行,始終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進行堅決有力的斗爭。
(三)聲畫沖突下的“詩意”
電影開頭處,滿臉鮮血的葉先生將刀拼命地刺向敵人,畫面傳遞出血腥與暴力,這個鏡頭穿插在上海城市風景、何主任走入辦公室以及上海舞廳場景的片段中,與悠緩的弦樂形成對比,構建出一種“優雅的暴力”,將殘酷與詩意交融,營造出獨特的美學氣質。當何主任身著西裝坐在老式汽車中決定放走江小姐時,江小姐一襲紅衣站在錯落有致、昏暗陰郁的蘆葦蕩內,畫面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江小姐的哭泣、何主任的痛苦神情都傳達出悲涼之感,此時的江小姐失去了人生方向,失去了堅定意志。觀眾并不能絕對確定江小姐究竟是帶著赤誠之心回歸,還是帶著悔恨離開。低落、悲傷的畫面配以宏大、磅礴的背景音樂,昂揚的女高音在使用四度音程、連續上行的級進型交響樂伴奏下吟唱,產生了強烈的聲畫沖突。
四、結 語
1908年,卡米亞·圣桑為電影《吉斯公爵的被刺》進行專屬配樂,開啟了專業電影配樂之濫觴。百年后的今日,電影配樂已發展為一門多元化的藝術,能夠根據導演的商業傾向或個人風格進行“特殊定制”。《無名》作為一首時代下的個人史詩與一部動蕩時光中的群像紀錄,沉重卻有力,殘酷卻優雅。我們能夠從電影的聲音設計中窺探導演對于商業的考量和對“作者特性”的堅守,感受到他對商業、藝術如何平衡的自覺探索。
參考文獻:
[1] 徐鵬遠.《無名》導演程耳:真正的好電影一定比商業更商業、比藝術更藝術[EB/OL].https://www. inewsweek.cn/life/2023-01-28/17457.shtml,2023-01-28.
[2] RickAltman.Soundtheory,soundpractice[M]. NewYork:Routledge,1992.
[3] 米歇爾·希翁.視聽:幻覺的構建[M].黃英俠,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64-93.
[4][5] 劉珞琦,白晨.導演程耳:“《無名》開蓋即飲”[EB/OL].https://www.sohu.com/a/634425009_388075,2023-01-25.
[責任編輯:喻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