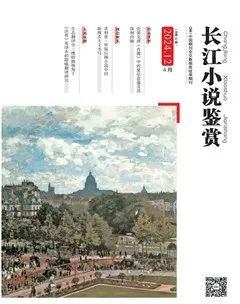“困境”與“流散”
[摘" 要] 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作為現當代加拿大小說家,敘事多以其故鄉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布雷頓角為背景,其代表作小說集《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敘寫了當地蘇格蘭移民后裔在現代文明沖擊之下,在社會中不斷被邊緣化的身份困境。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在小說敘事過程中格外強調對于布雷頓角中心失群人在工業文明社會中的關懷,展現了布雷頓角居民的“流散”現狀,呼喚布雷頓角的青少年們回歸族裔群體,從而保護當地文化不被侵蝕,進而進行獨立敘事。本文從后殖民主義視角出發,探討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在《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一書中的敘寫所呈現的不同流散人群的困境,發掘邊緣人群的焦慮并分析其根源,批判主流社會對于少數族裔的歧視態度,喚醒更多人對于社會邊緣群體的關注。
[關鍵詞] 遲子建" 《踏著月光的行板》" 人性之美" 平凡的生活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12-0014-06
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Alistair MacLeod)是在后殖民語境下進行文學創作的典型代表,他用細膩的語言書寫加拿大布雷頓角本土不同代際的人群在話語權缺位下產生的身份焦慮。其短篇小說集《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The Lost Salt Gift of Blood in the Wind)和長篇小說《布雷頓角的嘆息》(No Great Mischief)都貫徹了對“身份焦慮”的敘述。
國內對于麥克勞德的研究始于2013年,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張陟教授在論文《海邊的風笛手——阿·麥克勞德的短篇小說創作簡評》中針對麥克勞德成長背景對其作品書寫風格的影響,以作品中青年男性形象為切入點,分析故事情節中反映的現代化大潮沖擊下傳統價值與生活方式的失落與傳承,把矛盾設定為城市和鄉村的沖突、現代文明和家族傳統的沖突,闡釋了該矛盾的根源為加拿大社會階層的變化。泰山學院馬秀華在其論文《人類生存異化的關注者——加拿大作家麥克勞德的作品解讀》中也強調了現代社會工業文明給傳統漁村帶來的沖擊,指出急速發展的工業文明之下加拿大諸如布雷頓角小村莊年輕人產生的一味追求大城市生活,渴望擺脫落后傳統的生活方式的病態心理及身份的焦慮,強調麥克勞德的作品是對這一現象的反思。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編輯王冠珠所撰論文《來自布雷頓角的生命回響——記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與浙江省作家協會文學院黃詠梅的閱讀對談《面對“平地的艱難”——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lt;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gt;閱讀對談》更多講述了麥克勞德的生平和作品的文學特色及抒情性。
國外自20世紀末21世紀初就有對于麥克勞德作品的研究,20世紀末相關研究大多是關于麥克勞德寫作風格藝術性與文學性的探究,以及作品中文學意象的書寫。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圣弗朗西斯-澤維爾大學學者James O. Taylor于1994年在論文Art Imagery and Destiny in Alistair MacLeod’s Fiction中就著重研究了其作品中冬犬的意象,闡釋了麥克勞德寫作中的抒情性對家鄉布雷頓角樸素的刻畫。Sharon Selby在英國利物浦大學英加研究期刊上發表的論文More than Representation: Storytelling and Self-Invention in Alistair MacLeod’s Narratives中分析研究了麥克勞德在作品中以第一人稱視角展現的個人對自我的認識和凝視,反映了自我意識在角色個人成長過程中的轉變。以上兩篇論文是對麥克勞德情節與角色分析的典型代表。涉及麥克勞德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社會現象及原因分析的論文有Peter Thompson的‘If you’re in quest of the Folk, you’ve come to the wrong place’: Recent Trends in Atlantic Canadian Literary Criticism。作者發掘了作品中主角所代表的蘇格蘭移民后代所屬的傳統文化被邊緣化的現象,闡述了加拿大中產階級出于商業目的浸淫的當地文化。Thompson指出了麥克勞德與眾多加拿大中心城市作家的不同之處——對貧窮社會中被邊緣化文化的書寫,點明了消費社會對傳統漁村家庭觀念的沖擊,明確指出了當代眾多加拿大作家對于現代社會敘述的欠缺。Thompson提倡用后殖民理論來理解加拿大非中心城市鄉村的人與社會和歷史、空間、加拿大其他地區以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的關系。Virginia Scott的論文Review Essay: Eastern Mosaic: A Review on the Culture of the Maritimus也提及了Peter Thompson所涉及的傳統文化邊緣化的現象。
國內外對麥克勞德的研究多從其作品藝術性出發,關注作品中社會邊緣化人群無法融入現代社會的困境,將原因歸結為工業文明對傳統文明的破壞。但是這些研究忽略了加拿大蘇格蘭后裔的身份特征,未從角色身份焦慮的角度進行重點研究,也缺乏對后殖民語境的分析。國內外對后殖民文學的研究大多也是從黑人、亞裔、拉丁美裔的角度切入,沒有關注到社會中“窮白人”面臨的困境。因此本文將結合后殖民文學評論家薩義德、霍米巴巴等人的理論,分別從《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中不同代際的布雷頓角人探討其中反映的身份焦慮并分析其成因,從后殖民語境切入探索當今世界邊緣人群文化敘述的困境,探究加拿大文學中對后殖民文化的描寫,拓展對于后殖民文化的理解,延伸麥克勞德作品的現實意義。
一、身份與“困境”敘述——蘇格蘭移民后裔無法融入白人主流群體
小說集的背景布雷頓角是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東部的一座小島,與大陸之間隔著一條坎索海峽,蘇格蘭人于19世紀初移民至此,由于四圍環湖環海,島上也有豐富的礦藏資源,島上居民多以采礦與捕魚為業。獨特的地理條件將布雷頓角同加拿大大陸中心城市隔離開來,而當地居民所從事的生產活動近百年來變化微乎其微,致使其與現代信息社會存在著一定的隔閡。天然環境與社會經濟共同影響下島上蘇格蘭移民者后裔,無論是較為年長的父輩,還是外出謀生的子輩在離開小島抑或是接受到現代文明沖擊的情況下便出現了無法融入白人主流群體的困境,而浸潤在主流話語與現代文明下的孫輩則面臨著與長輩文化背景的割離。《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涉及了不同年齡段的人群面對的困境。
1.父輩——移民后裔漁獵采礦為生,無法跟進工業社會
《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中的父輩大多是指出生于20世紀初,廣泛從事移民者初期工作方式,如采礦捕魚,較好地保有蘇格蘭習俗與蓋爾族民族特征。但也正是因為這群居民保留了較為淳樸簡單的生活方式,在20世紀工業文明迅速發展的情況下,父輩居民不可避免與現代高速發展的社會脫節。小說集中比較典型的對于父輩的描寫集中于《秋》《黑暗茫茫》《船》三篇。
《秋》中父親這一角色原為煤礦工人,但因身體原因無法繼續負荷礦下工作,后以農業種植為主要謀生方式。父親所支持的家庭境況并不樂觀,家中老馬斯科特也至遲暮,為了維系家庭經濟狀況,父親決定賣馬。但是父親對馬心存不舍,然而粗俗的家畜商人麥克雷反復催促呵斥,毫不在乎這種鄉野村莊中的人與動物的感情,一切從商業文明的利益導向出發,凌駕于父親的情緒之上。在小說結尾,父親乃至全家人仍舊需要為了生計發愁,前景迷茫,工業文明不僅擠壓了農業文明的生存空間,樸素真摯的情感也遭到傾軋,父親在這里從經濟層面與情感層面都與工業社會脫節。
《黑暗茫茫》中對于父親和祖父的敘述都符合父輩形象敘寫。父親常年在礦下工作,右手手指有缺,右臉有鉆頭失靈留下的疤,因為常年呼吸煤礦中惡劣的氣體,經常咳嗽大聲喘息。父親就是傳承祖父煤礦工人的身份繼續從事這樣一份工作,如文章所寫,“從1837年開始干煤礦一直干到現在”。祖父也留存下了諸多明信片和工資單,明信片大多為祖父在不同礦上工作留下的紀念品和其他煤礦工人的問候。對于小說中“我”即較為年輕、不愿繼續從事礦業工作的青年的叛逆和渴望擺脫當下生活現狀的心理存在著不理解,但是父親和祖父并不獨斷專橫,也并不會以自身的世界觀來束縛“我”的自由生長,因此父親與祖父其實理解“我”想要自己外出求生、追求自由的心理。但他們也指出了家鄉的影子永遠都會跟著這片土地上的人,不是能夠輕易擺脫掉的,這既包含著對于自身身份的認可與自豪,也有對于年輕一輩的警告和勸誡,他們沒有迫切想要融入主流白人社會的欲望與需求,足夠認可自身族裔文化,但是不免遭到年輕一代思想和行為上的挑戰,這也是麥克勞德在敘事時融入的沖突點。
《船》中的父親是霍克斯伯里港的漁民,一生都在海上作業,但父親本身對于捕魚這一行業并非熱愛,而是出于家庭的責任以及家族的傳承。父親愛好讀書,家中房間陳列著各類文學著作,而他沉靜如海的性格與這種接受知識熏陶之后的內涵使很多登上他游船的旅客都對他的性格抱有高度的贊美,文中就有旅客尊敬又幽默地稱父親為“歐內斯特·海明威”。但是父親對于這樣的稱贊并沒有過多的關注,對于現代文明加諸于身的“凝視”,父親泰然處之,繼續著他的捕魚工作生活,但是最后因為出海遭遇風暴,身體在遭到海浪席卷又撞擊到海巖的情況下變得殘缺不堪。
《船》中的父親并非典型的父輩形象,他有一定的知識,也有風度與談吐,愛好文學,并非如同《秋》《黑暗茫茫》兩篇中近乎文盲的父輩,但是他們在自己的行業任勞任怨都是相同的,但無論他們是否接受過教育,因為生產方式或固有觀念的束縛并不能夠被人理解乃至融入主流社會。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他們的家鄉淪為白人主流社會的殖民地,父輩一群人淪為被殖民者,在工業文明的裹挾下,面對固有文化與民族特征、身份特征被瓦解,他們的存在便是對這種殖民化的反抗,但是反抗也不甚理想,他們也只得無力地面對后代欣然地接受白人主流文化的殖民,在有生之年見證著族裔特征的溶解和身份認同的顛覆。
2.子輩——漁民礦工后代離鄉熱潮,爬升至中產后與城鄉社會的兩面隔閡
《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中對于子輩人物的設定多為一戰到二戰期間出生,部分接受過一定教育,受到現代工業文明影響較大,為后殖民主要殖民對象。其特征表現為對族裔長期以來生產方式和文化的不認同,甚至到了一種排斥、遠離的狀態。子輩人群多向往城市生活,甘愿拋棄自己原本的文化身份,但是最終往往面臨著既不被白人主流人群接受,也無法融入主流文化語境,從而不得不回歸到故鄉,重新認識族裔文化特征。麥克勞德對于子輩的書寫較為典型的為《黑暗茫茫》《回鄉》《去亂岑角的路》這三篇文章。
《黑暗茫茫》中的主人公渴望擺脫祖祖輩輩都在礦上工作的命運,“我”是家中長子,但也沒有受到父母亦或是祖父母分配的責任的約束,生長環境較為自由,因而“我”的自身性格塑造源于“我”的文化背景與接受的教育。在文化與教育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面臨著繼承還是打破文化傳統與身份特征的選擇。“我”首先是選擇了后者,一味想要逃離,辭別親人后毅然搭上車,心中的目的地永遠是“溫哥華”這樣的大城市,但是實際上“我”對于溫哥華的地理位置都不甚了解。沿途又遇到和故鄉相似的村莊,當“我”作為一種旁觀者,而非參與者,來看待自身族裔文化以及相似的文化時,“我”的心靈突然受到沖擊,原來自身身份背后的文化牽絆是這樣重。在“我”將旅程中所見所聞與自己過往的記憶聯系起來后,作為向往中的新世界的燈塔“溫哥華”在“我”心中便不復存在了。本篇的主人公展現了布雷頓角子輩抱有向中產階級靠攏的想法,并且進行了一些簡單的嘗試,最終對現代社會呈現出一種畏懼的態度。
《回鄉》敘述了已經從經濟層面上爬升至中產階級的子輩人物。安格斯出生于布雷頓角,接受過高等教育,學習法律成為律師,與蒙特利爾法官的女兒結婚。但是《回鄉》并沒有對安格斯爬升至中產階級這一過程過多著墨,而是把大部分的篇幅都放在安格斯和他的妻兒共同回鄉的一段經歷上,安格斯代表的離開家鄉、背離文化身份的子輩介于安格斯妻子瑪麗與兒子阿萊克斯所代表的工業社會中居于城市的主流白人群體和安格斯父輩礦工所代表的原始族裔之間,于是安格斯這個介于中間的角色在文中常常有著和兩方的疏離感,從他的妻子瑪麗對他的態度可見,安格斯并未完全融入瑪麗所屬的群體,于是在潛移默化之中淪為被殖民者。當安格斯事業有成、家庭美滿時,又對故鄉心存留念,這樣一份留念來得有些遲,對他的兒子也講不出故鄉文化風俗的所以然,此時的安格斯也明顯不再屬于布雷頓角的族群了。“隔閡”就是安格斯這類人面對的困境,這也是后殖民主義影響下許多在城市追求更高社會地位的窮人面臨的困境。
《去亂岑角的路》一篇中的卡倫幾乎是從城市逃離到鄉村,因為城市工業文明節奏過快壓力過大,在這樣一種人人都在爭取更大利益的潮流下,卡倫身體跟不上節奏,得了絕癥,內心也對這樣的價值取向產生了懷疑與厭惡,于是回到亂岑角找到了一直都住在未曾拆遷的老房子里的奶奶。卡倫這一形象直接呈現了現代文明對人的異化,卡倫曾經試圖融入,但是結果是自己不堪重負,如果將融入白人的主流社會作為目標和價值取向,卡倫無疑是一個失敗的例子。但是就卡倫最后回歸到故鄉,和溫和慈祥的奶奶對話,親近自然,從抵抗后殖民文化入侵方面來講,他無疑是成功的。
《黑暗茫茫》中的我、《回鄉》中的安格斯、《去亂岑角的路》中的海倫分別代表著嘗試融入主流社會未果、成功融入主流社會、嘗試融入主流社會但是最終選擇背離主流話語的三類人,都從各自的視角呈現出了后殖民主義文化思想對個人乃至整個父輩群體的影響,讓人產生少數族裔何去何從、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如何構建的疑問。于是麥克勞德又著筆于孫輩,敘寫青少年在面對文化失語困境下的反應。
3.孫輩——中產后代與父輩族裔背景的疏離感
本書中孫輩人物設定多為二戰后出生,成長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他們親身經歷著科技的革新、城市的進一步擴張。此時白人主流話語權已經將一些少數族裔的文明侵蝕殆盡,而他們這些孫輩與子輩比起來,和父輩的關系更為疏遠。麥克勞德對于孫輩的書寫較為典型的有《回鄉》《去亂岑角的路》兩篇。
《回鄉》不僅著眼于對于父輩的描寫,同時還從孫輩的視角入手。阿萊克斯來到布雷頓角后充滿好奇,和礦工的后代一起玩耍,面對祖父與祖母的關懷,阿萊克斯作為一個城市里的孩子也能很快融入眾人的氛圍中,但是其父其母都有意不允許阿萊克斯與當地居民哪怕是和自己有著血緣關系的家屬走得太近,以至于在分別時,祖母說道,在諸多孫輩中,她永遠無法理解的就是阿萊克斯。這是一種父輩對于孫輩逐漸和自身文化身份脫節的無可奈何與無能為力。但這并非阿萊克斯主觀造成的,因為他生長的環境已經鮮見蘇格蘭后裔相關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如果說其父安格斯是后殖民主義之下被殖民的蘇格蘭后裔,那么阿萊克斯就是被殖民者的后代了,他所接觸到的文化已經盡是主流白人文化,于是孫輩與父輩間的隔閡隨著代際更迭只會越來越大,族裔身份特征也就漸漸泯滅。
《去亂岑角的路》一篇中對于孫輩的描寫大多是一筆帶過,但是其中有兩個場景值得一提,一是孫輩在白人上流社會演奏現代樂曲,二是眾多孫輩都來勸他們的奶奶住到城市中,離開鄉野村莊,去養老院頤養天年。他們較子輩更加融入了白人主流社會,也沒有和族裔背景糾纏撕扯的需要,子輩也已為其提供了較為優渥的生存條件,他們也不會產生和子輩那樣奮力掙扎要擺脫的身份焦慮,但也正因此他們與父輩的隔閡越來越深,他們無從理解父輩,對父輩的態度也帶著現代城市文明的冷漠與疏離。
二、移民后裔知識分子與“流散”現實
正是因為蘇格蘭后裔于19世紀中期大部分移民至加拿大北部,仍然保留著一定的民族文化習俗,但是其后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人群廣泛接受了高層次的教育,緊接著大部分都離開家鄉文化環境,去向大城市,最終不可避免地與原生成長環境自主或被迫劃開了界限(生安鋒,2004),這就是后殖民語境中所闡述的“流散”(diaspora)。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從文化上和民族割離,從社會身份上又無法全情融入主流社會,他們游離在兩種文化之間,難以求得共鳴,這樣的境況也是后殖民理論三劍客(愛德華·薩義德,霍米·巴巴,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所面對的。現代文學創作中有后殖民話語書寫,并著重對知識分子流散現實進行呈現的有法國哲學與社會學家迪迪埃·埃里蓬所著的《回歸故里》及加拿大蘇格蘭后裔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的《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前者為非虛構性紀實創作,后者則是作者提煉了自身經歷呈現出的小說。
1.社會施加的身份焦慮使其依附又疏離主流文化語境
移民后裔知識分子因為離鄉來到大城市后總會因為自身經濟階層背景無法完全融入城市中的主流社會——一個以白人精英為主導的社會,在小說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是《回鄉》和《去亂岑角的路》。安格斯和卡倫都為了融入主流社會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從兢兢業業的律師和教師做起,不斷攀升、不斷追求心中虛構的一個未來和一個虛構的“融入者”身份,努力去“依附”,完全打碎了自身的文化特征。但他們哪怕已經在專業水平上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仍然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得到上流社會白人的認可。
兩個角色不同的是:安格斯得到了市法官的垂青,與其女結婚,半只腳踏進了主流社會卻仍然會被議論;卡倫沒有那么幸運,徘徊躊躇,不知前路何在,身患絕癥,對城市生活心灰意冷。主流話語權對于兩個角色都施加了一定程度上的身份焦慮,使得他們不顧一切都要去依附;但是他們的身份背景在后面牽扯著,無法讓他們全情拋開過往接受全然被城市與主流社會馴化的自己。
這樣一種矛盾實際上就使得移民后裔知識分子既依附于主流文化,又與之存在一定的疏離感。
2.“流散”身份使其尋求與族裔身份的聯系
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對于主流社會文化還是存在一定的疏離感,于是安格斯在功成名就、家庭圓滿時想到的是回鄉,要帶妻兒回布雷頓角看看;卡倫在失望過后也是選擇回鄉,并且決定永居家鄉。他們還是將歸屬感的獲得重新寄托在家鄉以及族群上,尋求與族裔身份之間的聯系,并渴求永遠不會和這樣的聯系割裂開來。安格斯的回鄉無疑觸發了其子對布雷頓角的好奇心,卡倫的歸鄉無疑觸發了眾城市中親人對于家鄉老人的關懷。他們寄希望于通過切實的歸鄉來解決“流散”的身份焦慮,但是安格斯最終仍舊需要回到城市工作,卡倫在自己的長輩都去世后與家鄉的聯系不復存在。這樣一個悲劇性的現實使人們不得不思考類似知識分子到底該處于何種身份、具有何種文化地位這一深刻的問題。
3.知識分子在后殖民語境下找到第三空間
在愛德華·薩義德和法儂的理論中,后殖民語境下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完全對立的,也就意味著一個人要么永遠處于自己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的地位,或是由被殖民者同化為殖民者。但是霍米·巴巴則認為在固守和同化之間存在著一個“第三空間(Third space)”,一個介于兩種勢力之間的模棱兩可但又大有可為的探究領域,這個領域并不是指急于將族裔中的“民族意識”轉變為認同度極高的“社會意識”,擺脫殖民后又擺脫民族主義,這個層面太過理想化,也沒有切實可行的方法(趙稀方,2009)。那么只能如霍米·巴巴所說,讓知識分子探索第三空間,在混雜的話語體系中找到對于自身族裔文化的正確解釋,揭穿殖民者的文化入侵方式,讓自身族裔文化成為社會的一部分,不再處于邊緣化地位中。
全書中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就是末篇《去亂岑角的路》中的卡倫,他銘記著長輩留下的故土情思與文化傳統,又勸誡著自己的子輩孫輩切莫在城市中丟掉了自己的來路。這是麥克勞德自身的一個投射,同樣都是教師,同樣都是做著用教育來引導思想的工作,用知識分子的方式在第三空間書寫著自己對于文化的理解,呼喚著外部世界對于少數族群的平等對待。
三、結語
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在《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中用詩意細膩的筆調描繪了蘇格蘭移民后裔三代人的命運。在后殖民語境的敘寫下,他將關切的眼光投射在父輩身上,關懷著邊緣化族裔低收入人群,對他們與自然共處但又不得不受制于自然條件抱有無限同情。
對于背井離鄉、不斷爬升的子輩,他則是戲謔地嘲諷其幼稚的渴望離鄉的執拗心理,批判了完全背離族裔群體的子輩,肯定了最終選擇回歸的人,同時又對中產知識分子抱有期待和鞭策的心理,即希望他們尋找到“第三空間”,尋找到新的敘事方式。
麥克勞德對于中產后代青少年孫輩施加的筆墨多可見其慈愛,他并未因為孫輩與故土的微弱聯系而輕易責備之,而是期待他們能夠通過回歸故鄉發現故鄉的美好,關注并回歸到族裔文化語境。
《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無疑是在后殖民語境下將“困境”與“流散”展現得直觀生動的著作,其作者也為世界后殖民主義小說探索了敘事空間,探索了在現實世界中“第三世界”里的表達方式,這部作品也一定會感染更多的人關注后殖民語境下各種群體面臨的現狀,鼓舞更多的人創作出有力的又能觸動人心的作品。
參考文獻
[1] Taylor J O. Art Imagery and Destiny in Alistair MacLeod’s Fiction: “ Winter Dog” as Paradigm[J].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1994, 29(2): 61-69.
[2] Scott V. Review Essay: Eastern Mosaic: A Review on the Culture of the Maritimes[J]. 1990.
[3] Selby S. More than Representation: Storytelling and Self-Invention in Alistair MacLeod's Narratives[J]. British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2008, 21(2): 239-256.
[4] Thompson P. “If you’re in quest of the Folk, you’ve come to the wrong place”: Recent Trends in Atlantic Canadian Literary Criticism[J]. Acadiensis, 2012, 41(1): 239-246.
[5] 黃詠梅,汪廣松.面對“平地的艱難”——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閱讀對談[J]. 青年文學,2019(5).
[6] 馬秀華.人類生存異化的關注者——加拿大作家麥克勞德的作品解讀[J].名作欣賞,2014(29).
[7] 萬姍,劉立輝.第三空間與身份建構:《人造黑人》的后殖民解讀[J].當代外國文學,2019.
[8] 王冠珠.來自布雷頓角的生命回響——記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J].世界文化,2018(4).
[9] 張陟.海邊的風笛手——阿·麥克勞德的短篇小說創作簡評[J].世界文學,2013(4).
(特約編輯 楊" 艷)
作者簡介:陳霄蕊,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