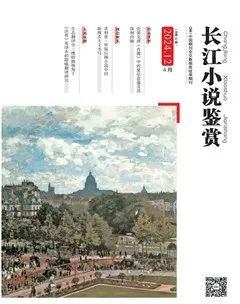論果戈理《肖像》中的象征意蘊及其深刻內涵
[摘" 要] 作為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果戈理擅長通過忠實反映現實生活中荒誕不合理的現象來揭露社會制度的黑暗與腐朽,由此引發人們對于國家命運與民族出路的思考,因此文學界中對果戈理的研究往往側重于現實主義批判,對其文學創作中象征主義的研究相對匱乏。但不可否認的是,縱觀果戈理一生的文學創作,象征主義手法依然是其展現現實世界善與惡、美與丑、喜劇與悲劇的一種藝術工具。《肖像》作為果戈理歷時8年之久,歷經兩版反復對比刪改寫成的小說,在其創作生涯中具有特殊意義,文中充滿豐富象征意蘊的世界不僅表達出果戈理獨特的善惡觀,更體現出果戈理對心靈的不懈探索。
[關鍵詞] 象征主義" 主觀能動性" 善惡觀" 形而上" 現實主義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12-0028-04
19世紀的俄國禁錮于腐朽的封建農奴制度,在沙皇與社會上層階級的剝削之下茍延殘喘、行將就木,殘酷的社會現實自然而然地催化出批判現實的文學思潮。憑借著對現實驚人的洞察力及毫不掩飾的批判,果戈理成為俄國“自然派”文學的奠基人,使“生活的散文”提升為“生活的詩”[1]。與此同時,隨著果戈理創作的進展,其象征主義手法也在不斷發展,《外套》《鼻子》《肖像》《欽差大臣》《死魂靈》等作品都各自展現出深刻的象征內涵。這些作品之中,《肖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果戈理創作早期與晚期的分水嶺,因為在小說《肖像》創作期間,果戈理開始經歷思想上的“危機”,對于國家前途的迷茫使作家逐漸轉向對“心靈的事業”[2]的探索。
王爾德在創作《道林·格雷的畫像》時曾認為一切藝術既是表象,也是象征,他的這番理解在今天看來可以說是對果戈理《肖像》跨越時空的影射[3]。小說《肖像》全文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講述貧窮的青年畫家恰爾特科夫在意外獲得肖像畫帶來的巨額財富后,不斷追名逐利直至毀滅的過程;下半部分講述肖像畫畫家在創作肖像畫過程中受到邪惡力量的影響,但最終迷途知返實現自我救贖的過程。果戈理在塑造恰爾特科夫和肖像畫畫家的過程中賦予了他們不同的象征含義,但這種含義并非直接定義了主人公的善惡好壞,而是將視角轉向主人公的內心世界,通過挖掘他們的情感與想法,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將善與惡由主體轉變為客體,由行為的施加者變為行為的承受者。于是主人公對于善惡自發的主動追求代替了善惡天性控制主人公被動行動的情況,這種主客體的轉換,使得恰爾特科夫的行為由簡單的“惡”轉變為“向惡”,肖像畫畫家的行為由簡單的“善”轉變為“向善”,象征的意義由形而下轉變為形而上,在表達出果戈理獨特善惡觀的同時,也為其獨特現實主義的塑造埋下伏筆。
一、“向惡”的象征:肖像與墮落
果戈理是一位善于寫惡的作家,他的眼睛總能夠發現生活中存在的各種各樣的惡,并犀利地將這些惡訴諸于筆端,別林斯基認為,果戈理筆下的現實生活被表達得“赤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1]。與此同時,果戈理也是一位善于刻畫魔鬼的作家,但其筆下的魔鬼并非是虛無縹緲的。“他第一個看到了不戴面具的魔鬼……他第一個明白,魔鬼的面孔不是遙遠的、陌生的、怪異的、虛幻的,而正是身邊的、熟悉的、現實的‘人的,太人的’的面孔”[4]。魔幻世界與現實世界在果戈理的筆下實現了和諧的交融,并“以如此巨大的穿透力呈現出并擊中了人性和社會的弱點及邪惡方面,從而使無限夸張到荒誕無比的幻想或魔幻世界獲取了嚴酷的真實性和現實意義”[5]。
在本文中,惡的源頭集中體現在肖像上,因為放債人將自己的靈魂轉注于肖像中,并渴望自身邪惡的精神本質永存。區別于放債人的邪惡,恰爾特科夫的天性是崇高的,他擁有天賦的繪畫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恰爾特科夫是個沒有一絲一毫邪念的人。果戈理認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帶著原罪出生的,一個人向善還是向惡的關鍵取決于他抑制內心“永恒之惡即人類之鄙俗”[4]的能力。文中恰爾特科夫在面對肖像時實際上已經感受到了不由自主的恐懼,但是當他看到夢寐以求的金圓時,他的欲望還是壓倒了恐懼。因此,與其說是魔鬼在引誘恰爾特科夫,不如說是恰爾特科夫主動選擇被魔鬼引誘,在這個過程中恰爾特科夫始終是一個擁有自我意識的、能夠獨立進行價值判斷的個體,他的主觀能動性并沒有被束縛。可以說,恰爾特科夫是在“清醒著墮落”,是他主動選擇了向惡靠近。不同于肖像“外部的惡”,恰爾特科夫是一種“形而上的內在因素之源頭的惡”[6]。
恰爾特科夫并不是唯一一個“向惡”的人,在他之前就已出現了許多主動同魔鬼進行交易的人,他們中不僅有來自上層階級卓越的青年政治家和英俊的貴族公爵,也有來自下層階級樸實的平民、伙計和安分守己的趕車人。但無一例外的是,在主動與魔鬼進行交易后,他們都走向了痛苦與毀滅。因此,恰爾特科夫只是作為“向惡”的一個典型人物被表述出來,果戈理用他“向惡”的過程象征社會上各形各色的人墮落的過程,暗諷了現實生活中人們心靈鄙俗、迷戀追求庸俗無聊事物,面對誘惑無法堅定意志的現象,“魔鬼正是那個渺小——卻因我們自己的渺小而顯得偉大的東西;正是那個軟弱——卻因我們自己的軟弱而顯得強大的東西”[4]。
相比于天性本就邪惡的魔鬼,果戈理更害怕看到日常生活中的人墮落成“不戴面具的魔鬼”,他痛心于美好事物的覆滅和天資聰慧的人的隕落,因為“被墮落的超自然生物(魔鬼)當作交換籌碼的不僅僅在道德層面,更是囊括了對美的鑒賞力和創造美的能力”[7]。因此,果戈理希望人能夠抑制心中惡的傾向,努力克服心靈的鄙俗,不是向惡墮落,而是向善前進,去追求精神世界的豐盈充實。恰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揭示出的果戈理一生的核心主題:與鬼的斗爭[4]。
二、“向善”的象征:苦修與救贖
許多人認為,果戈理在忠實反映惡的同時,忽略了對善的發掘,他的作品中總是缺乏正面的“善”的人物形象。羅贊諾夫甚至認為:“果戈理就是用僵死的眼光看生活,他在其中看到的只是死魂靈。”[8]不可否認的是,在果戈理的眼里,現實世界的確是黑暗且冷酷的,并且他也毫不回避地、極力地向世人展現出這種地獄般的俄羅斯,正如其在《作者自白》中承認道:“在《欽差大臣》中我決定將俄羅斯所有我所知道的粗野、愚蠢、惡劣的東西,所有那些最需要人的公正的地方和情況下出現的不公正歸在一堆并一下子就嘲笑所有這一切。”[9]但單純展現“惡”并非是果戈理創作的終極目的,他認為“藝術是往心靈里建立和諧和秩序,而不是驚慌不安和紊亂”[9]。果戈理希望的是讀者在自己筆下看到一個真實殘酷的俄羅斯的同時,也能看到一個光明復蘇的俄羅斯;希望讀者在看到一個個“僵死的靈魂”的同時,也能看到他們完成“靈魂的復蘇”的過程,這種“向善”的靈魂救贖的過程才是果戈理著重強調的。
因此,當我們著眼于果戈理筆下一些典型的象征“惡”的人物形象時,通過分析其行為軌跡往往能夠窺探到一種“向善”的動機。以《死魂靈》為例,第一部中的乞乞科夫是純粹“惡”的象征,他生而為人,卻以惡魔的姿態存在,仿佛游走于人世間“僵死的靈魂”,但即便這樣,乞乞科夫也會在謄寫農奴名單時不由自主去想象筆下之人生前的模樣,并發出完全“不乞乞科夫式”的感慨,這些細節為果戈理在《死魂靈》第二部中展現乞乞科夫靈魂上的復蘇與覺醒做了鋪墊。
《肖像》中肖像畫畫家作為果戈理筆下不可多得的正面人物形象,其自然被賦予了“向善”的象征含義。與恰爾特科夫相同的是,肖像畫畫家也是一位天性崇高的藝術家,“他是一個自學的畫家,無師自通,也不懂什么規則和法律,僅僅被渴求完美的欲念所驅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沿著靈魂所昭示的道路前進”[10],但區別于恰爾特科夫的是,肖像畫畫家克服了心靈的鄙俗,將自身的藝術創作視為上天的恩賜,而非獲取財富的工具,“正像莊嚴的靜穆比塵世的煩囂崇高,創造比破壞崇高……偉大的藝術創作也比世上的一切東西不知道崇高多少倍”[10]。因此,他的精神世界始終充盈著一種高尚的力量,這股力量成為驅使他迷途知返、主動遁跡荒野,潛心苦修,最終求得救贖的關鍵所在。
在果戈理看來,人是有罪的,也是一定會犯罪的,因為他們并不完美,而潛心苦修正是幫助人們洗滌凈化靈魂中骯臟與污垢,引領人們救贖自己,走向真善美的唯一途徑。果戈理曾在1840年給Н·別洛澤爾斯基的信中就寫道:“我現在更適于過修道院的生活,勝于過世俗生活。”這種苦行僧的志向、修道士的理想借助肖像畫畫家的象征意義在小說中再次被真切地表達出來[2]。
三、充滿豐富象征意蘊的世界:形而上現實主義的表達
別爾嘉耶夫曾評價果戈理:“不是現實主義者,也不是諷刺作家,他是幻想家,他描繪的不是現實的人們,而是最原始的惡的靈魂,首先是俄羅斯人所具有的虛偽的靈魂。”[11]這番話在某種程度上揭示出果戈理形而上現實主義的表達。事實上,果戈理這種獨特的現實主義傾向早有預兆。以喜劇《欽差大臣》為例,作品上映的巨大成功并未給果戈理帶來滿足,反而使作者為它的“失敗”而感到難過,“我生觀眾的氣,因為他們沒理解我;我也生自己的氣,因為觀眾不理解我,這怨我自己”[12]。這種異常反應的緣由可以在《欽差大臣的結局》中果戈理作出的諷喻性闡述上找到解釋,文中他寫道:“劇中的縣城應當理解為‘心靈的城’,劇中的官吏們應理解為人類的各種貪欲,赫列斯塔可夫是‘輕浮的上流社會的良心,出賣的、騙人的良心’,而人真正的、大公無私的良心卻被象征為喜劇收場時宣布駕到的那個真正的欽差大臣。”[12]由此可見,果戈理真正想要呈現給觀眾的是以現實主義手法對鄙俗心靈的嘲笑,可觀眾只看到了鄙俗的現實,卻沒看到鄙俗的心靈,這種對形而上現實主義的忽視正是作者的沮喪與挫敗之處,因為果戈理始終把“心靈的事業”當作自身的永久事業。
別林斯基曾高度評價果戈理文學創作的樸素性、人民性、真實性與獨創性,稱贊果戈理為“現實生活的詩人”[13],肯定其在現實主義文學發展進程中至關重要的作用。可當果戈理發表小說《肖像》后,別林斯基卻給予了極其消極的評價:“《肖像》是果戈理君在幻想體裁方面的一篇失敗之作”,是“毫無想象摻雜其間的顯然的蛇足”[13]。但這種批評無疑是片面的,因為果戈理不僅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更是一位從事“心靈的事業”的道德家,在《肖像》中他追求的是對“形而上的內在因素之源頭的惡”的深度發掘,而不僅僅是對社會政治制度等外在因素的惡的粗淺表現,在其看來“社會弊病最深刻的根源不在于社會本身,而在于人”[14]。
《肖像》中果戈理首先把現實生活解析成了兩個層面,不僅包括外在的、顯現的、形而下的物質生活,也包括內在的、隱蔽的、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其次把創作的重心由對物質生活的聲色描繪轉入了對精神生活的深入刻畫,從而把隱藏在現實世界身后難以用言語描繪、難以用理性認識,只能依托于心靈感知的形而上的現實主義呈現在讀者眼前。在對這種形而上現實主義進行批判的同時,果戈理強調出一個人內在改造的必要性,并認為這種改造歸根結底必然能夠成為整個國家改變面貌的保證[2]。
四、結語
《肖像》中果戈理的象征藝術通過深化主人公的主觀能動性,著重展現出人對于善惡的主動追求,表達出“人性集神性與魔性于一身,塵世集天堂與地獄于一體。不是上帝與魔鬼來到塵世彼此較量,而是人在面對善與惡時內心的掙扎”[15],這種強調人的主體性的美學思想幫助小說達到了主體與客體、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高度有機統一。
回顧果戈理的創作歷程,在《肖像》之前,作者就已經開始使用豐富的文字符號象征“善”與“惡”,例如《五月的夜》中連結天堂與人世的梯子,《圣約翰節前夜》中烏克蘭民間的妖魔小鬼,等等。然而,《肖像》的出現創造出一種更為豐滿的象征“善”與“惡”的手法,使得果戈理筆下的象征不再是單薄的文字符號,而成了一種厚重的心靈符號,它不僅打破了人們對世界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刻板印象,更展現出果戈理號召人們摒棄庸俗、完善自我、追求崇高,實現俄羅斯大地光明復蘇的深深教誨。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審視《肖像》,我們能夠發現果戈理隱藏在象征手法之下渴望通過改造心靈拯救民族與國家的想法,這種想法雖然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值得肯定的是,它無疑是果戈理憂國憂民和愛國精神的重要體現,也是其在當時年代下對于如何拯救黑暗僵化的俄羅斯這個宏大時代命題所做出的答復。
參考文獻
[1] 尼·瓦·果戈理.果戈理小說戲劇選[M].滿濤,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2] 尼·瓦·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七卷)[M].吳國璋,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 奧斯卡·王爾德.道連·格雷的畫像[M].黃源深,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4] 德·謝·梅列日科夫斯基.果戈理與鬼[M].耿海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
[5] 金亞娜.并非不可解讀的神秘——果戈理靈魂的復合性與磨礪歷程[J].俄羅斯文藝,2009(03).
[6] 宋胤男.白銀時代宗教哲學批評視閾下的果戈理研究[J].俄羅斯文藝,2017(01).
[7] 耿海英.文本自身的反駁——果戈理的妖魔元素對“現實主義”神話的解構[J].中州大學學報,2022,39(05).
[8] 瓦·瓦·羅贊諾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M].張百春,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9] 尼·瓦·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六卷)[M].吳國璋,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 尼·瓦·果戈理.果戈理選集(第二卷)[M].滿濤,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11] 尼·亞·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12] 袁晚禾,陳殿興.果戈理評論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13] 維·格·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M].滿濤,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3.
[14] 金亞娜,劉錕,張鶴,于明清等.充盈的虛無——俄羅斯文學中的宗教意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15] 宋胤男.從墮落到救贖:果戈理《肖像》兩種版本之比較[J].西伯利亞研究,2021(06).
(特約編輯 范" 聰)
作者簡介:魏沛靈,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為俄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