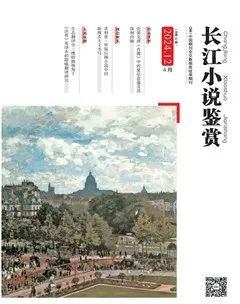人間孤影:喬·克里斯默斯的情境身份
[摘" 要] 喬·克里斯默斯是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小說作品《八月之光》的主人公。他一生下來就被人懷疑是黑白混血兒,四處轉徙,最終在杰弗生鎮殺害了北方白人喬安娜·伯頓,被私刑處死。克里斯默斯在身份掙扎中的人生軌跡歷來是研究者討論的重點,但運用社會思維理論進行分析的文章尚不多見,本文運用社會思維理論展現克里斯默斯思維的社會特點,證明克里斯默斯情境身份的第一人稱歸因和第三人稱歸因之間的斷裂是導致他走向最終毀滅的根本原因,更為清晰地描畫了作者對種族主義的尖刻批判。
[關鍵詞] 社會思維" 情境身份" 《八月之光》" 克里斯默斯
[中圖分類號] I10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12-0036-04
一、作品背景與人物介紹
社會思維理論(social mind theory)由英國認知敘事學家艾倫·帕默(Alan Palmer)于2010年正式提出。帕默主張看待文學作品中外在、活躍、公共、社會和具體化的思想,聚焦群體社會中相互交織的虛構思想。他將小說中的人物的公共思維劃分為人物間的“交互思維”,代表了人物共識的在語言和行動中表征的集體思維。《八月之光》是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探索美國南方社會生活當中種族、性別等多重面向的重要作品,重點塑造了許多在美國南方鄉村清教徒社會中邊緣人物在以次要人物、匿名人物所轉喻的群體環境當中的種種掙扎,集體思維交互的特征明顯,不失為社會思維理論應用的新領地。
小說主人公喬·克里斯默斯是一個種族身份不明的私生子。他在收養他的長老會鄉村長大,同女招待博比有了第一段戀情。后來混跡于黑人貧民窟,先后從事各種工作,但始終無法融入任何社區或建立任何持久的人際關系。來到杰弗生鎮后,他殺害了跟他有了情愛關系、支持黑人權利的北方白人喬安娜·伯頓,最終因此被私刑處死。克里斯默斯模糊不清的種族身份,是推動他人生軌跡不斷轉變的核心。對此,福克納自己曾經說過:“我認為他的悲劇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是誰——究竟是白人或是黑人。因此他什么都不是。由于他不明白自己屬于哪個種族,便存心地將自己逐出人類。在我看來,這就是他的悲劇,也就是這個故事悲劇性的中心主題: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一輩子也無法弄清楚。我認為這是一個人可能發現自己陷入的最悲哀境遇——不知道自己是誰卻只知道自己永遠也無法明白。”對于這一中心問題,學界也多有探討,生安鋒指出,克里斯默斯的人格具有現代社會的分裂特點,這使得他的性格模糊而不確定,成了懸置在“黑人”和“白人”之間的變化過程[1]。徐其萍揭示了喬的種族和性別主體身份在“強迫性重復”中逐步內化了白人/黑人、男性/女性等種族和性別身份的二元思維模式,喪失了作為人應有的主體意識和抗爭能力[2]。這些討論雖然從不同側面表現了克里斯默斯種族身份的建構特點,但大體仍注重于分析他個體性格的形成,預設了一種盡管模糊、矛盾,但仍屬于個體本質的身份圖示。生安鋒在運用后殖民主義剖析克里斯默斯的身份僵局時,引用格林那克指出的觀點:“一般說來,身份感牽涉到對他人的關系并包含一種社會決定的因素。伴隨著本人和/或他人的一定程度的觀察。即便是對個人來說,他內心的自我感覺也不足以產生出一種身份感……對自我形象的感覺(意識的核心,圍繞他一個人的身份感得以建立)由于不斷地重新定義而得以保持并或許被激活。這種重新定義伴隨著與他人的比較和對比。”對這種本質主義視角有了重大突破,但可惜的是,其對克里斯默斯身份形成的公共性、群體性特點仍然流于模糊。克里斯默斯“為了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而瘋狂地逃避社會”[3]的這種論述仍然賦予了主人公一種追求身份建構的能動性,以致邏輯本身都沾染了自相矛盾的意味。然而,在帕默看來:“諸如自我、身份、主體性這些概念有時會以無益的、限制性的方式關注一種脫離了社會語境的個體。”相比之下,情境身份的概念,則意在傳達一種個體自我認知和他人對個體認知視角的平衡,是對自我性質第一人稱歸因和第三人稱歸因的結合。克里斯默斯對于自身種族身份的傾向、判定,和克里斯默斯社會交往中的其他集體社會思維——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南方的社會思維集體,以“隱性雙重認知敘事”的非具身主體浮現——對他的身份的下意識猜想與感性認識,構成了小說中克里斯默斯種族身份的第一人稱歸因和第三人稱歸因。本文將運用帕默理論中的情境身份概念表明:《八月之光》中,導致克里斯默斯數次自我放逐的幾次重要挫折,都源于這種第一人稱歸因和第三人稱歸因的錯配和失當。這使得克里斯默斯無法在美國南方意識形態這一社會思維最大框架下形成一個統一的情境身份,一次次在“角色崩潰”之后黯然離去[4]。
二、克里斯默斯的身份歸因進程
事實上,第一位分析克里斯默斯身份狀態的評論家確實是福克納自己,在克里斯默斯已死時,他安排了一位美國南方社會的杰出人物——地方檢察官史蒂文斯對他發表了一番闡釋。他作為美國南方社會思維的一分子,將克里斯默斯的行為解讀成白人血液和黑人血液抗爭的結果。白人血液仁慈、虔誠;黑人血液狂暴、引他走向絕望[5]。克里斯默斯終其一生,都在這種基于種族秩序的第三人稱身份歸因中不斷審視。克里斯默斯對自己種族身份內在的第一人稱歸因讓其無法承認自己情境身份的合法性。他的身份失敗主要是在和所遭遇的各個子群體的歸因失調之中作用的。
1.情境身份的構建嘗試
在文中暗示的海因斯誘導孤兒院其他孩子叫他“黑鬼”之后,黑人身份的潛在可能就在他心中不斷蠢動。在面對鋸木棚里的黑女孩時——這一點可以看作喬個人生命起源的隱喻——喬“立刻感到慌張得要命,像體內里有什么東西要翻倒出來”,他聞到她的氣味,就“立即知道那是黑種女人的氣味”。隨后開始不自覺地用腳踢她。這實則是克里斯默斯白人身份受到了挑戰,是他黑人認同的一次覺醒。克里斯默斯在此和彌漫全書的美國社會這一“非具身主體”進行了思維交互,他在黑女孩(無力的,被強暴、女性化的黑人符號)面前,猜測到了自己第三人稱歸因的毀滅性結局,而開始校正自己的第一人稱歸因。克里斯默斯和美國社會在此達成了一種合謀,一種鎮服、壓抑黑色人種的合謀。這次合謀,縱然是以克里斯默斯諷刺地遭了養父一頓毒打為代價——這里或可見出福克納本人的傾向——仍不失為克里斯默斯所實現的“白人”情境身份建構。三年之后,克里斯默斯躺在戀人身邊回憶起這段經歷,她坦白了自己的黑人血脈。
她沒有動彈,但立即說:“你在撒謊。”
“就算是吧。”他說,躺著不動,手仍在撫摸。
“我不相信。”她的聲音響在黑暗里。
“信不信由你。”他說,手仍然未停。
女招待的愛情經受不起多大的考驗,尤其是在克里斯默斯在她面前砸死了前來捉奸的養父之后。為了置身事外,她用起了克里斯默斯的黑人身份做幌子。(“把我給陷進去,而我一直把你當白人對待。當白人!”……“他是個黑鬼……我白被他奸了!”)改變了對克里斯默斯的第三人稱歸因,來為自己拋棄克里斯默斯尋求正當性。這里博比的意圖并不在于說服克里斯默斯,也不在于她對餐館伙伴的將信將疑,而更多是仰仗種族歧視美國社會來定性克里斯默斯身為黑人的“原罪”。后者作為“隱性雙重認知敘事”的非具身主體再次被點出。克里斯默斯的黑人情境身份因此并不是單純同博比等人所在的小集體構建,也是南方社會的大集體所參與的。克里斯默斯殺害了養父,也失去了愛情,他已然在世間無處立足。這次失敗建構了他在社會語境中一種合法的情境身份,但卻并非他本來所意想。
2.情境身份的歸因失調
克里斯默斯在這次挫折之后即失去了建構穩定情境身份的能力。這一方面是表現在喬本身對于白人歸因所附加的社會規范十分逃避——參見他對同伯頓小姐結婚的抗拒,他選擇了“前三十年經歷”使他選擇的道路,也可見于他通過說自己是黑人來嫖霸王娼的行為——另一方面,亦表現在他對黑人種的潛在蔑視:例如他對黑人女孩的毆打,例如他不相信會有白種女人愿意找黑種男人。在他調整第一人稱歸因之后,對方沒有按照他所預想的南方社會集體思維的期待行事,反而激起了他的驚懼悲憤。
這種第一人稱歸因的左右搖擺,本質原因即是克里斯默斯在嘗試同南方社會進行思維互動時,并不能在其二元的種族秩序中找到自己的混雜位置。他的第一人稱歸因和第三人稱歸因在深層上即是斷裂的。他因此永遠不能從他把戲似的破壞情境中獲得自己認同的情境身份,縱然懷抱著利用這種種族秩序的天然想法也不能。固然他確實也不知道自己認同什么。在和黑種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時候,他“竭力往體內吸進黑人的氣味,吸進幽深莫測的黑人思想和氣質;然后又從體內著意呼出白人的血、白人的思想和白人的氣質。‘在路過白人街區的時候’‘這就是我向往的一切’他想,‘看來這要求并不顯得那么過分’。”克里斯默斯成了南方社會的社會思維之中一精神分裂的個體。
克里斯默斯游蕩人生的結束始于他來到杰弗生鎮后同伯頓小姐發生的關系。她和克里斯默斯一樣是美國南方社會的外來者,從新英格蘭地區遷徙至此的她,由于內戰的原因,和她本人對改善黑人民權懷著宗教性的狂熱,而被小鎮居民所隔離、憎惡。又被當地的“有色鄉親們照看著”。她和她死去的父祖兄弟,(哥哥加爾文因為爭取黑人選舉權演說而被鎮上的前邦聯士兵、奴隸主殺害了)形成了同杰弗生鎮居民不同的集體思維。在了解到克里斯默斯的混血身份之后,她期待他上黑人學校,去黑人律所,以黑人身份為黑人斗爭服務。這是由于在伯頓小姐及其家人為代表的美國北方白人(也包括了他們蔭蔽之下的鎮中的黑人)的集體思維當中,都假設了這樣對于黑人身份的第三人稱歸因。結局是,喬仍然無法擺脫自己作為白人的第一人稱歸因,反抗了伯頓的安排。伯頓小姐在交互過程中未能閱讀到喬在美國南方社會種族秩序的內在認同。(“如果她能看清他的面孔,會發現它陰郁而面帶沉思”)事實上,在同克里斯默斯的情愛關系上,伯頓一直更堅決、封閉,居于主導地位,思維閱讀能力較差,“精神已淪為自我保護本能的犧牲品”。喬則對她的精神世界和社會生活始終抱有謹慎的拒絕。他浸潤在美國南方社會思維中,也根本無法自我歸因為一個自立、自信的黑人形象。在伯頓小姐要求他上黑人學校,去找黑人律師,告訴他們他是黑人的時候,克里斯默斯“仿佛突然命令自己的嘴說道:‘住嘴,別再胡說八道!聽我說。’”克里斯默斯再次拒絕了黑人的情境身份。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結果。
諷刺的是,通過殺害伯頓小姐,被通緝,克里斯默斯終于對自己的黑人歸因徹底滿意了。“他仿佛看見自己終于被白人趕進了黑洞洞的深淵……現在他終于真的跨進來了……‘這便是我三十年來想要得到的一切。看來整整三十年我所要求的并不太多’。”一個殺人犯不會被看作白人,鎮上對他的稱謂也統一地成了“黑鬼”。他感知到了自己終于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唯一、穩固的黑人歸因,(固然是南方白人構建的,歧視性的黑人)反倒讓他在身份秩序當中第一次確認了自己的位置。他和美國南方社會的思維互動終于一勞永逸的和諧了。這樣的命運安排,凸顯了福克納對美國南方種族秩序的諷刺。
在福克納的《八月之光》中,喬·克里斯默斯的個體身份困境不僅是其個人層面的內在掙扎,更是社會集體思維對個體身份建構的顯著影響的體現。通過克里斯默斯的悲劇性命運,作者揭示了個體在社會集體思維框架內的無力感與邊緣化狀態。克里斯默斯的身份認同問題,實質上反映了美國南方社會種族歧視與身份政治的微觀縮影。他的存在挑戰了南方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界限與身份標簽,而這種挑戰并未帶來預期中的解放,反而導致了更深層次的孤立與排斥。
克里斯默斯在白人與黑人兩個社群之間的徘徊,體現了他在身份認同上的不斷嘗試與自我否定。他試圖在這兩個世界中找到自我定位,但最終發現自己既無法融入白人社群,也無法真正被黑人社群所接納。這種雙重排斥現象,不僅源自他種族身份的模糊性,更根植于社會集體思維對他所持有的刻板印象與預設判斷。個體的第一人稱歸因是在與第三人稱歸因互動中不斷重新定義的,而克里斯默斯卻始終未能在這種互動中實現自我認同的建構。
克里斯默斯與喬安娜· 伯頓之間的關系,既是克里斯默斯第一人稱歸因僵局的延續,也是集體思維沖突的極端體現。伯頓小姐,作為北方白人的代表,其集體思維中蘊含著對黑人民權的支持,這與南方社會的種族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試圖將克里斯默斯納入自己的集體思維框架中,但克里斯默斯的內心抗拒這種預設的身份安排,他的“非具身”的集體思維與伯頓小姐的期望之間發生了根本性的沖突。這種沖突不僅是個體層面的,更是南北不同社會集體思維的碰撞與交鋒。
克里斯默斯的最終崩潰,是他無法在南方社會的種族秩序中找到自我定位的必然結果。他的身份認同問題,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得到了“解決”——通過犯罪行為和社會的徹底標簽化,他以某種受虐狂的形式被迫接受了社會賦予他的身份歸因。這一悲劇性的轉變,凸顯了社會集體思維對個體身份建構的強大影響力,同時也暴露了種族歧視對社會和個體造成的深遠傷害。
福克納通過克里斯默斯揭示了個體在社會集體思維中的困境,反映了其對美國南方社會意識形態秩序的深刻批判。他借助文學的力量,呼吁人們反思并超越固有的種族觀念,尋求一種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會身份建構方式。克里斯默斯的隕落,折射出了福克納對于個人身份的隱含的不信任和對本質主義身份性質的拒絕。
三、結語
總結回溯克里斯默斯的一生,可以發現他始終囿于兩層社會思維的拘束之間,在同作為“非具身主體”的美國南方社會的失敗互動導致他無法對自己的情境身份形成穩定的認同,這導致他無法同書中的一般人物建立關于自己身份展演的共識。被自我放逐,被社會放逐,克里斯默斯永遠被困在了無法看到自我的靈薄獄中。他想:“可我從未走出這個圈子。我從未突破這個圈,我自己造就了永遠無法改變的圈。”克里斯默斯作為美國南方社會邊緣人物的人生經歷,揭示了身份的社會建構和個體思維的社會決定特點,表現了福克納對于美國南方這一土地更為復雜的悲憫和同情。
參考文獻
[1] 生安鋒.現代社會中人格的分裂與模糊——試析《八月之光》中的雙重人格[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3(S1).
[2] 徐其萍.論《八月之光》中身份敘事的創傷維度[J].陜西教育(高教),2017(07).
[3] 生安鋒.白皮膚、白面具:《八月之光》主人公喬·克瑞斯默司的身份僵局[J].外國文學研究,2004(04).
[4] 陳成文.社會學[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5] [美]威廉·福克納 著.八月之光[M].藍仁哲,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特約編輯 范" 聰)
作者簡介:印光昊,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中國地質大學(北京)2024年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社會思維理論視域下的福克納《八月之光》"""群體思維研究”的成果,項目編號:A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