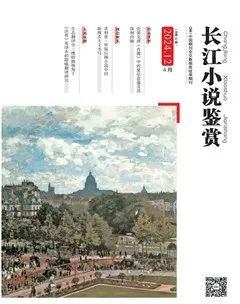《牡丹亭》中象征因素的探討與解析
[摘" 要] 湯顯祖《牡丹亭》的整個劇本,是圍繞杜麗娘“因愛而死,為愛復生”的情節展開的,從人物形象到情節發展,從場景布置到唱詞編排,《牡丹亭》都充滿了獨特的藝術魅力。本文從“杜柳相愛的重要媒介:夢”“花神、胡判官、石道姑等神秘人物的塑造”以及“被虛化的‘亭’”三個角度分析湯顯祖是如何在《牡丹亭》中運用象征手法營造出一種夢幻般的氛圍。
[關鍵詞] 《牡丹亭》" 湯顯祖" 象征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12-0076-04
一、前言
《牡丹亭》全稱《牡丹亭還魂記》,取材于話本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是明代劇作家湯顯祖的代表作。湯顯祖身處險惡官場,滿腔報國熱情逐漸被官場中的爾虞我詐消耗殆盡。上疏貶官事件后,他便辭官告歸,開始了隱居生活,專心投身于戲曲創作之中。湯顯祖在原作《杜麗娘慕色還魂》的基礎上,融合魏晉志怪小說和唐傳奇有關的故事情節,進行了獨具匠心的藝術創作,將原作擴展為長達五十五出的戲曲劇本《牡丹亭》。劇本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南宋年間,南安太守杜寶只生一女,名為杜麗娘,管教頗嚴。麗娘在丫鬟春香的慫恿和美好春光的感召之下,私游家中花園,并在夢中與秀才柳夢梅歡會。被落花驚醒后卻因思戀過度,香消玉殞。隨后杜寶升任,舉家離開南安,在埋葬麗娘之地修建梅花觀守護其靈位。柳夢梅進京趕考途中在梅花觀養病,拾得麗娘的自畫像,并與麗娘幽魂相會。隨后柳夢梅在麗娘指點下為其開棺,使其復生,二人便結為夫妻。后柳夢梅得中狀元,麗娘又經許多波折與父母相認,故事終得一圓滿結局。作者湯顯祖以此作歌頌青年男女間的真摯情感,作品處處傾注著作者的心血,也處處展現著作者的絕世才情。《牡丹亭》整個劇本,是圍繞杜麗娘“因愛而死,為愛復生”的情節展開的,而這一情節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生”觀念為依托。本文將基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象征因素,對《牡丹亭》中的象征因素進行探討與解析。
二、《牡丹亭》中的象征色彩
《牡丹亭》中,杜麗娘一夢而亡卻不入輪回,去世三年但尸身不腐,她勇敢地追求世俗的欲望與現世的幸福,最終與柳夢梅結為良配,與父母親人美滿團聚。在杜柳二人的愛情故事中,花神、胡判官、石道姑等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扮演了重要角色均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他們也都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人物。從人物形象到情節發展,從場景布置到唱詞編排,《牡丹亭》都給人一種玄幻之感。筆者將從“杜柳相愛的重要媒介:夢”“花神、胡判官、石道姑等人物的塑造”以及“被虛化的‘亭’”三個角度分析作者湯顯祖是如何在《牡丹亭》中運用象征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及安排情節發展的。
1.杜柳相愛的重要媒介:夢
湯顯祖在創作《牡丹亭》時,將自己的情感深刻地融入其中,他“因情成夢,因夢成戲”,并稱自己的“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1]。在《牡丹亭》中,杜麗娘的經歷體現了這種“因情成夢”和“因夢成情”的轉化。在春色滿園卻無人共賞的寂寞中,杜麗娘因傷春之情而夢見柳夢梅,這個夢境激發了她對柳生的愛慕之情,進而引發了后續的冥判、回生、圓駕等一系列情節。
《牡丹亭》中“夢”意象的功能就是讓杜麗娘被壓抑的里比多——本能欲望獲得象征性滿足。[[]]從杜麗娘的夢境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對個人情感的強烈追求,這種追求不僅是對愛情的渴望,也是對封建禮教體系的挑戰。她的夢境成了一種反抗的宣言,表明傳統的束縛對她已不再具有約束力。在她的內心深處,對愛情的渴望和對自由生活的向往異常強烈,這與她所處的封建社會環境形成了尖銳的沖突。她的生活和情感都被封建禮教所限制和壓抑,這種沖突最終引發了她的身心疾病。
《牡丹亭》通過杜麗娘的夢境和情感追求,展現了對個人情感自由的渴望,以及對傳統禮教束縛的批判。湯顯祖通過這部作品,不僅表達了對真摯愛情的贊美,也反映了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
在杜麗娘的精神世界中,她對青春活力和美好愛情的渴望成了一種對封建家庭和禮教有意識的反抗。她的不滿和反抗通過她的夢境得到了釋放,夢境成了她逃離現實世界的一種方式。在夢中,她可以自由地添加和修改個體世界中的任何元素,她可以短暫地逃離現實世界帶給她的痛苦和束縛。她的游園之夢,既是對現實的一種逃避,也是對理想生活的一種追求。
最終只有與柳夢梅的愛情才能徹底拯救她那顆壓抑而又躁動的心。杜麗娘的故事,不僅是對個人情感的追求,也是對整個封建社會的一次深刻反思和批判。她的夢境和現實生活的沖突,以及她對愛情的執著追求,展現了一個女性在封建禮教壓迫下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追求,同時也揭示了封建社會對個人情感的壓制和扭曲。
對于一夢而亡的說法,紀淮在《lt;牡丹亭gt;文字觀之二:生死》中指出:麗娘為花飛驚閃而亡,其他愛花而亡、相思病死、慕色而亡、感傷而死諸解,皆其注腳也。[[]]故筆者以為,杜麗娘早已自擬為花,游園時便覺自己的命運如同滿園春色一般無人欣賞;后來更是如莊周夢蝶一般,沉浸在自己的夢中,她看到花瓣掉落,便覺得看見了自己的死亡,故而花落驚得她身殞。
2.花神、胡判官、石道姑等人物的塑造
花神,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位女神,也被稱為花姑,是民間信仰中的百花之神。她被視為春天的使者,以其慈悲和神奇的力量,賦予大地生機與活力。人們深信花神能夠帶來吉祥和好運,她的存在象征著美好和希望。
在《牡丹亭》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愛情故事中,花神扮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在杜麗娘初次在夢中與柳夢梅歡會時,花神便用五彩繽紛的鮮花圍繞他們,為他們的相會營造了浪漫而甜蜜的氛圍。她的存在使得二人的相會充滿了詩意和美好,成為了一段難忘的記憶。最后,當杜麗娘從夢中驚醒時,一片落花輕輕飄落,驚醒了她的香魂,花神便在這時飄然而去,這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麗娘死后,她的鬼魂入地府,花神再次出現,這次她在胡判官面前為杜麗娘辯護。她以花神的身份,以其對生命的獨特理解和慈悲之心,說服了胡判官,使他允許杜麗娘重返人間尋找柳夢梅。花神的介入,不僅展現了她的力量,也體現了她對杜麗娘的深厚情感和對愛情的祝福。
在杜麗娘重返人間的過程中,花神繼續發揮著她的保護力量。她保護著杜麗娘的肉身不被損壞,確保她的復活能夠順利進行。花神的庇佑,使得杜麗娘能夠順利地找到柳夢梅,并最終與他團聚,實現了他們的愛情。
花神在《牡丹亭》中的形象,不僅是一位神秘而美麗的女神,更是一位充滿智慧和力量的存在。她在杜麗娘和柳夢梅的愛情故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既是他們愛情的見證者,也是他們愛情的守護者和促進者。她的存在,使得整個故事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富有浪漫和神秘色彩。
在《牡丹亭》的《冥判》一出中,胡判官作為地府中審案的官員,展現了一個與傳統印象截然不同的地府形象。在這里,地府并非陰森恐怖,而是與人間并無太大區別,環境依舊充滿了生機,人物也依舊有著豐富的情感和血肉之軀。這種設定打破了常規,為觀眾呈現了一個全新的地府世界。
胡判官在審理杜麗娘的案件時,聽說她是因慕色而亡,本欲將她貶至鶯燕隊。然而,在進一步查明杜麗娘與柳夢梅在姻緣簿上的姻緣后,再加上花神的勸說,他改變了初衷,應允了杜麗娘的幽魂回到人間尋找柳夢梅,并允許她與父母相見。這一轉變體現了胡判官的公正和慈悲,他不僅考慮到了杜麗娘的情感,也尊重了她的選擇。
胡判官在處理杜麗娘的案件時,不僅展現了他的公正和慈悲,更是替麗娘考慮周詳。他囑咐花神保護杜麗娘的肉身,千萬不要損壞,以便來日還魂。這一細節展現了他對杜麗娘的關心和照顧,他希望她能夠在人間得到幸福,并有機會重生。
盡管胡判官是地府的官員,但他依舊保有著人態、人性、人情。他允許麗娘去追求現世的幸福,以及對于復生還魂的認可,都是故事中人物思想的體現。他的形象打破了人們對地府官員的刻板印象,展現了一個有溫度、有情感的地府世界。
胡判官的形象和所作所為,使得《牡丹亭》中的地府不再是一個冰冷恐怖的地方,而是一個充滿了溫情和希望的世界。他的存在和行為,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使得整個故事更加豐富和感人。
石道姑在《牡丹亭》中扮演的角色是推動整個劇本情節發展的關鍵人物。她是一位具有神秘色彩的女性,以其獨特的身份和地位,貫穿于整個劇情之中。
在杜麗娘游園驚夢、一病不起之后,她的父親杜寶為了救治女兒,請來了石道姑進行禳解,希望借助她的力量能夠驅散病魔。石道姑誦讀經卷,為杜麗娘祈福,展現了她對于神秘力量的信仰和運用。
麗娘去世后,杜寶為了紀念她,在后花園上蓋起梅花觀,安置小姐神位,并請陳最良和石道姑看守。石道姑的存在,使得梅花觀成了一個神圣而神秘的地方,為后續劇情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石道姑發現了麗娘的幽魂與柳夢梅夜間歡會的秘密。這個發現促使石道姑決定采取行動,她叫上小道姑陪同,晚上去柳夢梅的房間探聽,并且闖進去搜人。這一舉動不僅揭露了麗娘與柳夢梅的關系,也使得麗娘意識到她與柳夢梅人鬼不同途的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麗娘坦白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并請求石道姑幫助她開棺重生。石道姑毅然決然地答應了她的請求,并幫助柳夢梅開麗娘之棺,使得二人得以團聚。這一行為展現了石道姑的善良和成人之美的品質,她不顧個人安危,為了他人的幸福而冒險。
麗娘還魂之后,她擔心被陳最良發現,惹來許多麻煩。在不知如何是好之時,石道姑再次獻計,勸說杜柳二人結成夫妻,找只船連夜逃走,共赴臨安。這一計策不僅讓他們擺脫困境,也為他們的未來鋪平了道路。
石道姑在整個劇情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既是神秘力量的代表,也是善良與智慧的化身。她的存在使得劇情更加豐富和緊湊,她的行為和決策對于整個故事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她的形象既神秘又親切,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難看出,《牡丹亭》中花神、胡判官、石道姑等人物,皆是通情達理、古道熱腸、變通靈活的形象,與杜寶、陳最良等呆板教條,只知“存天理,滅人欲”的腐儒形象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相比之下,這些故事人物顯得更加真實,更加有人情味兒,這與作者湯顯祖在創作時的情感偏好不無關系。而這些“至情”之人也更好地詮釋了湯顯祖的“至情”論思想,更好地服務于《牡丹亭》“至情”之主題。
3.被虛化的“亭”
《牡丹亭》劇本中的環境設置滲透著一股“玄幻風”,戲劇中的場景是夢境與現實的交替,人物交互的過程中也并沒有受到場景的限制。從街頭到廢園,從杜家到京城,人物的一來一去完全沒有被戲劇學中存在的舞臺遮擋。故而“牡丹亭”這一意向是不受時空限制的,是被展開的空間,也是被虛化的空間。在麗娘重生之前,杜柳二人未曾同時存在于“亭”中過,卻通過麗娘的夢境、麗娘的自畫像在不同的時空里完成了兩次對話。
從人物的角度來看,杜麗娘活動的“亭”與柳夢梅活動的“亭”是相對而言的。杜麗娘所處之處,是狹義的“亭”;而柳夢梅所處之處,是廣義的“亭”。杜麗娘的所有活動軌跡,從成長到死亡,都未踏出后花園一步,都沒有走出過后園的廢亭。正因如此,這個“亭”也成了杜麗娘魂系之所,同時也成了柳夢梅魂牽夢繞之處。柳夢梅雖是在“亭”里養病,在“亭”里攻讀,但他接觸的“亭”與杜麗娘不同。他在整個戲劇情節中,永遠都是跑出廢園去活動,他去科考、去官舉,去替麗娘尋找父親的消息,去接觸整個社會,這些行為都擴展了他的所在之“亭”,也使得柳夢梅一直活躍在廣義的“亭”里。
杜麗娘僅僅是傷懷姹紫嫣紅都付斷井頹垣,便夢到柳生,因愛而死;柳夢梅也僅僅是拾到麗娘的自畫像,便愛上了麗娘,即便得知二人是人鬼異途,也依然癡情堅定。“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4]便是杜麗娘之“亭”與“柳夢梅”之“亭”連接起來的原因。湯顯祖以色彩斑斕的奇思虛構接續現實中的情節走向,不僅將此前現實中并未直接關聯的生旦兩線交織關聯起來,還將至情推向了橫越生死、感人至深的境地。[5]
雖然麗娘從未離開過狹義的“亭”,可她對柳夢梅的想象,從來都不是第一人稱的幻想,柳夢梅是通過麗娘從不同的角度考察、想象才進入她的夢中的,才被她愛上的。柳夢梅身上洋溢著青春的力量,滿足了麗娘對于青春的渴望。同時,在作者湯顯祖所處的時代,家庭、事業與科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而柳夢梅又是一位即將上京科考的舉人,這說明他有著上進之心。而后柳夢梅得中狀元,也使杜柳二人的結合門當戶對、順理成章。雖然狹義的“亭”限制了杜麗娘的活動軌跡,但并沒有限制她的精神與思想,在麗娘的夢里,她依然可以馳騁在廣義的“亭”里,活動于這個被開放的空間之中。
三、結語
在《牡丹亭》中,杜麗娘的故事雖然未涉及飛升成仙的情節,但她的經歷卻充滿了超自然的元素。她的尸身在不腐的狀態下得到花神的庇護,她的靈魂在胡判官的幫助下得以重返人間,繼續追尋她的愛情。這種對死后生命的想象,以及對愛情超越生死的信念,體現了對生命和愛情的崇高追求。
湯顯祖在《牡丹亭》中通過唱詞和念白的交融,以及對空間環境的描繪,營造出一種夢幻般的氛圍,增強了故事的神秘感和超現實感。劇本中的這些元素,不僅增強了情節的玄幻感,也反映了作者對于愛情和生命力的頌揚。
在《牡丹亭》中,象征手法的運用豐富多樣,不僅體現在人物命運的轉折上,也蘊含在劇本的文學表達中。湯顯祖的“至情”理念,強調情感的自然流露和真摯表達,這一理念在劇本的象征性描寫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通過對《牡丹亭》中象征因素的探討與解析,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湯顯祖如何通過戲劇形式,表達對生命、愛情和自然情感的尊重和贊美。
參考文獻
[1]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駱蔓.論兩個“夢”意象構成的浪漫劇及其象征追求——《牡丹亭》與《仲夏夜之夢》比較[J].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03(03).
[3] 紀準.《牡丹亭》文字觀之二:生死[J].戲劇之家,2022(13).
[4] 湯顯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5] 李洋.《牡丹亭》與《長生殿》奇幻與現實結合手法比較[J].今古文創,2022(25).
(特約編輯 楊" 艷)
作者簡介:李雨時,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