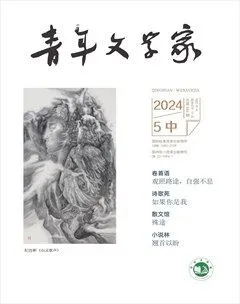所謂朋友
人這一生打交道最多的是朋友、熟人、敵人。經常見面,見面后忘記,是熟人;不經常見面,快樂和悲傷忍不住想告訴他,是朋友;想到他,緊張得握緊拳頭,是敵人。人的一生離不開朋友,離不開熟人,也離不開敵人的打擊。當然,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可以相互轉換的。熟人圈里的聲音是一樣的,志趣相近的人逐漸走近,能推心置腹的時候就成了朋友。朋友為了利益背后拆臺,互相競爭就成了敵人。敵人在競爭中欽佩對方的能力、氣度、個性,最后發展成朋友,也并不少見,這種關系形成的朋友往往比熟人形成的友誼更可靠。
李斯與韓非都曾受教于大師荀子,同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李斯以其政治抱負與才能得到秦王嬴政的賞識。不久,韓非寫的《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被秦王讀到,秦王對其極為贊賞。后來,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合謀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這是一個有名的由朋友發展成敵人的歷史故事。李斯、韓非均為聰明絕頂的人物。在那個人人想實現抱負與理想的時代,李斯從輔秦時看到了自己出頭的曙光。于是,為了獨邀功名利祿,李斯誣陷韓非、打擊韓非,假韓非思想為自己獲取功名的利器。“功夫不負有心人”,一日,他終于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秦國宰相。韓非在活著的時候是“郁郁澗底松”,很不得志。然而,人眼不明天眼亮。李斯也不得善終,被秦二世處以極刑,這一方面說明統治階級是冷酷無情的,另一方面也驗證了小人得志只得一時之志,作惡多了就會得到報應。相反,李斯對韓非的排擠打擊在某種程度上倒成全了韓非。若干年后,歷史還其公允之說。韓非成了與孔子、孟子齊名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而李斯仍然是李斯,后人大多只知道他曾為秦國宰相,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是荀子的學生,曾是法家思想的積極實踐者。韓非成就在千古之外,李斯成名于史冊之中,歷史是極其公平的。
在中國歷史上流傳最廣的友誼是劉、關、張的“桃園結義”,為了友誼歃血為盟,“同甘苦,共患難”“茍富貴,勿相忘”。“義”成為聯結他們友誼的最牢固的紐帶,并且成就了劉蜀政權。當然,也正是江湖狹義最終斷送了劉蜀政權。為朋友兩肋插刀,這是中國式朋友之間最常見的處事方式,這種義的狹隘性就在于他不是建立在公理與正義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小范圍的共同利益之上。“桃園結義”而成的友誼是黃金難買的,它可以一直穿透時空,照徹人類歷史。
遠離歷史和戰爭,現代人在生活中熟人多了,敵人少了,所謂的朋友也大多是熟人而已。說不定哪一天熟人中的一員就可能決定你的命運,于是,對熟人也一概稱為朋友,這種友誼大多限于飯局中。
做敵人要有資格,平庸的人一般不會有敵人,有敵人的人大多是在事業上、工作中處處占盡風頭的人,樹大招風,也容易招人嫉恨。敵人會明槍實火地真干,一般不會背后使絆子,背后使絆子的那是小人,他對誰都一樣。如周瑜與諸葛亮,那種你死我活的斗爭會形成敵人。他們斗的是勇氣、智慧、謀略,但他們從心底里都把對方當作有分量的對手看待,在某些原則問題上他們也可能驚人的相似。
朋友不多,這是現代人內心共同的感受,只是大家都不愿說出來而已。那種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友誼在現代社會缺乏土壤。許多時候,有共同利益的時候就是朋友,沒有共同利益的時候就是熟人,就是路人。友誼也像現代生活節奏一樣稍縱即逝—得勢時,門庭熱鬧;失勢時,門前冷落。這已是共性。那種像金剛鉆一樣的友誼我們只能從歷史的天空仰望。
“一次性”是個很流行的詞,同樣也適用于現代友誼。當然,“投之以桃,報之以李”這是朋友相處的基本原則,但那種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的友誼畢竟是極其脆弱的。于是,現代人常常所謂的朋友一大片,內心深處仍然是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