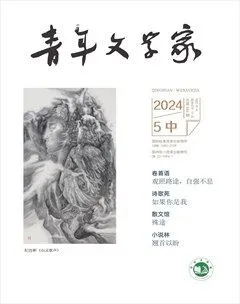逝去的時光
很久以前,因水清如鏡而得名的鑒江,從這座有著深厚歷史文化積淀的化州縣城中間浩浩蕩蕩奔流而過,將城區分為河東和河西兩大區域。河西是那個年代的主城區,也是我童年成長的搖籃。每當回憶起那段崢嶸歲月,我思緒飄飛,仿佛穿越了時空隧道,重拾那年那月那逝去的孩提時光。
20世紀50年代中期,惠南路西頭靠北邊那排居民屋都開有后門,與陵園路相接。街坊們關系融洽,一家有難,百家幫忙。我和小伙伴們在這些兩頭通的民宅中捉迷藏、打水仗,玩得不亦樂乎。走街串巷的郊區農民和小商販響亮的吆喝聲,此起彼伏,可以穿透一條街,抵達房屋的最深處。少頃,便有家庭主婦出來招呼農民進去,將家里平日儲放的尿液以一角到三角錢不等的價錢賣給農民做肥料種菜。也有老人家拿著爛鍋、廢鐵賣給收破爛兒小販。我也曾拿過牙膏殼換糖果。香甜的糖果味道彌漫著口腔,那感覺別提有多快樂。
盛夏季節,酷暑難耐。那年代沒有空調、電風扇。傍晚時分,街坊們便拿著一盆清水潑灑在自家門口的街道上降溫。華燈初上,一張張草席已鋪滿一條街。大人手里拿著大葵扇,為小孩兒扇風散熱,驅趕蚊蟲。街坊們互相交談,說著近來城里發生的新鮮事。一些調皮的小孩兒則在草席間嬉戲追逐。我躺在外婆身邊,仰望夜空,靜靜地聆聽著外婆講述牛郎織女、天狗食月、吳剛砍樹的天上故事。
縣城可供街坊們休閑游玩的地方屈指可數。大舅或是帶著我沿著凹凸不平的石青磚路,穿過江堤水閘門,到鑒江河里游泳;或是帶著我去河西大橋頭,觀看從河東那邊天際冉冉升起的旭日,享受江風吹拂;或是帶著我去解放路最南端的飛馬雕塑像前乘涼,敘說飛馬奔騰的神話故事。飛馬雕塑像是當時縣城的地標,提起飛馬,本地人都知道是指哪里。大舅偶爾會帶著我登上寶山,在烈士紀念碑前講述烈士為了祖國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英勇犧牲的事跡,熏陶我的心靈。寶山是城里最佳觀景點,整個城區可一覽無余。
在靠近羅江邊的中山公園里,有形態各異的假山石,古色古香的亭子,綠茵茵的草坪,遮天蔽日的大樹,散發著清香的鮮花,是人們最喜歡去的地方。
大舅經常領我去公園看假山的猴子,魚池中的金魚和關在籠子里的箭豬等動物。箭豬給我的印象最深刻,遇到人們走近時,它會立刻豎立棘刺,發出噗噗的響聲嚇唬路人,甚至抖動身上的刺像利箭一樣射出來。人們經常能在鐵籠外面撿到箭豬射出來的刺箭。
公園前面有兩個一大一小的湖,四周有石欄桿圍住,中間被一座石拱橋隔開。湖畔柳樹婆娑,婀娜多姿。絲絲細風掠過湖面,蕩起層層漣漪,甚是美麗。
公園瀕江處有一座望江亭,亭子左邊的城墻向著縣委那邊的清風樓延伸。滔滔的羅江水,沿著城墻下的江堤緩緩而過。亭子右邊是水上公社篷船停泊休憩之地。白天篷船在河里來往穿梭,拉貨物搞運輸。夕陽西下,篷船靠岸,勞碌了一天的船家人開始在狹窄的船尾甲板上生火做飯,炊煙裊裊,如絲如縷。夜色朦朧,密密麻麻的篷船煤油燈相繼點亮,似夜空若隱若現的繁星,倒映水中,醉美人間。
公園旁邊是一座兩層樓高的電影院。夜幕降臨,電影院門前人頭攢動,熙熙攘攘。等待第二場電影的街坊們會漫步電影院對面的中山公園,欣賞月光透過樹枝縫隙灑落在草地上的神秘光影和湖水閃爍著的迷離光澤。
后來,中山公園的大湖被填平做成了廣場,小湖被填平建起了燈光籃球場,中山公園被改建成了青少年宮。這里經常放映露天電影,舉辦籃球比賽,豐富了市民的文娛生活。如今,廣場被圍閉起來擬作他用。燈光籃球場變成了市民臨時停車場。
逝去的時光,消失的舊物,泯滅的景色,雖然一去不復返,卻永遠珍藏在老一輩街坊的記憶深處。舊城那質樸簡潔的氣息,仍彌漫縈繞著這塊生生不息的熱土,讓老一輩街坊們回味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