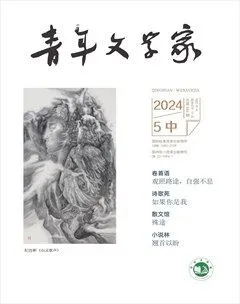故鄉的那縷炊煙
故鄉昔日的那縷炊煙,時常縈繞在我的心間和夢里,至今仍然清晰地在我的記憶里繚繞升起。
從我來到人間,第一次在襁褓里睜開眼睛,眼眸就親昵著故鄉幢幢屋頂上升騰的縷縷炊煙。
從蹣跚學步時,我總坐在自家屋門上癡迷地看著屋前屋后的鄰居家房屋頂上冒出的縷縷炊煙,看它慢慢悠悠、裊裊騰騰地升到一定高度,然后被同一風向的風糅合到一起,在山村的上空緩緩飄逸,逐漸成為淡淡的云彩飄向山外,飄向遠方。
到了上學的年齡,我邀約一群小伙伴在春夏晴日的清晨放牛、打豬草。走到偏高的山梁上時,我會坐著欣賞村莊里家家戶戶晨起的縷縷炊煙,看它與山間溝壑的霧氣攪和在一起,映著從地縫里新出升起的朝陽,云蒸霞蔚,色彩斑斕。一團團流動飄逸的彩霞,縈繞山間,繚繞山村的上空,形成一幅美麗的畫卷。
放學回家的下午,我和小伙伴們人手一把小柴刀,爬到高處的山岡上砍柴,坐在山梁的土包上,視野更加開闊。極目遠眺黃昏時的村寨,我發現山環水繞、縱橫交錯的溝壑深處的山梁上,到處繚繞著淡淡的炊煙被風揉成的煙團,被夕陽的晚霞燒紅了,像一團團滾動的彩霞飄向山外,飄向浩渺的天際。
近處,村子里的民居房屋繚繞的炊煙,在晚風里散發著淡淡的青菜、蘿卜、紅苕煮熟了的飯菜的香味,張開嘴巴吸一口夾帶素味飯菜的空氣,倍感醉人和享受!那一縷縷繚繞的炊煙從早晚升騰兩次,慢慢變成了一日早中晚升騰三次。空氣中由原來彌漫的清淡菜香慢慢變得濃郁起來,那是雞鴨魚肉的香味,令人食欲大開!
20世紀80年代中期,順應時代的發展變化潮流,我走出了山村,搏擊商海,沉浮江湖。1993年,受鄉書記鼓動,一同離職下海,復又重回商海,在商潮的沖擊下,離家越來越遠,遠離故鄉煙火。那時,家中還有一位遲暮的父親,但不管離家多遠,每年回鄉拜年和父親生日,兩次回鄉親近故鄉煙火。有時父親病了,要回家探視和看護,多一些機會領略故鄉煙火的芬芳。
久遠不回鄉,發現村莊里添了許多新樓房,添了許多煙火,故鄉的炊煙更為浩繁,色彩更為厚重濃艷!炊煙里散發的芳香更為濃烈和醉人。
自2007年起,父親身體衰老很快,身體機能失調,大小便時常便在身上。為了方便照顧,我把父親帶到深圳,在那里住了半年,可父親天天吵著要回家,我以為是我們照顧不周,引起老人反感,我跟父親進行了細致的溝通,他說:“不是你們照顧不好,是我覺得在這里生活不習慣。這里的天氣比老家熱多了,吸一口空氣都難以咽下喉嚨。這里的水也很難喝,盡管你們想盡辦法為我準備飯菜,可就是做不出家鄉的味道。家鄉的空氣吸一口是帶有清新甜味的,喝的水也是甜的,飯菜也是有煙火味特有的味道。我要回去,不愿在這里。”我只好請幫工為我做生意,回家陪伴父親最后一程。
10月,父親去了天國找我久違的母親了。從此,我回鄉的次數就少了。雖然回鄉的次數少了,但兄弟姐妹、外甥侄輩們依然惦念著我,故鄉的煙火也時刻縈繞在我的心間。
俗話說:“想致富,先修路。”隨著形勢發展變化的快速節奏,村民們開始自發組織籌款修公路,在外人員捐款集資修路,我也熱烈響應,捐了款。到2015年,大部分鄉村公路通車,故鄉的公路也通到村組、民戶。家家戶戶都有了交通工具,交通便利,回家方便了。家鄉的每家每戶都用上了家用電器,也沒人再上山砍柴了。封山育林讓林木掩蔽在茂密的雜樹里,成了原始森林,林木之間行距分明,雜草不生,不像從前的林區那般。
如今,回到家鄉,再也看不到家鄉的煙火,沒有了昔日的裊裊炊煙,再也聞不到家鄉的煙火香味,再也看不到煙騰繚繞、云蒸霞蔚的美麗景象了。但兒時鐫刻在心間的鄉村炊煙繚繞的美麗畫卷,仍然在記憶里裊裊升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