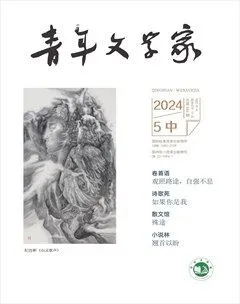我的初戀
人生,也許都有一段不同尋常的初戀,或是刻骨銘心,念念不忘;或是花前月下,喜地歡天;或是平淡無奇,一訂終身……
我的初戀并不出彩,但隨著歲月的延伸,卻留下難以忘懷的記憶。而這種記憶,與某一觸點碰撞時,會愈加強烈。
我很喜歡聆聽小提琴演奏曲《梁祝》中的“十八相送”。每每聽著這首曲子,眼里便含著辛酸的淚珠。只因在我青春時期,有一段與“十八相送”相仿的初戀經歷。
當年,我正青春,任職于駐湘某軍事單位。因執行一項任務,被指派到某軍工企業搞調研。由于工作需要,與該單位一位年輕靚麗的女秘書萍兒(化名)經常交流工作情況。她不僅外表漂亮,而且聰慧精干。這一來二往,我們從彼此略有好感轉化為愛慕之戀。
人類的情感也許是最豐富的,何況是一對未婚的男女青年。她經常利用休息時間,邀我到附近的湘江邊和山野游玩。湘江邊那張用石頭壘成的石椅,成了我倆促膝暢談人生的天然寶地。她總讓我靠近她一點兒,但我還是保持著一定距離。那個年代,可不像如今這么開放,而且我還有較嚴格的約束紀律。她看我不像一般男子,見到年輕女子就腿軟,更認為我是一個可依托終身的人。附近的曠地長滿野花,她便摘下幾朵插在自己的兩條小辮上,問我:“好不好看?”我隨口回答:“好看。”她又告訴我,其實,她最喜歡的是紫羅蘭,因它是希臘神話中,女神維納斯淚珠的結晶,代表著永恒的美與愛。她是家中的獨女,父母年老多病,希望她能在當地成家立業,以便照顧。我便附和著說:“對呀,應該的。”她話鋒一轉,問我能否與她組成家庭,并留在當地工作。我一時無法應答。雖然我也很喜歡她,但這畢竟是婚姻大事,且又要我永遠留在當地工作,必須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行。
事后,我寫信給父母說明這一戀情,父母卻堅決反對,而且他們還在家鄉托人為我物色了對象。當我把這一情況婉轉告訴萍兒時,她難過得流下了淚水,問我:“我是不是長得丑?”我說:“怎么會丑呢,在我心中你是最美的。”她又說:“那永遠留在當地工作,也只是嘴巴說說而已,真成了家,還不是要隨夫而行。”我說:“那樣又違背了你父母的心愿。”她低頭不語,淚水滴在臉上。
幾個月的調查工作基本結束,我就要返回自己單位了。萍兒得知后,就像丟了魂兒一樣,依依不舍,又特意為我準備了土特產,盼望我能再來。
當年中秋節前,她專程到我單位探望。我所在部門領導的妻子,把她當成我的戀愛對象,熱情款待,還將她留在家中住了一宿,第二天她走時,還特意送禮物給她。部門的領導也吩咐我,要送她到公交車站。她看我部門領導和其妻子對她這么盛情,愛意越發洶涌。在送她到公交車站的路上,突然,她開口表白,一定要跟著我,無論天南海北。我不知所措,隨口說出:“我們可以成為好朋友啊,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更優秀的人。”她瞬間淚如泉涌,嗚咽不斷,用沙啞的聲音說:“我都把整個心交給你了,哪兒還有再找別人的心思呢?”我一時不敢作聲。
當到達公交車站時,她又不愿與我道別,執意要我再步行送她到火車站。哎呀,那可是六七公里的路程。看天色已是傍晚,我也不好推托,便繼續與她同行去火車站。
一路上,她緊緊牽著我的手,想從中得到絲絲的溫暖。這也是我們相識以來的第一次牽手同行。她臉上現出喜悅的紅云,不時還故意碰我一下。途經一座大魚塘時,她看見成雙成對的鴨子在嬉戲,忙讓我停下來看看。她戲說我就是那只棕色呆頭鴨,我說她是那只白毛的調皮小鴨,她高興地發出爽朗的笑聲。途經湘江大橋時,她見江里一漁夫正在撒網捕魚,便嬉笑著說我也是漁夫,她是可憐的魚兒。我會意她的心緒,笑而不答。
這一段路,我倆足足走了近兩個小時。當我送她上火車后,她緊緊貼著玻璃車窗看我,辛酸的淚水在眼珠里打轉。我的眼里,也含著淚珠。真可謂“相見時難別亦難”。
沒過多久,她知道我準備結婚了,獨自哭成淚人,幾天不吃什么東西。我知道后,感到很慚愧,急忙寫信安慰。
歲月悠悠,又過了近一年,聽說她在當地草草地找了一個人,成了婚。從此,一個天真活潑的人變得沉默寡言。
不知不覺,又是幾年。我后來才知道她到醫院檢查時,確診了絕癥,不久便郁郁而終,留下一個沒有母親的小女兒。當時,我真是心如刀割,非常愧疚。這不是因我而鑄就的人生悲劇嗎?我特意領受任務,再次到其單位公干,專程到我與她生前常去的附近湘江灘頭,望著奔流而去的江水發呆,仿佛又看到她那美麗可愛、戲水歡歌的模樣。
從此以后,每逢清明節期間,我都會買上一束紫羅蘭,到附近江邊祈禱,愿她在天堂再無病痛與悲傷。為悼念她,我還特意寫下詩歌《你在哪里》和《情殤》。
我常常癡情地想,假如人生真有來世,我不會再讓她難過。望著茫茫夜空,情傷之痛躍于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