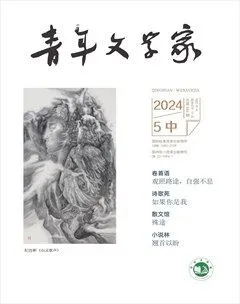淺析袁枚《小倉山房尺牘》中的“說話”藝術
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左氏傳》寫道:“《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以三尺長簡書律法,是簡帛時代公文例行的通則,而書信則常寫于一尺短簡之上,故又稱“尺牘”。如此,尺牘之重要性自然無法與法律條文相提并論,但也正是基于此,形成了尺牘自由灑脫、不拘一格的寫作風格,作為親友、同僚之間交互的媒介,往往能更鮮明地展現書者的性格和語言風格,更真實地傳達筆者的“說話”藝術。
一、《小倉山房尺牘》的成書及版本
(一)成書
在袁枚看來,尺牘是“古文之余唾”,其所為尺牘,隨作隨棄,故此時袁枚尚未有成體系的尺牘集。直到鹽商洪錫豫,他對文章也頗有見解,發現了袁枚尺牘的過人之處并贊嘆道:“讀之意趣橫生,殊勝蘇、黃小品;且其中論政、論古、論文學極有關系,在他人必闌入正集矣。”他進而對袁枚嚴格劃分古文界限而舍棄尺牘的行為進行辯駁,為袁枚尺牘的留存傳世尋求可能性,“先生以四六為《外集》,其嚴畫古文界限之意,業已了然。尺牘每況愈下,豫豈不知……今先生既以嚴且潔者示人,而不以不嚴不潔者示人,則學者又何由知古文與尺牘所由判別之故哉”,以尺牘與古文作對比,便能更鮮明地展現出古文的規范;同時,尺牘作品也得以保存下來。經此一言,洪錫豫終于獲得了袁枚的首肯,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前后刊刻了《小倉山房尺牘》,初刻本共六卷,此后又陸續增刻至十卷。
(二)版本
《小倉山房尺牘》早期主要版本有乾隆、嘉慶間刻《隨園三十種》本,同治五年(1866)三讓睦記刻《隨園三十種》本,光緒十八年(1892)勤裕堂排印《隨園三十八種》本等。晚清以來,《小倉山房尺牘》又相繼出現了眾多選本與注本,包括胡光斗《音注小倉山房尺牘》八卷,有咸豐九年(1859)青蘿室刻本、光緒四年(1878)蘭言書屋刻本、光緒中申報館排印《申報館叢書》本等;陳名金《小倉山房尺牘詳注》六卷,有同治二年(1876)文光堂刻本;馬步元《小倉山房尺牘輯注》十卷,有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虞山猶龍子《增廣詳注言文對照小倉山房尺牘》四卷,有“民國”十七年(1928)中西書局石印本;章榮《廣注語譯小倉山房尺牘》八卷,有“民國”二十五年(1936)世界書局鉛印本;等等。“民國”時期甚至還出現了徐楨在胡光斗原注基礎上增注的《新體廣注小倉山房尺牘》八卷,有“民國”八年(1919)上海廣文書局鉛印本等多種版本。
二、《小倉山房尺牘》的“說話”藝術
尺牘作為親友、同僚之間交流的工具,不必嚴格按照詔書一類文體,行文嚴謹、措辭考究,而往往自然流暢地展現出書者的“說話”藝術。袁枚《小倉山房尺牘》的“說話”藝術主要體現在“致上陳情”“彰顯性靈”的場合下,袁枚總是仗義相助,或幫人舉薦,或替人求情,“說話”毫無“急功近利”之痕跡,卻往往能達成目的。
(一)致上陳情
袁枚在任縣令期間就表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且其人才華橫溢、公正嚴明、愛民如子,的確是可以委以重任的好官,可惜袁枚這一生為官都不順利,初入仕途時期,袁枚一直被上級器重,卻只能做一介小小縣令,輾轉于百姓的日常矛盾之間,空有一身本領卻無用武之地。至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袁枚曾獲悉有補高郵州知州位的機會,他以為自己終于能夠躍上一層平臺,展示自己的才華和滿腔抱負,卻又事與愿違,最后落空,至此,袁枚遂有了退出仕途的想法。經此幾番,袁枚最能知曉人才不被賞識的失意落寞之感,加之他為人清明豁達、慧眼獨到、賞識才俊、仗義率性,故此,他常常動用自己的人脈,向仍居廟堂的舊友或親人舉薦自己看重的人才及門人弟子,或為貧困子弟請求資助。
1.上拜請愿,環環相扣
袁枚在替后生尋請資助時,十分注重說話的分寸,極盡恭敬謙遜,卻又不卑不亢,絕無低微之態,他往往會說明后生目前所處境況之無奈,通情達理地表示希望而不強人所難。當然在面對不同的準資助人時,袁枚也會轉換不同的說話方式,在對朋友時,他的方式是通情達理、陳陳相因;當面對親友時,他的陳辭中又增添了幾分無奈與懇切。在《與盧雅雨轉運》一文開篇,袁枚率先提及了二人之前在隨園時相談甚歡的風雅樂事,追憶了二人的深厚情誼,這也在為下文的請求之語作鋪墊,希望盧見曾(字雅雨)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不要駁了自己的面子。隨后,他又從為官、選才、文學等方方面面稱贊了盧見曾的品德、能力、眼光、才華與堅韌。第二段袁枚才開始正式切入正題,說陳毅是在盧的賞識幫助下才成了家,但成家以后人口漸增,自然所負供給生活的壓力也隨之增加:“陳生古愚,因受知于先生,而有其室家;因有其室家,而轉增食口。良醫治人,原不能十全為上也。然恩始恩終,大君子必無厭色。喜渠食指無多,桶中之妻,尚易畜養。古語云:‘賑饑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于規行。’茲來晉謁,祈進之前席而洗其寒酸,幸甚!”這是袁枚轉述境況之語,如此說來便合情合理、扣人心弦。緊接著,袁枚并沒有直說資助陳毅一事,而是繞了個彎子,對盧見曾表示體諒,自言郎中治病救人尚且不能圓滿,但若君子施恩之行,定是勝過治病救人的福澤善事,有始有終才是君子之道,想必先生也不會厭煩拒絕的。此處袁枚就已經給盧見曾設了一個陷阱,讓他不好意思拒絕。袁枚步步緊逼,接著又說陳家所求不多,尚且好養活,先生救人于危難之際,不必顧慮許多,少許錢財便可解這一家的“涸轍”之困,所以還請先生能夠幫幫他們。經袁枚這么一番闡釋,資助陳毅倒成了一樁不難辦的小事。袁枚寥寥幾句下來,說得是滴水不漏,讓盧見曾沒有拒絕還口的余地,還給盧見曾的臉上添了光彩。
2.舉薦才俊,直言不諱
袁枚引薦才俊不受條件限制,即便是素昧平生的才俊對他有所請求,他也會為之欣然修書,如伯樂相馬一般將他舉薦給自己的故交,不讓其聰穎才華白白浪費。在《與帥璞山刺史》中,袁枚與潘生素無交往,甚至潘生的詩文也并不規范,不符合著書立說的要求。潘生也是因為計劃落空才在窘迫不已的情況下投奔袁枚的。嚴格來講,潘生是不夠資格被舉薦的,但袁枚恰恰看重潘生是有志之士便愿意舉薦潘生,可見袁枚對人才的看重和仗義豁達。接著,袁枚也給帥家相設計了一個圈套,說自己害怕南京官職均滿,尚未有可補的職位,但湊巧潘生家鄉就在您的屬地廣德州,您德高望重,一定能幫助潘生有所成就。一個轉折就讓帥刺史不好再開口拒絕了。
(二)彰顯性靈
袁枚所提倡的“性靈”包含“性情”與“靈機”兩個部分,“性情”是“性靈說”的基本要義,強調個性的彰顯、性情的張揚和自然本性的流露,《小倉山房尺牘》中袁枚彰顯“性情”的作品多是展現他深明大義、直言不諱的仗義之舉,袁枚見義勇為,絕不是快刀斬亂麻式地解決問題,而恰恰是運用“說話”的藝術周全各方。
1.比喻新穎,灑脫率真
袁枚的“說話”藝術不僅表現在他舉薦后生上,也表現在他仗義執言的處事方式上。在《乞上元令李竹溪釋枷犯》一文中,袁枚見到一俊美少年郎被縛枷鎖,心生憐憫與惋惜之情,詢問得知是因賭博而被捕,便仗義執言,替美少年求情:“天性好賭,自古有之。王侯將相且然矣,況里巷子弟乎?且造物雖巧,生人易,生美人難。談何容易,于千萬人中,布置眉目,略略妥當,而地方官不護惜之,反學牛羊,從而踐踏之,忍乎哉?”袁枚稱王侯將相的門戶里尚且有賭博成癮的子弟,又何況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呢?這一理由倒是無可厚非,但袁枚替少年郎求情的另一個理由就讓人哭笑不得了,他以為,少年郎生得俊美,這在天機造物的蕓蕓眾生里實屬不易,萬不可像對待牛羊一樣踐踏了這份美貌,能說出這番癡人癡語,足見袁枚不拘小節,他放浪形骸又率真灑脫,卻也勸得了李縣令放走了少年郎。
2.兩歧之語,緩和氣氛
袁枚也善用“兩歧語”說理解難,能夠有理有據地緩解矛盾雙方的尷尬,使人信服。在《答唐靜涵問坐位》一文中,袁枚便明白曉暢地對問題作了解答,宴席之上,彭大司馬坐在了朱觀察之上的位置,惹得朱觀察甚為不滿,托唐靜涵向袁枚寄信詢問孰是孰非,袁枚則認為二者皆各有理由上座:“朱所執者,《孟子》‘鄉黨莫如齒’一言;彭所執者,《王制》‘一命齒于鄉里,二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之義也。彭官一品,是三命矣,于父族尚不齒,而況于鄉里乎?”朱觀察所執的理由語出自《孟子·公孫丑下》,意即:在鄉里,是按照年齡分尊卑的,可見朱觀察的年齡是要高于彭大司馬的;而彭大司馬所執的理由實則語出自《周禮·地官·黨正》,而非《王制》,意即:一命的官要與鄉里眾賓按年齡序尊卑,二命的官要與本族眾賓按年齡序尊卑,三命的官就不與眾賓按年齡序尊卑了。那么彭大司馬官居一品,是三命的官階,尚不與父族按年齡序尊卑了,又何況是與鄉里呢!朱觀察按年齡定座位,彭大司馬按官階定座位,于二人而言都是合乎情理的,袁枚雖以“兩歧語”為二人作了合理的解釋,但其實孰是孰非已經明了于心了,彭大司馬自然無需與朱觀察按年齡定座位,按照官階,彭大司馬上座才是合乎禮法的。只是袁枚的一番解釋,緩和了二人的矛盾,同時也保全了雙方的美名:如此看來,朱觀察倒也有理有據,并非故意為難;而彭大司馬縱然官階三命,卻仍禮讓鄉里,德高望重。
3.清麗雅言,韻味無窮
袁枚用語從不過分藻飾,卻總能用平淡的文字彰顯出清雅別致的獨特韻味。在寫回復尹繼善的《答兩江制府尹公》這封信時,適值袁枚久病初愈,身體雖然見好但仍很虛弱。信中便有“適窗前有綠梅一株,水仙數種;對之展讀,正與古香冷艷,同入襟懷”一語,寥寥幾字,并無綺麗華美之語,但使人讀來卻有微風徐徐、梅香幽幽之感,平添了一絲淡雅清新。其以“綠梅一株”“水仙數種”立于窗前的畫面,勾勒出一幅對窗展讀的圖景,營造出一種清雅的氛圍,此情此景,花香縈繞,佳句在心,怎能不令人心旌搖蕩、暢快自得?袁枚在此也向尹公暗示自己懶怠俗務,只想退隱隨園,經營吟詩頌文的清閑生活。在《與史抑堂少司馬》一文中,袁枚稱頌袁史兩家聯姻實乃天定良緣時還提及隨園內所植的三株紫薇花:“園中植紫薇三株,十易星霜,從無蓓蕾,今年盛開,爛如云錦,或者薇省呈祥,應在將來甥館乎?”袁枚并未直接袒露自己的喜悅心情,只道園中的三株紫薇花十年未曾開花,怎料今朝兩姓聯姻之時花團錦簇、燦爛盛放,且紫薇花本就“紫薇省”同名,寓意頗佳,不禁讓人聯想到女婿品行俱佳所得天降祥瑞,由此想來,讓人喜不自勝。這番花團錦簇的絢爛之景,亦得于十載披星戴月、歷經霜雪的沉淀,文字里是歲月積淀的清麗典雅,卻蘊含著喜上加喜的熱烈和共逢良緣的喜悅之情。在《與鄭時慶太守》一文中,為向太守舉薦潘生,袁枚特提及潘生的文章,形容其為“若春波之漾落花,流風之舞回雪”,雖未親自品讀潘生的文章,但在袁枚的描繪之下,便感覺那些文字就如同清溪一般緩緩流入心間,夾雜著落花的芬芳,沁人心脾;又好似微風徐徐,夾雜著雪花浮蕩心靈,使人覺得溫婉清新。清雅別致的意境,在袁枚的寥寥數語間便顯現了。
袁枚是清中期的一位文壇大家,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在散文領域取得杰出成績的同時,其尺牘也有著獨特的價值,在中國尺牘史上熠熠生輝。袁枚尺牘結合了古文與駢文的優勢,意蘊精深且觀賞性強。在清中期,科舉制度推崇下的八股之風盛行,加之以桐城派為首的古文風氣影響,尺牘已然呈現出衰落之態,其發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袁枚本身雖推崇古文,對尺牘尚且不是十分重視,但在這一時期,他將自己的卓越才華、高雅意趣和獨到見解傾注于尺牘,創作出了個性鮮明、風格獨特的尺牘作品,扛起了清中葉文壇尺牘文學的一面大旗。一方面,袁枚在尺牘創作中不拘小節、揮灑自如,使其尺牘充斥著率性純真與繾綣真情;另一方面,袁枚才華橫溢,在尺牘中引經據典、喻事說理,使其尺牘作品自然活潑而典雅厚重。袁枚憑一己之力將尺牘又推向了另一個高峰。袁枚在尺牘創作上的成就,值得我們關注并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