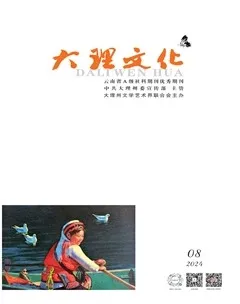靜鄉心語


走" 讀
一個人走過村莊,腳下的每一步,每一處停留的目光,都凝結著我的記憶與遐想。村莊如此靜謐,所有的美好都恣意鋪灑在這片土地上。
除夕午后,天有些放晴,接連幾天的濕雨陰霾,漸漸散去。母親和媳婦在準備年夜飯,父親干些雜活。我貼了春聯,看看也幫不上什么忙,就獨自下嶺,往村莊和田野深處走去——這是我第一次如此慷慨地貼近村莊。
嶺下是村委大樓、村史館、法治廣場,以及黨建、非遺文化和鄉賢教育于一體的鄉風民俗苑。一路見民俗民風墻,以及村民門前的對聯、紅燈籠和停著的小車。年味漸濃,不大的村莊,迎來了難得的人氣。
“后巖”,一個厚實剛氣的村名。這個500多人的小村莊,背靠敦實厚重的鳳凰群山,一灣后溪清流環繞村莊,面對著北上抗日先遣隊分水之戰的金紫山。一環溪壩,一陌村道,一架石橋,如同一張拉滿的弓。我熟悉這里,又似乎有些陌生。我試圖用腳步丈量,想更清晰地感知這里的一切,觸摸村莊的脊背、身軀和靈魂。
后溪河壩,從百歲坊王家塢口,一直通往三槐村,似一輪圓月彎刀,把后巖村三面環水的輪廓,勾勒得分外清晰。我一直想從村頭到村尾走一遍,將自己整個的身心,在某個瞬間,和草木、泥土、莊稼及村莊定格。除夕之日,終于成行。
橋頭是入村門戶,金紫山下的這座橋,恰似將村莊兩段勾連延展,下一段,蜿蜒至三槐,與天目溪相接。這里鋪滿了兒時的記憶。正月里拜年,沿著山溪邊小道,經云頭、西華、賀州、上岙、樂平,去往外婆家。有一次放假,我挑著兩把小竹椅,外婆拎著幾只竹籃子,一路沿村叫賣。
“竹椅哪個做的?”
“我父親。”
做篾匠的父親小有名聲,圍過來的路人也不說破,稱我乖巧、調皮。那段憨厚可愛又能吃苦的記憶,與外婆走村串巷,相依相伴的生動影像,讓人唏噓感喟。
河壩底下,我家的那二畝四分田,到底是哪一塊,只有大致的印象罷了。小村莊,背靠山,但多貧瘠。所有生計都在鳳凰山與后溪之間的一大片開闊水田里。
雙搶季,各家忙各家的,無暇幫工。一家四口,頂著熱辣的太陽,踩著火燙的泥水,比著速度:割稻,一路向前;插秧,一路后退。熱血沸騰的年代,村莊里最熱辣的一幕,終將在這里封存。后來,父親開墾的那塊沙地,也在這河壩下。回想辣椒當季的四月,戴著涼帽的母親,筐了一車的青辣椒、紅辣椒。我和媳婦在眼花繚亂的辣椒地里,手不擇路,分享著果蔬鮮嫩的喜悅。
我不再多想,我選擇往上段走,這里有我小時候放鴨躲雨的大樹,跳水摸石洗澡的溪岸,還有炸魚網魚的大河灘。歲月有些久遠,但拾擷一二,自有一份歡喜之心。
斑駁的石欄桿,一地的荒草綠苔,紛落的枝干碎葉,片刻間凝固成冬日清冷孤寂的畫面,隱約地折射出村莊寂寥的面目。但我并不傷感,眼前的一切,皆是現實中的真實,是這片土地真實的模樣,對于一個本土本村的中年人而言,既陌生,又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幽靜中,我一個人消融在無邊的山野里。
那幾棵大樹,枝葉雜亂地纏繞在一起,幾乎倒垂于水面,紛擾中自有沉浸。讓人驚喜的是,有一群鴨子,正從樹隙間,迅速向對岸游去,一晃,視線就被阻隔了。我竟然有些恍惚,五歲開始放鴨的經歷,機耕路、鋼筋橋,緩緩流動的清澈河流,河里晃悠著身子異常活躍的鴨群,瞬間如電影蒙太奇般浮現。
我坐在堤壩邊的石頭上,茫然若失。佇立在岸邊的那些樹,枝干正張牙舞爪地伸向天空,遠沒有少年時爬上去玩耍的那般喜愛。小片竹林和幾壟剪過的桑樹,和掛著幾串紅燈籠的菜地,成了堤壩外獨有寂寞的風景。
一路向西,北望山崗。
連綿的山頭,曾是我爬過的高地。兒時,特別到下半年,我們都要跟著父母上山砍柴。天未亮,就手拿柴刀、肩扛扁擔,翻過家北面的鳳凰峰,進入山背深處,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挑著柴火回家。一擔擔的柴火,從山頂山腰間挑下來,壓實了少年略顯瘦弱的肩膀。山上挑回家的柴,父親分門別類,將粗大的劈好整齊碼于檐下,自然風干。細小的捆成小捆,也整齊置于大柴邊上。
那些彎曲不平的山道,濕了又干了的汗漬和毫不猶豫堅實的腳步,印證了村莊生生不息的人間煙火。
田野里有一排栗子林。七八棵栗子樹,齊整地立在田埂的兩邊,頗有章法和氣勢。散落的黃葉和田里的青菜,勾勒出青黃相間的田園山水畫,這畫里有青色的底色和合理的留白。村莊的鄉野氣息撲面而來,不得不說,看到這樣的景色,我的內心是歡喜的。
未到柏油路的盡頭,突然聽到了陣陣巨大聲響。我料定是上村口河水的轟鳴聲。溪河勝景近在咫尺,萬千美妙觸手可及。
果然。眼前是一幀堪稱完美的冬日溪流圖,背景是層巒疊嶂的群山,山野清朗。遍地清流,氤氳出悠遠、空靈的意境。兩層闊大的堤壩,形成白花花的水勢,在溪流和山道邊肆意橫貫、傾瀉。山道邊的水流回返,濺起清澈的水花。與堤壩間排山倒海般的水流,迅速集結,奔涌而出。沖刷之下,水汽升騰,瞬間白霧彌漫。
留意于物往往成趣。我耐著性子,坐在一塊石頭上,靜靜地聆聽著這自然間最純粹最美妙的聲音,我感到了無與倫比的暢快——上善若水,“臨清流以洗心”,老家的這一方水土,徹底洗滌了我的濁心。
我蹲下身子,撫摸那些略顯黝黑的鵝卵石,它們在水里愈發得潤澤生動,可以看到堅硬之外的靈性。自然之物總是貯藏著一些野趣,伴隨自然之力而落于荒野僻郊。我下到最低處,用手掬一口水,喉間瞬間沁涼沁涼的。我忍不住拍起視頻,“我在老家后巖……”我竟然情不自禁地解說著,有些語無倫次,但卻很真實,情感抒發毫不掩飾。獨處的這一刻,在村莊的河流里,我享受著自然帶來的清澈和奇妙。
往村莊人家走,抬眼可見曬著的腌肉、魚干和蘿卜條等年貨。遠遠看見一個熟人,是小學許老師的女兒,她坐在門邊剝筍。我過去打招呼,剛好許老師從村舍邊過來,他遞煙給我,我說:“不抽。”他說:“你不是抽的。”我說:“喝酒高興了搞一支,空的時候喝杯酒。”“他笑笑說:“好啊。”他喜歡喝酒,而且充滿著豪氣。
山居鄰里安寧互助,雞犬相聞習慣往來,日子就悄悄地過去。我告辭,往村里走。一排排民居點,依稀記得這是發小敏芳家,這是胡培松院士家,那家是供電所李家兄弟,小廣場邊是臨安“云相見”民宿鄭李方家……季節里,天有些涼了,“搗蛋精靈農樂園”里的栗子樹,正一片一片,寂寞地落著葉子。
“回家。”一個聲音徐徐響起,在蒼穹之下,大野之上,清流之畔。我往家里走,內心平靜而充實。
夜" 讀
天色還不算太晚。車燈忽閃,正緩慢拐過街角;江面上,霧氣灰蒙,水灘淺擱;駛往鄉村的路,略窄又彎轉——冬日的蕭瑟在山林與溪河間彌漫,讓人愈發覺得寂寞與孤單。
在像回老家這類的問題上,我從來都有自己的主意,因為即使像這么簡單的事情,也是需要執著的,須放得下一些東西。阿慶嫂在這個問題上從來不會爭論,最多先打個電話,順便問一句吃不吃飯。
因為下午四點左右,兩個人都覺得餓,女人就下廚,燒了鍋青菜年糕湯。眼下飽著,就不覺得時間的早晚,而母親的電話終究過來了,“飯燒好了,要來的嗎?”催促的聲音里,夾雜著幾分平和,然后又立馬說,“等你們吃飯了。”或許,在每一個母親的心里,子女的到來,比什么都重要。
“哪里吃得下去?”女人把著方向盤,朝我笑了一笑,又補了一句,“吃,其實無所謂的。”她也不小了,懂得一些人之常情。
過了橋,天色愈發黑了,大半個天空像是黑夜,村莊黑漆漆一片。上了嶺,家門口也是,菜園地里也沒有一絲光亮。估摸著,雞已歸籠,父母親坐在飯桌旁,正等著我們了。內心最迫切的,往往是等待。
“門口燈都不開……”我伸手去按,“有人來,太黑了。”這話也沒傳到老人的耳朵里,他們一定已經習慣了,這些鄉村里習以為常的東西,墨守也好,成規也罷,不會太在乎。
一只火鍋——腌肉冬筍燉著,桌子底下生著炭火;三盤菜——農家菜埠頭、肉骨頭燉芋艿、辣椒肉丁炒豆角干,家常而已;四只杯子——父親照例滿上,母親自倒一半,我喝點啤酒,阿慶嫂開車,倒杯白開水。
無數個這樣的夜晚,在村莊深處,我們和父母,提酒,碰杯,說話。
“兩個孫女好的,懂事體貼的,都打電話來,說不要太辛苦,種點菜自己吃吃就好了,好大年紀了……”母親說著,看上去很欣慰,接著又說:“是啊,少種點,是要歇歇力了。”
“明年不種太多,但芋艿要種點,今年價格實在好。”父親有自己的堅持,不過他又說,“年紀大,不相干了,但是人情世故多,做還是要做的;真正做不動,會問你們拿的。”
我們互相碰杯——我的父親母親,杯里是酒,眼里都是看得見的幸福。
“少種點,空了就做點篾活,就好了,這個年紀,人家都吃完飯,走走路了。”
關于年齡與干活的話題,我們曾不止一次談及,而什么時候懂得饒過自己,對于勞累了一輩子的人來說,又是如此得不易,像極了兩根難啃的骨頭,而我的父母尤是。
“再加一點,”父親咂了口酒,“你們來,高興!”這個時候,父親的心里,多少放下了一些東西——他說的是實話,我們懂。
“鍋巴軟了,你們來得太遲了。”母親突然想起。惦記這一口松脆,吃不上,也只能怪我們自己。“我去添把火,放點豬油……”母親放下筷子。
吃完鍋巴,我笑著對老頭子說,“這些新椅子新籃子,我幫你宣傳一下。”過去拍照,以便帶貨上傳朋友圈。父親起早上小鎮賣菜,順便也搭些篾器,他的篾器,做工、品相都不錯,在附近村鎮,都小有名氣。
父親顧自喝著酒,吃著菜。他把喝酒當休息,這是老人一天里最愜意的時光。
“哦,路燈開了,我總要忘記的。”母親拿著一包土雞蛋,送我們到門口,每一次,她都會看著車下了嶺才回屋,繼續陪父親喝一點,再收拾收拾,然后洗漱睡下,她習慣了。
我也習慣了老家的景致:家門口的菜園地,季節里的時蔬,勾連著鄉村與城鎮里的日常與情感,或許遠不止這些。而此刻我腳下的這片土地,還有著最初的山川、田野和溪流。夜晚,這里很靜,走過幾家,隱約有燈火暖著;晨起,幾縷炊煙,從山坳竹林間裊裊而起,后溪的河面,也升騰起薄薄的霧氣。
陸續有人上工了,三輪車突突在機耕路上。田地里除草,季節性播種,施肥灌溉,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各有各的歸處,好似散落在坡地上的栗子樹,始終與土地相守。
而白天的熱鬧遠不止這些,一批批慕名而來的參觀者,驚嘆于這里。“鄉村,讓城市更向往”的自信,在從這里走出去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稻研究所所長胡培松的助力下,后巖人的“稻香共富夢”充滿著希望的魅力。小村莊,已然蛻化成蝶。
有人來,鄉村是活著的;有那么多人來,意味著鄉村活得好好的。而我有幸,見證著這里的一切,鮮活的鄉土中國,無論是白天的熱鬧,還是黑夜中的守護。
車過橋,遠去的鄉村漸趨沉默,正如夜,深沉如初。
舍" 離
車子駛出石橋,就出村了,那是整個村莊和田野都寂靜得出奇的初冬午后。
后備箱里,裝滿了母親為我們準備的土貨,一些時鮮蔬菜,嫩黃的生菜、嫩綠的香菜、青辣椒紅辣椒、扁長的梅豆、毛須須的芋艿、白皮的大冬瓜,還有兩只腰身修長的老南瓜和一大袋土雞蛋,這些村莊和土地給予的激動人心的東西,使我的每一次造訪,變得如此輕松愉悅。
我和阿慶嫂是中午飯點到家的,我從側門進去,見父親一個人坐在小灶間喝酒,這里空間緊致,稍暖和些。阿慶嫂從正門進去,母親正好在客廳嗑南瓜子,看《大俠霍元甲》。這情景,似曾相似,又覺意外。通常是,父親給母親倒半杯酒,他自己滿上,說說話,家長里短,田間地頭之類,在我們面前,還免不了爭幾句。母親給父親盛小半碗飯,再慢慢收拾一下,一餐就過去了,人也歇了。一天兩餐,據兩位老人自己講,750毫升的雪碧瓶,兩人對著喝,兩天就光了,不緊吃。檢查個身體,一個箭頭也沒有。
父親回老家生計,一晃也十幾年了,種地種菜,起早去菜場蹲賣,用他老人家的話說,叫“地里摸幾個”。另外他還做點篾匠活——他的老本行,竹凳、米篩、竹簍之類,掙點辛苦銅板,倒也自在。他也不服老,靠辛苦掙的幾兩碎銀,我再湊點裝修費,把新房子搭起來,算是老有所居,在村里也光鮮。算起來,這是父親起的第五回屋了,白手起家,做做篾匠,吃百家飯,這些年不容易。眼下,他蹲守老家,身心愈發安定。體檢單上沒有一個箭頭,我們也放心。除了心里計算著我們回家的日子,酒一高興,偶爾也會和兩個孫女視頻一下。
眼前是拐彎的公路,沿著一個又一個村莊與河流,一直通向小鎮。我看見路邊有個身材高大的女人,手里拎著紅色尼龍袋之類的東西,大包小包的,左顧右盼,正在等車的模樣,多半是村上的人。我也就趕緊叫阿慶嫂停車看看。果然是同村的胖嬸,論身板,我打小就認識,記得她走起路來,左一腳,跟著跨出右腳一大步,身子看上去晃動得厲害,但走得特別踏實。印象里,她住在村東邊最偏僻的角落,一個山彎彎里,獨門獨戶的,幾近鄰村了。集體經濟時,捧稻谷的她,總會留一點給后面拾稻穗的小孩,多少讓我對胖嬸產生好感。她的姑娘比我稍大一些,還有個小兒子,好些年沒見了……寒暄過后,我們開車帶上了她。
“老表進房子,喝酒,打包了一些東西,饅頭、扣肉、鹵鴨,外甥歡喜吃的。”胖嬸好像解釋著什么,生怕我見笑,她是個直性子的人,“你阿爸阿媽會做,人又好,我來村里,你媽總拿點東西給我的,我又沒有什么給你們……”
我說你現在住哪里,她說東溪。我說你家原來住村最東頭的,她說是的,房子破了,想回來造,別人勸她,一把年紀了,犯不著,沒意思的,想想那個地方太偏了,后山又有墳,一個人住怪怕的。我說小鬼呢,她說都成家了,過年才回來一趟,也不曉得他們想不想回來造,應該不會回來造吧……
“橋頭,你們把我放下來好了,一點點路,我走一下就到了,麻煩你們了。”胖嬸好似心里過不去一樣,“這點東西拎著不重。”她又補了一句。
“送到好了,你住哪里?”
“不用不用,等下我走走好了,這么一點路,又沒有什么事。”她執拗地說,多少還是有點麻煩了我們的意思。“你們好的,常常回去的……”她欲言又止。
“小鬼成家了,也有自己的事情。”說著說著就到了橋頭,我們不再堅持,就靠邊停了下來。胖嬸一邊說著:“麻煩了麻煩了。”一邊又放下回禮的那袋米,揮手與我們告別。我突然覺得,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會被這位毫不掩飾的人所理解,沒有一種坦言會讓她吃驚,或不愉快。
我搖上車窗,有些唏噓。舉手之勞,讓胖嬸如此感懷,多半是這多情的土地賜予她醇厚溫良的性格。
車子拐進小區時,母親來電話了,“今天我生日,你爸說請我去百歲坊飯店吃,他開玩笑的。算了,還是家里燒點,生日,算了,家里吃點好,又不是逢九逢十。”母親顧自己說話,我一時插不上嘴。
“到分水吃吧,等下來接你們。”我搶了一句,“生日,開心點過。”
“算了,還是家里過,不麻煩了。”
“媽,那你燒碗面吃,加兩個雞蛋。” 阿慶嫂把頭伸過來說。
“早上吃過了。好了,沒事,就這樣。”母親把電話掛了。
我想象著兩個活得通透的老人對酌的情景:桌底下,從灶孔鍬出的炭火燒得正旺。母親拿來布鞋,讓父親穿上,把腳擱在木架上暖。父親給母親倒酒,“今天生日,多倒一口。”母親說,“好好好,多一點點,可以,你自己倒滿來。”母親又把煎黃的石板魚擺到父親面前,“湊熱,你喜歡吃的,多吃點。”父親便說:“別客氣,來,我敬你一下,你辛苦啦!”
“炒了盤黃豆,吃吃看咸淡,松不松的。”母親拿手的炒黃豆,打小我們就饞,父親享受了一輩子,好有福氣的。
“松了,咸淡剛剛好。你也吃吃看。”父親和母親碰了碰杯。
夜色微涼,灶間溫暖。父親和母親喝著酒,一定也聊到了我們,還有孩子們……這一夜,沉浸在彼此相伴的感覺中,父親母親篤定心甘情愿地被對方迷醉,沉浸在愉悅、天氣、菜地和平靜的沉默中。
- 大理文化的其它文章
- 吟唱在博南古道上的詩魂
- 在大理一中的求學時光
- 鶴慶龍華山之約
- 行走賓川
- 品味大理
- 鄉土散文的別樣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