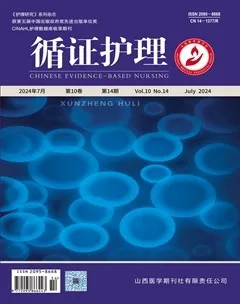腰椎間盤突出癥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影響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kinesiophobia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I Xiaohong,CHEN Juanjuan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Shandong 250012 China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Juanjuan,E-mail:18560086263@163.com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kinesiophobia;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decision tree model;influencing factor
摘要 目的:探討腰椎間盤突出癥(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危險因素,并基于Logistic回歸模型和決策樹模型建立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風險預測模型。方法:回顧性分析2021年3月—2022年8月在我院行手術治療的355例LDH病人的臨床資料,根據病人術后是否發生恐動癥分為恐動癥組和非恐動癥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篩選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危險因素,運用SPSS Modeler軟件建立預測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決策樹模型,并分析模型的預測效能。結果:本研究恐動癥發生率為37.46%;恐動癥組和非恐動癥組病人受教育程度、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ADS)評分、自我效能、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醫療費用支付方式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VAS評分、HADS評分、自我效能、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醫療費用支付方式均為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決策樹結果顯示,自我效能是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主要危險因素,其次為醫療費用支付方式、VAS評分、HADS評分以及家庭人均月收入;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OC)顯示,決策樹模型的預測能力高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結論:受教育程度、VAS評分、HADS評分、自我效能、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醫療費用支付方式為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獨立危險因素,醫務人員可結合上述模型從不同層面發現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影響因素,有助于評估病人病情,及時給予相應的干預指導。
關鍵詞 腰椎間盤突出癥;恐動癥;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決策樹模型;影響因素
doi:10.12102/j.issn.2095-8668.2024.14.024
腰椎間盤突出癥(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主要是由腰椎間纖維環、軟骨板以及盤髓核等部位出現退行性改變后,受外力因素所致的髓核組織突出,相鄰脊神經受到壓迫或刺激而易誘發的一種疾病。該病多發于20~50歲人群,病人多表現為下肢麻木、坐骨神經痛、腰部疼痛等,而疼痛作為主要臨床癥狀,嚴重影響病人的生活和工作[1-3]。目前,針對LDH初發病人或癥狀較輕、病程較短的病人通過休息后以及藥物或按摩、針灸等治療方式干預后均可有效緩解,而針對保守治療無效者,手術治療亦屬于該類病人的主要治療手段[4-5]。雖然手術可使大部分中、重度LDH病人從中獲益,但術后康復鍛煉仍是影響病人治療效果乃至預后的主要因素[6]。有研究報道,LDH病人于手術治療前經歷了長期的疼痛困擾,加以術后帶來的創傷性疼痛,亦可導致病人并發恐動癥[7]。恐動癥主要是指個體因害怕或疼痛而對身體活動或運動產生逃避的恐懼心理,其多發于外科術后或伴有慢性疼痛的病人中。而LDH病人術后并發恐動癥亦會導致病人逃避乃至恐懼早期功能鍛煉,嚴重者亦會出現肌萎縮、術后粘連以及關節僵硬等相關并發癥發生,繼而增加臨床治療難度,不利于術后恢復[8-9]。然而現階段國內有關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的相關研究較少,且部分研究僅采用傳統的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預測,雖然具有較好的預測效能,但該種模型在決策建議方面存在一定不足[10]。決策樹是以樹形結構所構建的預測模型,其可在不創建啞變量的前提下,對定性預測變量進行處理[11]。基于此,本研究將上述兩種方式用于LDH術后病人中,以期為LDH術后恐動癥的防治工作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21年3月—2022年8月在我院治療并行手術治療的355例LDH病人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通過我院相關檢查確診為LDH且行手術治療者;自愿參與本研究者;臨床資料齊全,可與醫務人員正常交流者;年齡≥18歲。排除標準:伴有腫瘤或峽部裂、腰椎結核、腰椎管狹窄等疾病者;伴有精神類疾病或血液傳染性疾病者;研究期間自行退出者。恐動癥診斷標準[12]:恐動癥Tampa評分表(Trampa Scale for Kinesiophobia,TSK)得分gt;37分者即判定為恐動癥。根據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情況將病人分為恐動癥組和非恐動癥組。
1.2 調查工具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
調查表包括年齡、體質指數(BMI)、病程、職業、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飲酒史、抽煙史、家庭人均月收入、醫療費用支付方式、高血壓史及糖尿病史等。
1.2.2 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 Scale,VAS)[13]
采用一條長10 cm的游動標尺,兩端分別為“0”“10”,0分表示無痛,10分表示難以忍受的最劇烈疼痛。
1.2.3 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14]
該量表包括焦慮與抑郁2個分量表,各包括7個條目,采用Likert 3級評分法,總分為0~21分,當得分≥8分時則提示受試者存在焦慮或抑郁癥狀。
1.2.4 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15]
該量表共10個條目,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各條目為4分,分數越高則表示受試者同意程度越高。GSES總分計算方法為各條目之和的均分,GSES總分為0~4分,分數越高則表示受試者的自我效能水平越高。
1.3 統計學方法
運用SPSS 24.0軟件分析數據,定性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定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運用Logistic回歸分析篩選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的危險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運用IBM SPSS Modeler 18.0軟件建立預測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的決策樹模型,并采用MedCalc19.8軟件繪制決策樹模型和Logistic回歸模型的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
2 結果
2.1 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的發生情況
納入行手術治療的355例LDH病人,術后有133例病人發生了恐動癥,有222例病人未發生恐動癥,恐動癥發生率為37.46%(133/355)。
2.2 兩組臨床資料比較(見表1)
2.3 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危險因素分析
以LDH病人術后是否發生恐動癥為因變量(發生=1,未發生=0),以表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自變量賦值情況見表2。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VAS評分、HADS評分、自我效能、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醫療費用支付方式為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3。
2.4 LDH病人術后恐動癥影響因素的決策樹模型
將表1中有統計學意義的6個自變量納入決策樹模型,見圖1。本研究決策樹生長5層,共計17個節點,其中終末節點9個,其中首層為自我效能,提示LDH病人自我效能與術后發生恐動癥最具相關性,自我效能≤2.2分的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率為72.09%,自我效能gt;3.3分的病人恐動癥發生率為42.22%。
2.5 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和決策樹模型的分類效果比較
預測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的Logistic回歸模型的ROC曲線下面積(AUC)值為0.743,95%CI(0.698,0.786),預測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的決策樹模型的AUC為0.798,95%CI(0.755,0.836),決策樹模型的預測效能稍優于Logistic回歸模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5.423,P<0.001)。見表4、圖2、圖3。
3 討論
由于機體血供異常,修復能力下降,加之自身機體活動多且負重大,促使多數人于20歲以后開始出現退行性改變。LDH疾病是由腰椎間盤彈性減退,遭受積勞性損傷或外傷時,肌肉韌帶緊張性增強,促使纖維盤無法承受而出現破裂所致[16],繼而導致大部分LDH病人均伴有不同程度的持續性疼痛癥狀。雖然手術可有效緩解病人疼痛程度,但治療期間因個體原因,病人受壓迫神經的恢復程度也有所差異,促使部分病人仍伴有明顯疼痛感[17]。此時,當病人感覺自身受潛在性疼痛威脅時,亦會習慣性回避可能導致疼痛發生的相關行為[18]。本研究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率為37.46%,低于宋瑩瑩等[19]研究報道的67.13%。分析原因可能與樣本量、研究設計等因素相關,建議臨床治療期間需加強對該類病人的關注度,繼而有助于優化LDH病人臨床療效,降低恐動癥發生風險。
3.1 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危險因素
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355例LDH手術病人的臨床資料,并采多因素Logistic回歸篩選恐動癥的危險因素,結果發現,病人受教育程度、VAS評分、HADS評分、自我效能、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醫療費用支付方式均是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獨立危險因素。
3.1.1 受教育程度
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是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危險因素[20],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病人術后更易發生恐動癥。本研究恐動癥組初中及以下學歷者占比明顯高于非恐動癥組,結果與其具有一致性。分析原因可能為:學歷相對較高者可通過書籍、網絡等多種途徑獲取疾病相關知識和信息,并對獲取的知識進行有效辨別,繼而有助于病人更快地掌握正確的應對方法,同時可通過家人以及朋友的支持,更好地調節自身情緒,反之,學歷相對較低的病人對疾病的認知不足,也無法更好地調節自身情緒,繼而導致術后發生恐動癥的風險增加。
3.1.2 疼痛
相關研究表明,疼痛是LDH病人的主要臨床癥狀,疼痛程度越高者術后更易發生恐動癥[19]。因為術后早期活動亦會增加病人疼痛程度,而疼痛易導致病人形成不良心理,繼而因抵觸活動而出現恐動癥。此外,亦有相關研究表明,對疼痛的接受程度較低者,術后恐動癥的發生風險隨之增加,且不利于病人術后康復[21]。
3.1.3 焦慮、抑郁情緒
范飛等[22]發現,焦慮、抑郁情緒亦是影響LDH病人術后恢復的重要因素,重視病人負性情緒有助于降低恐動癥發生率。分析原因可能為LDH病人因長期遭受疼痛困擾,加之手術本身就是一種有創操作,且術后康復功能鍛煉亦會進一步增加疼痛程度,促使部分耐受能力相對較差者極易出現負性情緒,繼而導致術后恐動癥的發生風險增加。
3.1.4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主要是指個體在實現目標過程中,對自身能力的自信程度或信念。王敏等[23]發現,自我效能越低的LDH病人術后更易發生恐動癥。本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效能較低者術后發生恐動癥發生率高于自我效能較高者,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一致。分析原因可能為:自我效能較高的病人于術后能夠努力克服疾病帶來的不良刺激,并堅持康復信念,積極應對不良心理;反之,自我效能較低者則會擔心疼痛對自身帶來的損傷,在面對困難時易選擇放棄,繼而有利于恐動癥發生。
3.1.5 醫療費用支付方式及家庭人均月收入
研究發現,自費治療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較低的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風險更大[24]。本研究結果與其相符。究其原因可能為:自費治療的LDH病人享受醫療保健的服務項目相對較少,促使病人面對疼痛時無法及時采取正確方式進行應對,繼而更易出現恐動癥。此外,收入較高的LDH病人在面對疾病時多考慮如何快速康復,不必擔心醫療負擔。反之,經濟條件相對較差者考慮得相對較多,思想負擔重,且更易產生消極想法,同時疼痛程度亦會被逐漸放大,繼而恐動癥發生風險隨之增加。
3.2 LDH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決策樹模型有良好的預測能力
本研究基于Logistic回歸模型和決策樹模型預測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的預測效果優于單純行Logistic回歸模型,但2種模型在預測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的影響因素結果具有較高的一致性。本研究Logistic回歸雖然可計算出受教育程度、VAS評分、HADS評分、自我效能、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醫療費用支付方式等不同因素預測恐動癥發生的OR值,并反映了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與上述各因素之間的數量依存關系,但其無法顯示各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決策樹模型可直觀顯示出各因素間的交互作用,本研究中自我效能是決策樹模型的首層影響因素,提示自我效能是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的重要影響因素,而決策樹第2層~第4層則顯示不同因素間的交互關系。上述2種模型各具優勢,臨床治療期間可結合上述模型共同預測,繼而充分發揮2種模型的優越性。
4 小結
受教育程度、VAS評分、HADS評分、自我效能、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醫療費用支付方式均是LDH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的影響因素。本研究構建的決策樹模型預測效能較好,有助于臨床篩查恐動癥高危病人,但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且樣本來源單一,結果可能存在一定不足。因此,相關結論還需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驗證。
參考文獻:
[1] 朱方強,姚亞偉,熊承杰,等.經皮椎間孔鏡技術治療肥胖患者腰椎間盤突出癥的臨床療效[J].華南國防醫學雜志,2021,35(11):806-809.
[2] 徐寅強,邢順民,方良勤,等.改良經皮椎間孔鏡TESSYS技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療效分析[J].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2021,36(7):729-731.
[3] AGHA O,MUELLER-IMMERGLUCK A,LIU M Y,et al.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 effects on multifidus muscle composition and resident stem cell populations[J].JOR Spine,2020,3(2):e1091.
[4] 鄒明翔,周其佳,左松球.經皮椎間孔鏡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的臨床療效分析[J].世界復合醫學,2020,6(11):41-43.
[5] 王鋒.針灸配合中藥外敷治療老年腰椎間盤突出癥療效分析[J].中國臨床醫生雜志,2018,46(1):112-114.
[6] TAO X Z,JING L,LI J H.Therapeutic effect of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spine system in the treatment of prolapse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J].European Review for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2018,22(1 Suppl):103-110.
[7] 葛明富,王柏卿,高曦,等.針刀松解夾脊穴配合深刺次髎穴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療效分析[J].針灸臨床雜志,2018,34(1):40-43.
[8] GUPTA A,UPADHYAYA S,YEUNG C M,et al.Does size matter?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size on the success of nonoperative treatment[J].Global Spine Journal,2020,10(7):881-887.
[9] OSTER B A,KIKANLOO S R,LEVINE N L,et al.Systematic review of outcomes following 10-year mark of spine patient outcomes research trial for intervertebral disc herniation[J].Spine,2020,45(12):825-831.
[10] 吳夢雯,何麗芳,肖春秀,等.中青年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的腰椎間盤自護行為水平及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護理管理,2020,20(4):529-534.
[11] 張燕,彭伶麗,張磊,等.基于logistic回歸和決策樹法預測顱腦腫瘤患者術后病情惡化風險[J].護理學雜志,2022,37(7):15-19.
[12] 徐慧萍,張炎改,劉延錦,等.全膝關節置換術后患者恐動癥的影響因素研究[J].中華護理雜志,2021,56(10):1460-1465.
[13] HELLER G Z,MANUGUERRA M,CHOW R.How to analyze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myths,truths and clinical relevance[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ain,2016,13:67-75.
[14] 葉瑞繁,耿慶山,陳劍,等.醫院焦慮抑郁量表與Beck抑郁問卷在綜合醫院門診病人中評定抑郁的比較[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3,21(1):48-50.
[15] 陳尚美,魏錦錦,黃升云,等.基于“5W2H” 的自我管理聯合脊柱推拿對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腰部功能及疼痛程度的影響[J].頸腰痛雜志,2021,42(6):887-889.
[16] 酈杭婷,沈嬌妮,萬昕瑞,等.髖膝關節置換術患者康復自我效能感在正念與恐動癥間的中介效應研究[J].中華護理雜志,2022,57(10):1177-1183.
[17] ZHANG R W,MO Z M,LI D,et al.Biomechanical comparison of lumbar fixed-point oblique pulling manipulation and traditional oblique pulling manipulation in treating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k protrusion[J].Journal of Manipulative and Physiological Therapeutics,2020,43(5):446-456.
[18] 劉莉,張傳志.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治療依從性的影響因素分析[J].檢驗醫學與臨床,2020,17(7):942-945.
[19] 宋瑩瑩,張嵐,梁瑛琳,等.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術后恐動癥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J].東南國防醫藥,2019,21(2):205-207.
[20] RAZA S,ECKHAUS J.Does surgical fixation improve pai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non-flail rib fractures? A best evidence topic review[J].Interactive Cardiovascular and Thoracic Surgery,2022,35(3):ivac214.
[21] FAGEVIK OLSN M,SLOBO M,KLARIN L,et al.Physical function and pain after surgical or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of multiple rib fractures--a follow-up study[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Trauma,Resuscitation and Emergency Medicine,2016,24(1):128.
[22] 范飛,姜貴云.下背痛與心理因素的臨床相關性研究進展[J].中華物理醫學與康復雜志,2017,39(3):237-240.
[23] 王敏,王霞,侯文秀.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術后恐動癥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J].齊魯護理雜志,2020,26(10):15-17.
[24] 陳俠,陳琰琰,李潔,等.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恐動癥的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醫刊,2019,54(12):1364-1367.
(收稿日期:2023-12-02;修回日期:2024-06-17)
(本文編輯賈小越)
作者簡介 李曉紅,護師,本科
*通訊作者 陳娟娟,E-mail:18560086263@163.com
引用信息 李曉紅,陳娟娟.腰椎間盤突出癥病人術后發生恐動癥的影響因素[J].循證護理,2024,10(14):2610-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