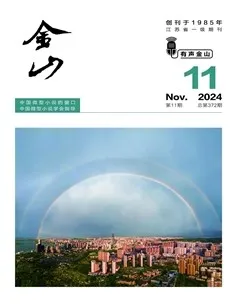和外婆的握別
我們家的親戚平常也不怎么聯系,沒事的時候噓寒問暖之類的很少。2018年3月21日(農歷二月初五,春分)傍晚的時候,我突然接到小舅的電話,頓時一怔,果然,小舅說,你外婆“走了”。語氣還算平靜,說年紀大了,九十六歲壽終正寢。
早在上世紀的1991年,我就寫了篇散文《外婆》刊登在《莫愁》雜志上,那時候我才24歲,是個多愁善感的文學青年。那篇文章后來我都不怎么示人,因為那個年紀還不成熟,字里行間都能擠出情感的汁來,我的個人散文集出版的時候,都猶豫著要不要收錄進去。算起來,我那篇文章發表的時候,外婆是70歲,古稀的年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涌動著朦朧詩潮,我也會寫一些不明不白的東西自我陶醉,一發表了就有誦讀天下的熱望,但從這篇散文發表后,我就告別了青春寫詩的熱情季節,開始了散淡的散文寫作,所以,這篇《外婆》于我來說也有一定的象征意義。
外婆長壽,她終于等到我也快老了,因此,這些年我都會在春節前去看她一次,聽聽她絮聒。早前,我一去,她還能拄杖站在門口,過去的一些鄰居會圍攏了來,她會大聲炫耀說:“我外孫來看我了。”還把我的名頭說出來,讓別人嘖嘖稱贊,她則滿足地執著我的手把我往家里拽。再后來,她漸漸行動不便了,平時她的長孫媳婦會照顧她坐在門前的藤椅里曬太陽,年輕人自然不會總是陪她說話,她就把頭抵著手杖等太陽下山。我去的時候,她會一直拽著我的手,問許多事情,問完了,就講從前的事,一遍遍不停重復,妯娌間的不和過去這么多年也還記得清楚,總說:“我就不死,我不死在她前頭。”我就笑,并大聲地說:“好啦,都幾十年前的事了,我要走了。”一見我要走,她會哭出來,使勁拽著不松。
我還記得外婆過九十大壽的時候,小舅舅把她接到城里的酒店,辦了好多桌,那時候她已經耳背,被大家安頓在臺前中間的椅子上。小舅舅是中學的校長,他站著致辭,外婆也聽不到講什么,但臉上總是保持著笑意,大概曉得大家的意思。她的懷里是晚輩獻的一捧鮮花,衣著整潔,頭發也綰得整齊。大舅歪頭笑著對我說:“你看,身體比我還要好。”
每年的年根我照例去看她,大舅也照例說,身體還好。但我還是覺得她的精神一年不如一年了,后來眼睛也渾濁起來,已經不大能看得清來人。我去的時候,大舅會大聲地告訴她。但她的意識還是清楚的,還是會說起妯娌的不好。我明顯覺得到她身體越耗越輕,骨瘦如柴,力氣也小了下去,假牙拿掉了扔在旁邊盛了水的碗里,一個人睡在一間屋子里,我感覺她身體的溫度抵御不了寒冬。大舅說,有電熱毯。
今年過年前,我買了許多開水沖了就能吃的東西,有奶粉、芝麻糊,還有軟糕點等等,驅車去看她,囑咐表弟媳平時可以給外婆進點營養。外婆一人靜靜地躺在床上,問誰呀,誰呀。大舅如往常一樣大聲地告訴她,她突然哭起來不能抑制,我因感冒初好,并不敢久留,怕她這樣的歲數萬一被傳染了抵御不了。她看我又是來去匆匆,就把瘦瘦的手伸出被窩緊握住我的手不放,沒牙的嘴癟下去,大哭,大哭。
總以為跟平常一樣的,但在年后的春分那天,大舅事后好幾遍地重復說,中午還吃一點飯的,也是清醒的狀態呀。下午本準備去打麻將的表弟媳發現了異樣,連喊了人來,就已經“走了”。
外婆的一生,跟她這個年紀的人一樣,大都經歷了苦難。她的長女,也就是我的母親考上學校成了家庭的驕傲,然后又早早地過世,成了她長久的心痛。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外公,早年是地下組織成員,后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直到晚年才平反歸來。這些都構成她勞碌一生的坎,連她自己晚年也驚詫能活這么久。
這世上本就沒有什么永遠。
我后來一直想,外婆在年前一定是在跟我握別,只是她哭得那樣的不能抑制,這讓我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