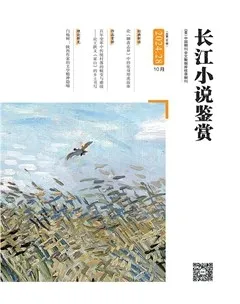論理查德·福特小說《獨立日》中的美國后南方消費社會
[摘要]美國后南方時期主要代表作家理查德·福特的小說《獨立日》通過描寫20世紀80年代末房地產行業的興起,探察消費文化對個體的思維模式和價值理念的影響。在符號的系統化操控下,傳統的地方感失去了原有的象征意義,蛻變為經濟資本控制的商品;個體的社會存在決定了其思維模式和商業理念,房地產經紀人的身份促使巴斯克姆遵循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其主體意識、職業選擇和人際關系皆處于異化的過程之中。不過,福特在小說中呈現的并非對后現代時期美國消費社會的批判,相反,他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接納消費文化,并探索消解異化的途徑,以期調和精神追求和物質享受的沖突,傳達了與時俱進的價值理念。
[關鍵詞]理查德·福特" "《獨立日》" "美國后南方" "消費社會
理查德·福特是美國后南方時期主要代表作家,在當代文壇具有重要影響。1995年,他憑借小說《獨立日》成為首位同時榮獲普利策文學獎和國際筆會/福克納文學獎的作家。作品聚焦主人公弗蘭克·巴斯克姆的城市體驗及其價值理念的變化,再現了工業文明和消費文化的影響下美國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圖景。著名美國南方文學評論家弗萊德·霍布森認為福特小說中的巴斯克姆是典型的南方人,無論身處于新澤西州還是底特律市,他都懷有濃郁的地方情結。馬修·奎因對此持不同觀點,在《南方現代主義之后:當代南方小說》中,奎因聚焦福特作品中的價值理念與南方傳統價值觀的非連續性,從歷史意識、地方感、家庭觀的淡化闡明巴斯克姆的情感和意識形態的變化。他認為福特的小說呈現無根性、碎片化、不確定性等特征,標志著美國南方小說開始從現代主義朝后現代主義轉向。
劉易斯·辛普森提出“后南方”(Post South)的概念,用來指稱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后現代資本主義語境下受到國際化、同質化影響的美國南方[1]。從福特的前作《體育記者》可以看出巴斯克姆對城市化、工業化、消費主義的接納,表明他開始與美國南方傳統的價值觀背離。續篇《獨立日》中,福特進一步解構了傳統價值觀,小說中“地方”的意涵產生了根本性轉變,它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精神歸宿和道德載體,而是經濟學上的地產概念。作為房地產經紀人的巴斯克姆意識到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與“地方情結”的沖突,開始尋找新的生存哲學。本文通過考察《獨立日》中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房地產行業興起的態勢,剖析資本秩序主導下的消費文化對地方感的影響,以及符號邏輯的操控下個體的主體意識、職業選擇和人際關系的異化現象,并進一步探究擺脫異化的途徑,揭示福特在小說中呈現的并非對后現代時期美國南方消費社會的批判,相反,他擁抱消費文化,試圖緩和精神與物質的二元對立,該小說傳達了與時俱進的價值理念。
一、房地產交易的興起:地方感的消逝
作為“南方文藝復興”的理論基礎,《我要選擇我的立場》傳達了約翰·蘭色姆、艾倫·泰特和羅伯特·佩恩·沃倫等“納什維爾農業主義者”對工業化、城市化的態度。他們弘揚農業主義傳統,肯定舊南方的田園風光,批判工業文明對自然、土地和鄉村生活的破壞。蘭色姆認為資本主義財產關系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系,“大量的資金、大規模生產、市場或者信用系統。資本主義通過這些無形的事物改變了農民的生產方式”[2]。他留戀農業社會,抗拒把有機、自然、穩固的地方變成非自然、機械化的工業化社會。實際上,“南方”這一地域概念隱含一種意識形態,人們傾向于維護舊南方上層階級的立場而美化農業主義傳統。馬廷·波恩在《當代小說中的后南方地方感》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農業主義者把“南方”作為抵擋資本主義引發的土地投機、房地產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對“地方”破壞的根據地[3]。
20世紀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張,尤其是福特主義開創的新型勞動和生產過程被廣泛接受后,西方社會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即以消費為導向的時期。在工業文明的影響和消費文化的巨大沖擊之下,美國南方傳統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模式失去了堅固的基礎,人們的觀念從崇尚節儉、反對過度消費向注重物質享受轉變,逐漸開始接納消費文化。福特在小說中呈現了這一文化轉型的現象。《體育記者》中,巴斯克姆經常閱讀商品目錄,從商品消費中獲得物質欲望滿足。《獨立日》中,巴斯克姆積極投身于房地產行業,通過成為房地產經紀人實現自身價值。顯然,“房地產是巴斯克姆曾在商品目錄中對物質追求的一種延伸”[3]。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原本深受歷史和個人情感影響的‘地方’概念產生了新解,蛻變為受經濟資本控制的、獨立于個體情感的商品”[1]。傳統的地方意識轉變為經濟學上的地產概念。
巴斯克姆無法忍受家鄉密西西比州的單調乏味,認為地方難以提供安全感,“地方在你需要它們的時候從來就不配合,為你恢復尊嚴。實際上,它們幾乎總是辜負你的期望……最好把眼淚咽回去,去適應令人感傷的小事,向下一個目標前進,不要回首過去。地方毫無意義”[4]。因而他離開密西西比州,不再把南方作為精神歸宿,他跨越地域的界限,從更廣闊的天地中汲取力量源泉。巴斯克姆輾轉紐約市、新澤西州、佛羅里達州和法國,最后選擇在哈達姆鎮定居,因為此地給人輕松、親近之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地理位置的變更,巴斯克姆的地方意識也悄然發生變化。段義孚認為,“地方是一個具有意義的有序世界,它本質上是一個靜態概念。如果我們把世界看作一個過程,不斷變化,我們就無法發展任何地方感”[5]。然而,巴斯克姆的地方感是動態變化的,隱匿在消費文化主導下的社會現實之中。
馬卡姆夫婦與巴斯克姆形成強烈的對比,他們忽略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意圖把地方情節轉移到新的處所。馬卡姆夫婦雖然離開了落后的家鄉佛蒙特島湖,但他們仍然留戀那里的一切,“我不想住在一個地區中……波士頓區、三洲區、紐約區。沒有人會說佛蒙特區……大家都是稱它為地方”[4]。馬卡姆夫婦忽視現實經濟條件的局限性,固執地在新澤西州尋找第二個島湖,延續以往的地方感,最終滿腔希冀化為泡影。馬卡姆夫婦的“地方感取代了自我意識”[3]。他們無法接受資本主義主導下的產權關系,不能對房地產現狀作出理智的判斷,導致錯過了理想的住所。巴斯克姆因此強調,“不要把地方神圣化”,因為“那些地方沒有你存在過的跡象”[4]。如果馬卡姆夫婦把個人情感和經濟現實分離,深入了解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那么他們就不會被迫選擇租房度日。在后南方時期,農業理想已被市場經濟所取代,消費文化的盛行致使“地方感”脫離了原有的語境,產生了新的意涵,同時也對人們的思維模式和價值理念產生強烈沖擊。
二、“符號邏輯”的操控:房地產經紀人的異化表征
詹明信“把后現代文化看作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文化”[6]。鮑德里亞認為消費是溝通和交換的系統,是被持續發送、接受并重新創造的符號編碼,是一種語言[7],他發展了商品邏輯的符號學理論,指出消費必然導致人們對符號進行積極的操縱。消費社會中到處都滲透著符號與廣告語言,商品原有的交換價值和工具理性變為資本的運作范疇,被“商品-符號”邏輯所取代。巴斯克姆的社會存在決定他的思維模式和商業理念,房地產經紀人的身份促使他遵循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福特在小說中展現了無所不在的異化現象,它彌漫在個體的主體意識、職業選擇和人際關系當中。
當個體認為自己“同強加于他們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從中獲得滿足時,個體就開始走向了異化的境地,簡言之,異化了的主體被其異化了的存在所吞沒”[8]。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強調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導致個體放棄自我認同和原本的情感聯系,轉而以利益衡量一切。巴斯克姆的行為模式體現了消費文化對個體生活和職業選擇的影響。巴斯克姆大學畢業后沒有回到家鄉密西西比州,而是選擇去具有經濟發展前景的紐約市工作,成為一名作家。20世紀80年代,房地產經紀行業蓬勃發展,巴斯克姆敏銳地覺察到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規律,緊跟時代潮流,成為房地產經紀人。巴斯克姆具備獨特的投資理念,除了自己的住所以外,他還購置了兩套房子用于出租。不論是職業路徑的改變,還是投資理念的形成,都預示著巴斯克姆正進行“符號的系統化操控活動”[9],積極地與生存環境進行互動。對他來說,出租房屋不僅能夠幫助沒有住所的人,也能夠投資社區,維系與哈達姆鎮居民的聯系。巴斯克姆通過這種方式彰顯自己慷慨的品質。他之所以從事房地產行業,是因為“它結合了超前思維和保守思想。我一直想把兩者結合”[4]。他在房產交易中找到了滿足感和存在的意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異化造成個體思維模式和價值理念的轉變,開始以個人利益為導向行事。
巴斯克姆和馬卡姆夫婦之間的社會關系因為房屋交易變成物質交易關系。在向客戶推銷房子時,巴斯克姆表達物質高于一切的價值理念,“當變故到來時,(房產)價值將是一切立足之本”[4]。相比于房產銷售帶來的巨大收益,人際關系的維系顯得微不足道。巴斯克姆和馬卡姆夫婦即便已經認識了四個月,對彼此仍知之甚少。為此,巴斯克姆形容他們是“最佳陌生人”[4]。為了提高房屋交易的成功率,巴斯克姆總結了一些推銷經驗,比如強調房產價值、房屋的建造工藝、房子的耐用性等,甚至為了獲取客戶的信任,巴斯克姆在衣著上也頗費功夫,他選擇的并非價格昂貴的品牌,而是從商品目錄購買的無商標的衣服,如此,他就能讓客戶“抱有同情心,或者獲得優越感”[4],以解除對他的心理防備,從而提高房產交易的成功率。但面對菲利斯·馬卡姆對經濟情況的擔憂,他感到束手無策,因為他的關注焦點是房屋銷售技巧,而不是客戶的心理狀態。巴斯克姆把自己的溝通技巧稱為“偽交流”,表面上他設身處地為客戶著想,及時解決他們的困惑,關心他們的生活,實際上,一旦完成交易,他就把客戶看作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顯然,巴斯克姆以交換價值衡量人際交往的價值,把人與人的關系看作物與物的關系,陷入了拜物教的思維方式。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消費異化是社會弊端的顯著表征之一。物品不再是簡單的消費品,而是整個社會系統中的符號和象征;個體逐漸被外部的體制和規則所規訓、塑造。巴斯克姆的異化程度隨著經濟發展的進程而逐漸加深。他置身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潮流之中,將商業運作視為一種應對生活突發事件的生存策略。成為房地產經紀人后,他被生產活動和商品所控制,逐漸喪失主觀能動性,并將房產交易視為一種謀生手段,從而進行虛假的自我實現。房產銷售和顧客之間呈現一種表面化的關系,缺乏深度和情感聯系。巴斯克姆以實現交易為目標與客戶進行互動,其內在動機不是為了建立真正的人際關系,而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福特通過展現小說中人物的自我意識和人際關系的異化,折射出資本主義社會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弊端,批判社會機制對消費異化行為的鼓動以及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至上的價值觀。
三、普遍異化的消解:精神與物質的調和
文學評論家切爾內基認為,“福特的巴斯克姆系列小說反映了當代美國的文化氛圍:人們不再渴望個人的救贖,更不用說回歸到某個早期的時代,而是追求一種感覺,一種短暫的幻覺,即個人福祉、健康和心理安全感”[10]。福特的消費敘事就是這種文化觀念的體現。他并不像傳統南方作家那般對消費文化持負面觀感,強調物質享受是低層次的精神愉悅,而是擁抱消費文化,把物欲的滿足作為日常生活的普遍狀態。巴斯克姆的上司羅利認為房地產行業與現實世界不同,“這是房地產,現實在其他地方”[4]。但巴斯克姆“意識到房地產就是(社會經濟的)現實,隱藏在哈達姆的地方感之中”[4]。他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消費時代的到來,尋找新的價值觀。如今人們生活在一個標準化的后現代文化之中,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促進了人們的消費需求。只有順應消費社會的大環境,立足當下的價值觀,才能找到在新時代的生存之道。
在列斐伏爾看來,異化無處不在,且個體始終處于異化與去異化的辯證過程之中。福特的消費敘事就是列斐伏爾異化觀點的例證。一方面,巴斯克姆享受物質生活,并把商業當成信仰,通過房產經紀人這一職業實現自我價值,享受物質生活。另一方面,他意識到自己被物質需求操縱,不斷為“去異化”做出努力。在進行房產交易的過程中,巴斯克姆發現,房屋承載了獨特的家庭記憶和深厚的情感,而房屋交易本身也超越了其商業本質,成為修復家庭關系的媒介。《獨立日》中,與以往購買房產進行投資的動機不同,巴斯克姆期望通過購買前妻安的房子重新建立與家人的聯系。離婚后,他放棄了在紐約體育雜志社的工作,先是搬去佛羅里達州短期居住,然后前往法國旅居,回到哈達姆鎮后,發現安在康涅狄格州的迪普里弗已開啟新的生活。出于對家庭生活的眷戀,巴斯克姆購買了安的房子,因為他曾在那里和孩子們共度了難忘的時光:“我習慣了在這個房子里生活,因為孩子生病時我在那里度過了三年不眠之夜。”[4]這個房子充滿了溫馨家庭生活的回憶,是他與過去、孩子聯系的紐帶。
福特在《獨立日》中重新定義了“獨立”的含義,他強調“獨立是指與他人交往的自由,而不是指中斷與他人的聯系”[4]。他曾在訪談中提到,“為了維持生活的平衡,巴斯克姆付出的代價是被孤立……他的問題在于,在這一過程中如何與其他人聯系”[11]。面對生活的各種挫折——兒子去世、婚姻破裂、職業困境,巴斯克姆備受打擊,難以從中解脫出來,因此他沉溺于物質世界中,減少與他人的交往,并試圖通過創辦房地產公司實現自我價值。然而,他發現自己無法完全割裂與過去的聯系,正如他所言:“房子對我們有一種近乎權威的力量,只要我們在一個地方待得太久,它就會摧毀我們的生活,或者讓我們的生活變得完美。”[4]他認為安的房子中有過往家庭生活的印記,是真正的家。搬進安的房子后,過去的溫馨回憶涌上心頭,他與安以及兩個孩子之間的關系也變得更加緊密。由此看來,房屋交易不再是純粹的商業行為,而是重建家庭生活的方式。
福特通過描摹巴斯克姆在城市中的獨特經歷和坦然接受物質生活的積極態度,揭示在后南方社會中人們不再擔憂物質的潛在危害,恪守精神高于物質的價值觀,而是享受城市帶來的高品質物質生活,通過物質的符號功能進行自我實現。與此同時,福特也探索了擺脫異化的途徑。對于傳統價值觀和消費文化的沖突,巴斯克姆找到了解決辦法,即“把破碎的過去和混亂的現在聯系”[4],而不是把兩者區隔開來。他通過回歸本真的日常生活,重建家庭關系,調和物質享受與精神追求的矛盾,掙脫物體系構建的符碼邏輯,從而跨越異化。
四、結語
20世紀60年代之后,美國南方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開始融入美國消費社會的主流,南方文學的焦點從對土地的眷戀和歷史的懷舊情懷轉變為對消費主義、大眾文化的接納。福特在《獨立日》中顛覆“南方文藝復興”的價值觀,解除對消費文化的道德審判,對后南方社會的消費經濟活動、消費意識觀念和消費社會生活進行深入的剖析,引導當代南方人走向后現代文化浪潮。他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接納消費文化,調和了物質和精神間的矛盾關系,傳達了把握當下的人生信條和與時俱進的價值理念。福特對消費文化的肯定態度使人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異化與去異化的辯證過程,這對于建立正確的消費觀和價值觀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 李楊.顛覆·開放·與時俱進:后南方的小說縱橫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2] Ransom J C.I’ll Take My Stand[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
[3] Bone M.The Postsouthern Sense of Plac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4.
[4] Ford R.Independence Day[M].London:Bloomsbury,2006.
[5] 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M].王志標,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6] 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劉精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7] 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8]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9] 鮑德里亞.物體系[M].林志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0] Chernecky W G.Nostalgia Isn’t What It Used To Be:Isolation and Alienation in the Frank Bascombe Novels[M]//Guagliardo H.Perspectives on Richard Ford.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0.
[11] Majeski S.Richard Ford:the Salon Interview[N/OL].Salon.(1996-07-07)[2022-07-16].https://www.salon.com/1996/07/07/interview_18/.
(特約編輯 劉夢瑤)
作者簡介:何璐嬌,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