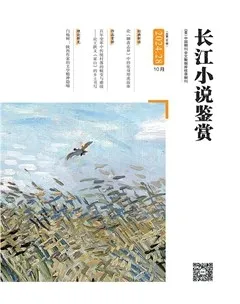文學倫理學視角下的《圣女的救濟》
[摘要]《圣女的救濟》是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的長篇偵探小說之一,也是“伽利略系列”的第五本小說。東野圭吾從社會男女問題的角度出發,運用獨特而詭譎的偵探小說筆法展示了現代日本女性所面臨的道德倫理困境,凸顯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艱難處境。通過細膩的描寫和深刻的心理剖析,小說探討了倫理困境中的人性復雜性。綾音的每一次選擇,無論是對家庭的妥協還是對自我的堅守,都是在倫理秩序和社會規范的夾縫中進行的。本文對小說女主人公真柴綾音在倫理困境下的倫理選擇進行解讀,旨在揭示作品中蘊含的倫理道德內涵。
[關鍵詞]《圣女的救濟》" "文學倫理學" "倫理混亂" "倫理困境" "倫理選擇
東野圭吾的代表作之一《圣女的救濟》可視為《嫌疑人X的獻身》的續作,也是在其基礎上構建的“神探伽利略”虛構世界觀中的第二部長篇偵探小說。《圣女的救濟》的情節以真柴義孝與妻子真柴綾音的家庭紛爭為開端,揭示了真柴家庭內部的主要矛盾——孩子的問題。爭吵過后,綾音留下了獨白:“你剛才那些話殺死了我的心,所以請你也去死吧……”[1]東野圭吾通過偵探小說的體裁敘事,闡明了自己的倫理思想和價值判斷。小說內蘊著女性倫理思想以及社會人倫的書寫,是對男女雙方主從關系的深入思考,也是對家庭倫理悲劇的沉痛反思。
本文旨在揭示現代女性在家庭倫理層面所面臨的倫理困境,并對妻子身份的倫理秩序以及倫理選擇進行解讀,通過洞察文學作品中存在的倫理道德價值取向,為人們提供了重新審視家庭以及社會倫理界限的新視角,實現正面倫理道德的回歸。
一、倫理混亂:身份的缺陷
文學倫理學批評指出:“倫理主要指社會體系以及人與社會和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和倫理秩序,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倫理的核心內容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形成的被接受和認可的倫理秩序以及在這種秩序的基礎上形成的道德觀念和維護這種秩序的各種規范。”[2]包含夫妻身份在內的家庭倫理也存在著對應的體系與規范,即對婚姻的忠誠。但是,當無形的倫理秩序遭到破壞時,受到傷害的一方就會遭受創傷,這種創傷難以修復,且會在內心不斷擴散蔓延,最終導致家庭內部倫理身份的錯亂。
在義孝和綾音的婚姻中,并沒有真愛作為支撐,義孝僅僅將綾音視為一臺“生育機器”,雙方之間的裂痕被不斷放大,綾音一直悉心照料著丈夫的生活,希望她毫無保留的愛能讓丈夫收回當初的約定,而義孝卻渴望綾音能為自己帶來子嗣,在他看來,將自己優秀的基因傳承下去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使命。以生育為目的的婚姻甚至超越了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而這個子嗣決定著他們后半生的命運。綾音的弟子宏美介入了兩者之間,偷偷與義孝暗中幽會,“在她察覺到他與若山宏美之間的關系時,她心想,該來的時候終于來了”[1],這兩人的背叛不斷刺激著綾音的神經,她為家庭付出的一切化為一團泡影,等待她的是丈夫的無情背叛與冷漠。義孝作為婚姻中的一方造成了家庭倫理秩序的混亂,踐踏了倫理規范所要求的責任,這直接導致綾音遭受了創傷。她絕望地意識到從潤子被拋棄的那一刻起,丈夫就從未打算改變想法,她的付出終究只是徒勞,對這種以生育為目的的婚姻產生不了任何作用。“婚姻當事人雙方意識到婚姻是倫理實體,自己與對方的人格統一是實體性的目的,并在精神層面認同與堅守婚姻倫理實體的普遍本性,不是作為個體而行動,而是以婚姻倫理實體為目的和歸宿,揚棄個體‘單一物’行為的任性、沖動和偶然性,實現個體‘單一物’與婚姻實體‘普遍物’相統一的倫理關系。”[3]也就是說,通過婚姻融合為一體,并擺脫個人的獨立性,才能為婚姻的穩固提供保障。
義孝的背叛讓綾音意識到自己將會成為潤子的翻版,而那位深受她鐘愛的宏美似乎在重演她年輕時的經歷,這重復上演的不正當關系化作了她內心的創傷。對義孝的出軌和宏美的背叛感到絕望與憤懣的她,回憶起了與潤子的一切,這讓綾音陷入了巨大的倫理混亂之中。定性的倫理秩序一旦崩壞,必定會引發不可修復的創傷,更加深刻的打擊是宏美的意外懷孕——背叛她的宏美輕而易舉地就獲取了丈夫一直渴求的孩子和愛情。遭受創傷的綾音由此從救濟丈夫的圣女變成了惡魔,心靈陷入了無盡的黑暗深淵。這層創傷也造成了綾音對倫理身份認知的錯亂,她意識到自己終究不是義孝所深愛的妻子,而丈夫也成為喪失倫理身份的出軌者,這種想法匯聚成了對義孝虛偽多情的深切怨恨。
從自然人到社會人演變過渡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人開始產生善惡的觀念以及倫理意識。倫理關系的相互交織構成了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客觀聯系。在每一層倫理關系中,人都要承擔起相應的倫理責任。因此,作為倫理關系之一的夫妻倫理也要求雙方對婚姻契約的忠誠和相守。
夫妻倫理的失序引發了家庭內部雙方的猜忌和失信,進而導致了嚴重的創傷。義孝的尖銳逼迫、宏美的背棄,加之綾音面對這雙重打擊后的絕望掙扎,不斷地在綾音心中敲響警鐘,直至她結束了對丈夫義孝的“救濟”。這一切都在東野圭吾無情而冷峻的“理科敘事”中顯露無遺。東野圭吾使用最樸實無華的語言敘事,不斷呈現出難以言喻的夫妻倫理道德邊界的試探,并以此作為情節構建的基石,搭建起了《圣女的救濟》這篇推理小說中最獨出心裁、最令人拍案叫絕的場景,達到了美學的高潮。
二、倫理困境:情感的矛盾
倫理困境是指文學作品中所刻畫的主要人物或主人公在精神和思想層面所面臨的道德糾葛的具體表現。在文學作品中,情感交織、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網絡以及情感的牽連促使人物在面對道德和人倫等限制性問題時陷入倫理兩難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人物的行為往往顯得舉步維艱,莫衷一是,難以從絕望與痛苦的矛盾環境中脫身。綾音在是否應該與義孝結婚的問題上陷入了倫理困境,面臨著兩個不同的倫理選擇。如果擺在綾音面前的選擇只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那么無論選擇哪一方都會符合道德尺度和倫理準則的要求。但是,綾音只能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
“倫理困境(Ethical Dilemmas)的產生是由多種因素所決定的,主要人物所處的環境和人物的內心兩個方面,外在的壓力和內在動力讓他很難作出選擇,然而最終還是要作出選擇,或者是悲劇,或者是喜劇。”[4]盡管綾音難以判斷潤子與義孝是否正在交往,但她發現自己逐漸陷入了與義孝的曖昧關系中難以自拔。兩人不久后便建立了男女朋友關系。直到潤子與綾音再次相遇時,潤子發現了他們的情侶飾品,于是徹底喪失了活下去的意愿。綾音在收到潤子寄來的砒霜后,得知了潤子的死亡訊息。好友的死亡以及扭曲的戀愛關系正是導致綾音陷入倫理困境的體現。昔日美好和諧的生活被徹底打破,加上與義孝不正當的男女關系,使得綾音陷入了無法逆轉的倫理困境之中。她甚至從未想過如何改變這種殘酷不堪的現實。這份難以言表的歉疚與虧欠一直深藏于綾音的內心深處。義孝在此時意外提出了一個條件:如果一年內不能懷孕,我們就分手。綾音知曉好友潤子和義孝已經交往了一年,并且意外發現潤子患有不孕癥。急于求子的義孝因此主動離開了潤子。而義孝向綾音提出的婚姻,不過是他為了生育而采取的一個手段。但更令綾音感到絕望的是,她曾經向潤子坦白自己存在先天性不孕的缺陷,這意味著她根本不可能懷孕。最初的砒霜只是一個預告,預示著綾音注定會走上一條曲折的道路。得知這一切后,綾音徹底沉浸在痛苦和絕望之中。
在相互尊重、自愿選擇、忠誠的基礎上建立的伴侶關系,并且對自己行為承擔責任,這是戀愛過程基本道德規范以及戀愛倫理的基礎要求。但是,綾音和義孝之間的情人關系從一開始便偏離了正軌,其間夾雜著違背情理的愧疚與虧欠。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出發,這種背離人倫的情感助長了綾音內心深處的惡,她企圖通過美滿和諧的婚姻來填補心理上的倫理空白。綾音天真地認為潤子被義孝拋棄的悲劇不在于“不孕不育”,而在于義孝并非真心深愛潤子,她只要能得到義孝內心最深處的情感,那么眼前的愛慕之人就不會因為自己無法生育而放棄自己。“雖然他對待潤子的那種做法難以饒恕,但只要他不同樣對待自己,她甘愿就這樣活一輩子。”[1]于是,綾音又重拾希望的光芒,既希望改變自己最終如同好友潤子那般悲慘的命運,又希望能與自己深愛的義孝好好生活在一起,從而擺脫良心上的愧疚與不安。綾音就這樣懷揣著殘存的希望。
無論是好友逝世并被告知“一年之內未懷孕的話就分手”時的絕望,還是后來自以為任勞任怨能換取義孝回心轉意時的希望,這些都是綾音在面臨倫理困境時,內心復雜情緒交織的真實寫照。同時,這些也為文學作品中主人公最終所采取的行動提供了倫理道德層面的有力支撐。
面對好友潤子的自殺以及“一年之內未懷孕的話就分手”的約定,綾音陷入了兩難境地,曾經想要嫁給義孝的堅定信念也開始動搖。這段婚姻最終可能會走向破裂和消亡,她不知道自己應該選擇放棄,還是選擇步入婚姻的殿堂。當她思考是否應該與這個曾與好友潤子交往多年的準新郎結婚時,身為不孕不育患者的她,心底一直有一個聲音在折磨著自己,不停地要求她對這個殘酷的現實作出抉擇,因為昔日的好友潤子也曾因同樣的問題被這個男人狠狠地拋棄。由于外部因素的干擾以及內心世界的掙扎與沖突,綾音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倫理困境之中,陷入了混沌的倫理道德關系之中。
倫理兩難的背后,蘊含著作品主要人物或主人公所不得不面對的潛在倫理困境。而處理倫理困境的過程又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主要人物的倫理行為及其倫理動機的價值判斷,成為一種先決條件。綾音在面對復雜的倫理兩難時,最終以追求真愛的倫理價值取向,作出了一個始料未及的倫理選擇——選擇與義孝步入婚姻的殿堂。反過來說,這一選擇也解決了長期困擾綾音的倫理困境。
在外部條件的驅使下,綾音一直進行著批判性的倫理反思,通過詢問義孝是否真心深愛自己來尋求答案。當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綾音從義孝口中得知,潤子的死很可能與她因不孕不育而被義孝拋棄有關,而自己同樣是不孕不育的體質,這讓她陷入了深深的迷惘與恐懼之中。然而,讓綾音決定繼續這段婚姻且唯一可以依靠的是義孝的一句深情回應:“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對你的愛從未有過絲毫的改變。”[1]這句簡單而深情的告白,為處于混亂與迷惘中的綾音帶來了堅定的力量。綾音正是聽到了義孝的這句話,才決定與他結婚。然而,這份決心并不僅僅是為了與他一起生活那么簡單,更是為了讓自己心中的愛與恨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感情達到某種妥協。于是,在掙扎與恐懼之后,綾音仍保持原來的意愿,選擇與義孝結婚。
基于主要人物在倫理兩難的抉擇之間所產生的復雜迂回的情感以及情愫表露,這有助于我們掌握并梳理埋藏在文本之下的倫理線和倫理結。綾音的倫理困境,是她作為生活在現代社會中處于劣勢地位的女性,在作出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時不得不直面的難題。綾音的思想抗爭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面臨焦灼彷徨、意識紊亂的現實寫照。而綾音最終的抉擇,既是對愛情的執著追求,也是對殘酷現實無奈的妥協,這位原本普通、善良、文靜的成年女性,在面對倫理選擇后,不幸走向了錯誤的道路,這使得綾音作為悲慘女性形象的特點格外凸顯。
三、倫理選擇:隱忍與戕害
構成作品倫理書寫敘事的核心要義即為倫理選擇。文學作品中的任何人物都會面臨選擇,無論是從善的道德選擇還是向惡的倫理選擇。倫理困境和倫理秩序的產生源于倫理選擇的存在,而作品中人物的斟酌與取舍會造成自身倫理身份的轉變。通過把握文學作品中人物作出的倫理選擇和取舍動向,我們可以深入審視人物內心起伏與波動的倫理意識,以及造成倫理兩難的因素,進一步揭示蘊含于文本與文字下的倫理道德屬性。在旁人看來,典雅知性的拼布師同時又是料理家事的賢惠妻子——真柴綾音,卻藏匿著一顆滿懷邪惡的心。這是一場滿懷殺意的“救贖”,所有的怨恨和遭受背叛的憤怒讓綾音失去人性的理智,不僅作繭自縛,也讓義孝在疑慮中離世。
1.人性因子的克制
理性意志(Rational Will)作為個體倫理意識的前提條件和判斷依據。當文學藝術作品內的人物面臨復雜的倫理選擇時,通常會面臨尖銳的思想抗爭。作為社會道德規制下的人所具有的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約束自身言行的理性因子往往會被考驗,而獸性因子由于具有強大的誘惑力,驅使人做出向惡的行動。綾音受理性意志所約束的一面,在地位不對等的婚姻中承受著義孝的自私和輕蔑,這使得綾音的理性意志愈發減弱。“只要他對自己的愛不變,綾音就打算絕不會讓任何人接近凈水器。雖然他對待潤子的那種做法難以饒恕,但只要他愛自己,她甘愿就這樣活一輩子。對綾音而言,所謂的婚姻生活就是守護站在絞刑架上的丈夫的日日夜夜。”[1]在痛苦掙扎過后,她選擇了最為極端的方式,用砒霜來“拯救”對義孝的愛,將毒藥藏匿在凈水器內,寸步不離地照料義孝的生活日常,以防丈夫飲用含有毒性的自來水。悉心照料的背后,是綾音復雜沖突的心境,其中交雜著憤怒和希冀。綾音一再選擇隱忍和接受,不斷受到理性因子的克制,抑制傷害丈夫的沖動。丈夫的愛是促使綾音伸出救濟之手的直接原因,而人性因子與理性因子的斗爭是推動綾音不去實施殺戮而選擇接受現實的根本所在。
女性長久以來一直作為第二性,在以父權為核心地位的社會中處于從屬的被支配狀態。義孝的行為模式背后是現代男權社會的縮影之一,綾音、潤子以及宏美的愛情遭遇象征著女性在日本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從她們的遭遇中可以觀照社會總體的性別趨向。女性長久以來都處于被男性壓制、失語的狀態中,“非理性、無邏輯、思維散漫”等這些被男性價值貶低的女性思維特征,被伊利瑞格視為背離和干擾清晰、單一的父權制象征秩序的力量[5]。在一年期限未至之前,憑借極度頑強的意志力,綾音守在內含毒藥的凈水器旁寸步不離。綾音希望通過對丈夫的“救贖”,讓義孝改變態度,最終能接受自己的不孕,挽救彼此的婚姻。綾音這種無力的倫理選擇是社會中處于劣勢地位的女性在進行倫理選擇時的縮影,這些基于意識層面的倫理選擇反映出人性因子以及理性意志中趨善的感情色彩。
2.獸性因子的涌現
人性因子指的是對人類社會倫理信條的遵循以及對倫理道德的服從;獸性因子作為人性因子的反面,則是對道德教誨束縛的破壞和踐踏,無限地釋放本能的原始欲望。“從倫理意義上而言,人是一種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獸性因子(Brutish Factor)組成。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學作品倫理表述的核心內容。”[6]丈夫對孩子極度的執著以及肆意的出軌和背叛最終導致綾音從愛中孕育出仇恨,綾音試圖用自己的愛去感化義孝,希望把他轉變成自己期待中的丈夫形象,從而使這段婚姻回歸正常軌道。但丈夫的出軌和宏美的背叛讓原本已積累了許多不滿的綾音萌生了殺夫之心。這種扭曲的倫理意識使綾音的人性因子一直處于被獸性因子壓制的狀態。
綾音倫理意識的混亂與義孝僵化的婚姻觀念息息相關。義孝對婚姻中的愛情以及女性懷揣著冷漠和輕視的想法,女性對他而言始終是他者,從未擺脫男性所設置的邏輯準則,處于劣勢和附屬的地位。“定義和區分女人的參照物是男人, 而定義和區分男人的參照物卻不是女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 相對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體 (the subject), 是絕對 (the absolute), 而她則是他者 (the other) 。”[7]從最初的抉擇困境開始,綾音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條錯誤且極端的道路,淪為父權制下被操縱的奴隸。她在倫理道德思想和行為上都缺乏客觀理性的價值判斷和現實依據,根植于內心陰暗面的原始欲望和野性將自己吞噬,同時也將義孝全部毀滅殆盡。
綾音以錯誤的倫理選擇為起點,默許了自己作為婚姻附屬者的倫理身份,并通過家庭內部的異化推翻了正面的倫理意識和價值取向。同時,義孝對倫理責任的缺失和放棄導致綾音遭受了創傷。以綾音為反面例子的描繪,在某種意義上要求現代人將現實的正面倫理準則作為自身行為動機的考量和警示,同時也呼吁女性發揮自然倫理的能動性作用,擺脫既有的附屬思想烙印,尋求女性主義的自由與解放。
四、結語
偵探小說《圣女的救濟》揭露了現代女性在家庭婚姻倫理中面臨的困境,通過展現女性的倫理性反應來批判男女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映射出日本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問題,體現了東野圭吾對家庭及夫妻雙方關系的深刻思考與反思。小說中的圣女綾音不僅試圖“救濟”她的丈夫,同時也渴望丈夫能“救濟”她,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即使這需要她付出極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她不分晝夜地守護著凈水器,不讓他人踏入廚房半步,同時懷著一絲能“救贖”丈夫的念頭。對她而言,這樣做既是救贖,也是贖罪;既是對所愛之人行使圣德的行為,也是向潤子贖清過失的懺悔。小說警示了家庭倫理內核的異化以及對倫理原則堅守的重要性,同時呼吁日本社會消除對女性的隔閡。
參考文獻
[1] 東野圭吾.聖女の救済[M].文春文庫,2008.
[2]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語[J].外國文學研究,2010,32(1).
[3] 駱毅.黑格爾精神哲學視域下的婚姻倫理觀及其現代啟示[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9(3).
[4] 鄒建軍.倫理批評的關鍵術語及其結構圖式[J].黃岡師范學院學報,2021,41(2).
[5] 馬新國.西方文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6]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倫理選擇與斯芬克斯因子[J].外國文學研究,2011,33(6).
[7] 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8] 王芳實.倫理兩難的構成條件及解決路徑[J].華中學術,2019.11(4).
[9] 聶珍釗.災難沖擊、倫理選擇與文學敘事[J].浙江學刊,2022(1).
[10] 王雯倩.社會漩渦中的女性“疼痛”——解讀《圣女的救濟》中的女性形象[J].2013(1).
[11] 狩谷新.メディアミックスによる小説世界の変化:東野圭吾の主人公描寫[J].大分県立蕓術文化短期大學研究紀要,2011(49).
[12] 堀江珠喜.東野圭吾の描く女性たち[J].大阪府立大學紀要,2015(63).
(責任編輯" 余" "柳)
作者簡介:龔" " 衍,南京工業大學。
楊洪俊,南京工業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