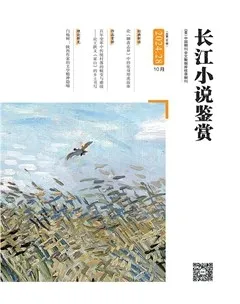論約恩·福瑟《吉他男》中主人公的異化
[摘要] 2023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挪威作家約恩·福瑟的《吉他男》深刻揭示了現(xiàn)代人的異化,表達(dá)了對社會個體生存境遇和人際關(guān)系的思索。吉他男自我身份瓦解導(dǎo)致個體孤獨(dú),家庭角色失敗使親密關(guān)系變得疏離,吉他男最終被社會現(xiàn)代性吞噬,淪為異化者。
[關(guān)鍵詞]約恩·福瑟" "《吉他男》" "異化
2023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獲得者、當(dāng)代挪威文學(xué)家約恩·福瑟的多部文學(xué)作品主題關(guān)注社會中人的困境。《吉他男》是福瑟較早被譯為中文且在中國戲劇舞臺上多次上演的獨(dú)幕劇。該劇人物關(guān)系簡單、語言獨(dú)白簡約、時空場景含混,戲劇舞臺之上的無名吉他男身在夢想與現(xiàn)實的撕扯中。國內(nèi)外研究或從福瑟戲劇美學(xué)視角探究[1],或從劇作關(guān)鍵意象分析[2],或從多元倫理困境視角解讀[3],或從自審感通論視域比較中西戲劇[4],或從音樂敘事視角解讀[5],這些已有研究幫助人們從多角度理解福瑟劇作。本文探析《吉他男》中吉他男的身份瓦解如何導(dǎo)致個體異化、家庭角色失敗如何導(dǎo)致親密關(guān)系疏離,吉他男最終被社會吞噬,成為異化者,該劇揭示了被異化的個體的悲劇。
一、自我身份的瓦解
福瑟劇中人物往往沒有具體姓名,僅被男人、女人、他、她、朋友等代稱指涉,旨在凸顯人物人生遭遇的現(xiàn)實普遍性。艾里希·弗洛姆在其著作《健全的社會》中綜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xué)和馬克思關(guān)于人的社會性學(xué)說,提出“人性異化”的概念,異化滲透到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中[6]。弗洛姆指出,“所謂異化,是一種經(jīng)驗方式,在這種經(jīng)驗中,人感到自己是一個陌生人,同自我疏遠(yuǎn)”[7]。《吉他男》中的主要人物姓甚名誰、來自哪里、歸往何處等問題均以含混的藝術(shù)手法呈現(xiàn),作者以吉他男代指蕓蕓眾生。無名無姓的吉他男最終放棄了追求音樂的夢想,否定自己音樂人身份,體現(xiàn)了自我的異化。
吉他男的異化體現(xiàn)在其音樂人身份在現(xiàn)實的重重壓迫之下逐漸被舍棄。弗洛姆認(rèn)為,“人從自然中走了出來,被賦予理性與想象力,需要形成一個關(guān)于自我的概念,需要說出并感覺到:‘我就是我。’他必須能夠感到自己就是自己行動的主體”[7]。
身份對現(xiàn)代人來說至關(guān)重要,身份缺失導(dǎo)致個體的異化。吉他男曾經(jīng)懷揣藝術(shù)夢想,帶著吉他離開家鄉(xiāng),踏上了追求夢想的旅程。他自幼便展現(xiàn)出音樂天賦,少年時代有成為音樂明星的夢想。他將自己比作一首老歌,而這首老歌卻從未被吟唱過。他在生活的泥潭中掙扎著想要找到“可以訴說我生命的語言”[8],然而成年后,現(xiàn)實挫折與生活的挑戰(zhàn)接踵而至,使他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賺錢幾乎耗盡吉他男的所有精力,他機(jī)械地工作著,已然無心投入藝術(shù)創(chuàng)作。吉他男日復(fù)一日地在地鐵站彈唱,只是期盼著路人能投入三五硬幣能讓他生存下來。然而,彈唱無法養(yǎng)活自己,吉他男在生活的重壓下自暴自棄,直言就是為錢唱歌,承認(rèn)自己是失敗者。吉他男對自己的音樂才華產(chǎn)生了深深的質(zhì)疑,逐漸失去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夢想的追求,變得冷漠和麻木。
吉他男試圖通過音樂尋找自我價值,但最終發(fā)現(xiàn)只是鏡花水月一場空,他不再幻想要創(chuàng)作一首屬于自己的歌曲,自嘲道:“我是個糟糕的吉他手。”[8]曾經(jīng)自己無比珍視的音樂天賦,最終淪為他人眼中的笑柄,這樣的自我認(rèn)知如慢性毒藥,漸漸侵蝕著他的音樂夢想。吉他男曾經(jīng)無比熱愛音樂,然而在音樂夢想無法實現(xiàn)與現(xiàn)實壓力的雙重夾擊下,吉他男最終放棄了夢想,為生計每日奔波,失去了理想,失去了自由而獨(dú)立的精神。
失去自我價值的吉他男掙扎著,甚至寄希望于上帝,渴望通過宗教信仰來解救困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自己,他輕聲祈禱:“現(xiàn)在我將我謙卑的信任獻(xiàn)給天堂的上帝。”[8]隨后他便無奈地笑著搖了搖頭,仿佛是在嘲笑自己將希望寄托于無形的信仰。吉他男的人生在悄無聲息中走向結(jié)束,這是自我失去后他的必然結(jié)局。
吉他男在追求夢想的路上一路坎坷,在現(xiàn)代社會中又孤立無援。他重復(fù)彈唱著屬于自己的故事,一遍又一遍,這是作者對現(xiàn)代社會渴望被救贖和被理解的人物的特寫。該劇的循環(huán)結(jié)構(gòu)不僅在形式上呈現(xiàn)了一種封閉的循環(huán),也在內(nèi)容上反映了人物無法逃脫的異化命運(yùn)[4]。循環(huán)不僅是一種人物異化的形式重復(fù),還深化了主題表達(dá)和情感抒發(fā),激發(fā)了觀眾對于人物處境的同情和反思,成為揭示人物異化狀態(tài)強(qiáng)有力的藝術(shù)手段。
二、家庭角色的失敗
家庭關(guān)系是社會人際關(guān)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弗洛姆認(rèn)為:“人身上只有一種感情能滿足人與世界結(jié)合的需要,同時還能使人保持完整性和個性,這種感情就是愛。”[7]家庭是愛與溫暖的港灣,是個體與世界建立聯(lián)系來對抗異化的重要載體。當(dāng)家庭成員失去了愛的能力,成員就無法從家庭中汲取力量和支撐,家庭關(guān)系趨向異化。弗洛姆指出,“愛總是意味著關(guān)心、責(zé)任、尊重與了解”[7]。家人之愛意味著代際關(guān)系中的責(zé)任和婚姻關(guān)系的尊重,家庭成員間應(yīng)尊重對方的個性與選擇,珍視對方的思想與情感。同時,愛要求家人對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家人要投入時間精力去理解對方的內(nèi)心世界。
《吉他男》家庭關(guān)系異化體現(xiàn)在夫妻婚姻關(guān)系上。戲劇開始時,舞臺上背光而行的吉他男獨(dú)自一人抱著吉他,在孤獨(dú)無助中爬行著上臺,他的身影從模糊到逐漸清晰,第一句臺詞是:“總算進(jìn)屋了。”[8]他不停地喃喃自語,開始傾訴自己的遭遇,他的獨(dú)白坦言“他來這里是因為一個女人,他留在這里是因為一個孩子”[8]。吉他男追憶與妻子相遇、相知的浪漫時光,然而那段甜蜜的往昔已經(jīng)被無情的現(xiàn)實打敗。夫妻關(guān)系在柴米油鹽的生活中漸行漸遠(yuǎn),夫妻感情逐漸消失在雞毛蒜皮的庸俗事務(wù)之中,婚姻家庭關(guān)系也一步步走向異化的深淵。
家庭關(guān)系中夫妻關(guān)系的疏離與隔閡,正是親密關(guān)系異化的體現(xiàn)。由于吉他男缺乏謀生技能,妻子被迫放棄了自己的藝術(shù)夢想,只能去教書以維系家庭的生計。從吉他男的描述中,不難發(fā)現(xiàn)他對妻子的藝術(shù)追求缺乏支持,甚至否定妻子的追求。弗洛姆指出,“如果我愛某人,我會關(guān)心他,也就是說,我主動地關(guān)心他的成長與幸福,而不是當(dāng)一個旁觀者。我對他負(fù)責(zé),就是說,我對他的需要——他說出來的需要,尤其是他未說出口的需要——做出反應(yīng)”[7]。愛被定義為一種主動的關(guān)心,而不是被動的觀望。愛一個人意味著要積極地參與對方的生活之中,關(guān)注對方的需求和愿望。顯然,吉他男并未做到這一點。妻子不停地抱怨他只會成天抱著吉他坐在那里,永遠(yuǎn)也不會賺到足夠的錢來養(yǎng)家糊口,到最后只會一事無成。盡管妻子的教師職業(yè)非常穩(wěn)定,但這并不能滿足她對藝術(shù)的追求。她曾是一位滿懷理想的藝術(shù)家,然而,她的畫作卻賣不出好價格,她不得不向現(xiàn)實妥協(xié),成為一名教師。在夢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鴻溝中,妻子感到了深深的孤獨(dú)與無助。丈夫?qū)λ龎粝氲牟焕斫夂筒徽J(rèn)可,更加劇了她內(nèi)心的苦楚。
在某種程度上,吉他男與妻子的處境頗為相似。他們都有追求藝術(shù)的夢想,而在他人眼中,他們似乎并沒有什么天賦。更關(guān)鍵的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shù)之路,并不能賺到養(yǎng)家糊口的錢,反而使他們陷入了貧困。無論是在地鐵站的演唱,還是賣畫,吉他男和妻子的行為都與他們內(nèi)心對藝術(shù)的追求背道而馳。殘酷的現(xiàn)實迫使他們接受了日復(fù)一日的工作,最初的激情與夢想,在生存的壓力下漸漸褪色。在這種互不認(rèn)可且缺乏愛與支持的家庭環(huán)境中,他們逐漸疏離。
《吉他男》家庭關(guān)系的異化也體現(xiàn)在父子關(guān)系中。福瑟的戲劇中,父親與子女的關(guān)系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3]。《愛的藝術(shù)》中,弗洛姆對自愛與自私做出了區(qū)分。他認(rèn)為自愛者通常也愛他人,而自私者不僅不愛他人,而且還恨自己,“不喜歡自己、不認(rèn)同自己的人常常對自我焦慮異常。他缺乏內(nèi)在的安全感,而內(nèi)在的安全感只能建立在真的喜歡與肯定自己的基礎(chǔ)上”[9]。吉他男并不喜歡自己,也并不肯定自己。作為一名駐唱歌手,他時常會遭受外界的非議。一方面,他既對社會對他的偏見感到十分厭惡;另一方面,他內(nèi)心又認(rèn)為自己的職業(yè)的確低人一等。這種內(nèi)心的矛盾促使吉他男急于逃離現(xiàn)實,擺脫社會帶給他的壓抑感。他的失敗,不僅在于其無法追求藝術(shù)夢想,更在于無法獲得兒子的理解和尊重。他渴望成為一名合格的父親,希望自己的音樂才華能獲得兒子的尊重與敬仰。然而,在陰暗潮濕的地鐵站駐唱既不光鮮體面,又無法讓其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陪伴兒子成長,更不能為兒子提供豐厚的財力支持。這種強(qiáng)烈的自尊和自卑交織的矛盾感導(dǎo)致吉他男與兒子的關(guān)系日漸疏遠(yuǎn)。“兒子為有我這樣的父親而感到丟臉和害臊。”[8]
家庭成員對吉他男作為丈夫和父親角色期望的落差,加重了吉他男內(nèi)心的沖突感,在這樣的雙重壓力下,吉他男選擇了絕望地放棄一切,他說:“我想我用不著再留在這里了。”[8]他放棄追求音樂,放棄當(dāng)合格的父親和丈夫,不僅是他在社會中不斷異化的必然結(jié)果,更是其個體價值和家庭關(guān)系異化的深刻表現(xiàn)。吉他男的獨(dú)白留給觀眾無盡的思考和情感的共鳴。
三、社會關(guān)系的異化
《吉他男》體現(xiàn)了個體在社會關(guān)系中的異化,被異化的人與社會缺乏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積極互動關(guān)系,無法在與外界的互動中實現(xiàn)自我成長和價值創(chuàng)造。與社會脫節(jié)往往導(dǎo)致個體在社會中變得孤立。異化導(dǎo)致個體失去對自己、他人和社會的認(rèn)同,導(dǎo)致社會成員之間的疏離。
吉他男在地鐵站彈唱,希望用這種方式養(yǎng)家糊口,然而鮮少有人為吉他男的音樂駐足,更別說給他錢。弗洛姆的《健全的社會》一書指出,“對于交換的需要是人性中固有的部分,這種需要是現(xiàn)代人的社會性格異化特征的表現(xiàn)”[7]。異化社會中的現(xiàn)代人總是用時間和金錢來衡量某事是否值得投入。異化社會中工作的機(jī)械性和重復(fù)性、人與人之間競爭的激烈性,使人們越來越陌生和疏離,社會趨向于分裂和不穩(wěn)定。
異化導(dǎo)致個體失去了對自己和他人的真正認(rèn)同和理解。喪偶老人駐足聆聽吉他男的旋律,老人與吉他男互為鏡像,老人對于吉他男的凝視是他對自己年輕歲月的回望,吉他男則通過老人預(yù)見自己老年后妻離子散、孤獨(dú)凄慘的景象。在戲劇的第二幕中,這位耄耋老人輕捧著亡妻的骨灰,反復(fù)地呢喃著“就這些”[8]。這低語,不僅是對逝者的緬懷,也是對生命本質(zhì)的哲學(xué)追問。吉他男以音樂慰藉老人,他唱著:“是啊,就是這樣,人生就是這樣。”[8]這不僅是對老人的慰藉,也是對自己生命旅程的反思。兩個孤獨(dú)的靈魂的情感共鳴,更加凸顯了他們在異化社會中的無力感。
老人的駐足雖為吉他男帶來了短暫的安慰,卻難以徹底治愈社會結(jié)構(gòu)對人造成的傷害。異化社會中的人通過尋求他人的認(rèn)可來獲得自我存在感。“異化的人一旦懷疑自己沒有與他人協(xié)調(diào)一致,就會感到自卑,因為他的價值感的基礎(chǔ)是因求同而獲得的獎賞,即他人的認(rèn)可。”[7]在這個層面上,老人的關(guān)注和贊賞,是對吉他男藝術(shù)價值的肯定,也是對他個人經(jīng)歷的尊重。這種同理心在異化的社會中顯得尤為珍貴,它讓吉他男感受到,即便在被大多數(shù)人忽視的情況下,仍有人愿意停下腳步,聆聽他的聲音,理解他的世界。“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是導(dǎo)致人們異化的根源。”[10]老人給他的三鎊,不只是對他金錢的援助,更是對他心靈的慰藉,是對吉他男藝術(shù)追求的認(rèn)可。這份感情如同一股溫暖的潛流,試圖穿透現(xiàn)代社會的冷漠壁壘,不僅是對個體價值和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肯定,更是恢復(fù)人與人之間聯(lián)系的嘗試。然而,盡管老人也為吉他男提供了情感慰藉,讓他在冷漠的都市生活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溫暖,但他們的對話揭示了現(xiàn)代社會中個體經(jīng)歷的異化。
兩位男性的生活軌跡雖各有不同,卻同樣為了愛人來到這座城市,同樣為生計奔波。他們的相互傾訴,表面上是情感的宣泄和尋求慰藉的行為,實則反映了現(xiàn)代人內(nèi)心的孤獨(dú)。面對異化,人們試圖通過向他人傾訴交流以尋求發(fā)泄。弗洛姆認(rèn)為:“向有同情心的聽者傾訴的現(xiàn)代方式則有著相反的目的,其作用是使一個人忘記自己是誰(要是他還有一些記憶的話),消除所有的緊張,與之伴隨的是自我感完全消失。”[7]現(xiàn)代社會中,人們傾向于向他人傾訴以緩解壓力,這樣做的目的往往是讓人忘卻自我。消除緊張感的同時可能導(dǎo)致自我認(rèn)同的喪失,從而加劇個人的異化。
四、結(jié)語
約恩·福瑟的《吉他男》深刻揭示了現(xiàn)代人的異化,表達(dá)了對當(dāng)代社會個體生存境遇和人際關(guān)系的思索。為追求夢想,吉他男離開故土,成為無根的漂泊者。在他鄉(xiāng),吉他男淪為失去身份的人,被現(xiàn)代性社會吞噬,淪為異化者。
參考文獻(xiàn)
[1] Sunde S C.Silence and Space:The New Drama of Jon Fosse[J].A Journal of Performance and Art,2007(29).
[2] 鄒魯路.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約恩·佛瑟戲劇作品中的關(guān)鍵意象[J].戲劇藝術(shù),2010(2).
[3] 王樹福.“既彼此遠(yuǎn)離,又相互靠近”:約恩·福瑟戲劇中的倫理困境[J].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xué)學(xué)報,2024(3).
[4] 汪余禮.體感淵深處,靜透夢影風(fēng)——自審感通論視域下的福瑟戲劇[J].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xué)學(xué)報,2024(2).
[5] 孔瑞,孟慧茹.弦斷為祭:約恩·福瑟戲劇《吉他男》的音樂敘事[J].新世紀(jì)劇壇,2024(2).
[6] Fromm E.The Sane Society[M].New York:Rinehart,1955.
[7]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M].孫愷祥,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
[8] 福瑟.有人將至:約恩·福瑟戲劇選[M].鄒魯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9] 弗洛姆.逃避自由[M].劉林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
[10] 孫振中.從弗洛姆的人本主義理論分析《勿失良辰》中現(xiàn)代人的生存困境[J].新紀(jì)實,2022(2).
(特約編輯" 劉夢瑤)
作者簡介:李慧穎,西安外國語大學(xué)英文學(xué)院。
孔" "瑞,山西師范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為歐美戲劇。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shù)學(xué)重大項目“當(dāng)代歐美戲劇研究”(項目編號:19ZD10);2024年度山西省研究生課程思政示范課程“當(dāng)代美國戲劇”(項目編號:2024SZ1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