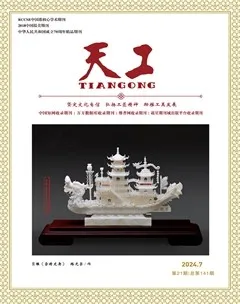傳統手工藝與新時代的碰撞
[摘 要]傳統手工藝是人類歷史的見證,對其進行保護和傳承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以界首彩陶為例,探索其傳承與發展的新路徑,通過分析界首彩陶的特點,結合當代人們的需求、審美趨向、科技發展現狀展開探討,力圖為傳統手工藝的發展解鎖新的方式,促進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當代社會,迸發出新的火花。
[關 鍵 詞]傳統手工藝;新時代;界首彩陶
[中圖分類號]J5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7556(2024)21-0006-03
文獻著錄格式:靳錦.傳統手工藝與新時代的碰撞:以界首彩陶為例[J].天工,2024(21):6-8.
基金項目:安徽省高校哲學社科研究項目“界首市優秀文化在視覺設計中的應用研究”(編號:2023AH050028)。
一、傳統手工藝界首彩陶傳承的意義與社會價值
手工技藝經過數百年的傳承與打磨,最終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最早的手工技藝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距今已有一萬年以上。人類通過加工自然材料,創造出工具和藝術品。這種對自然的探索和改造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因此,傳統手工藝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先民生活狀態的生動述說。
2017年,文化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聯合印發了《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提出建立國家傳統工藝目錄,旨在全面振興中國傳統工藝。
界首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民俗活動。2023年,界首市政府大力推進城市微改造,打造文旅項目,并與安徽大學達成校地合作計劃,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提升城市知名度。借此次校地合作之機,團隊多次到界首市考察,追尋當地的優秀傳統文化足跡,深感人類探索精神的偉大,收獲頗豐。本文以界首彩陶為例,探討傳統手工藝在當下社會發展中的新路徑。
界首彩陶起源于宋代,依據20世紀在淮北柳孜古運河遺址和徐州明城遺址考古中出土的大量界首彩陶殘片和剔花彩陶推斷而來①。界首彩陶技藝由民間匠人代代探索實踐,并在1960年受到當地政府的關注與扶持,重建了界首市工藝陶瓷廠。此外,政府積極培養更多技藝傳承人,選派人才外出學習,在發展中將技藝與藝術融合,培養了一批優秀陶匠,如盧山義、王京勝、盧群山、盧莉華等。2006年,界首彩陶燒制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2017年,田營十三窯古遺址被列為阜陽市第二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該古窯址被列為安徽省第八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盡管政府高度重視,界首彩陶仍面臨技藝傳承人少的問題,可見單純的保護并不能完全解決手工藝傳承的問題。在原本生存環境已改變的當下,應從多層面思考如何傳承傳統手工藝,探索出新路徑。
二、界首彩陶的特點
(一)界首彩陶的獨特工藝與技術特征
1.界首彩陶是高溫陶
低溫陶雖然具有良好的柔韌性和延展性,但時間久了容易破損,且光澤度降低。高溫陶的燒制溫度可達到1000攝氏度以上,使其性質更加穩定,并具有優良的耐腐蝕性和絕緣性。高溫燒制提高了陶器的密度,增強了其硬度,并延長了釉色的附著時間,同時在高溫環境下,釉色呈現出更多變化。
2.獨特的刻畫手法與工具
界首彩陶的紋飾采用剔花工藝,是古陶瓷的傳統技法之一。剔花工藝具體分為留花剔地和留地剔花,在現存的界首陶瓷作品中,留花剔地工藝居多。在燒制過程中,陶器先后飾以兩層化妝土,先是紅色化妝土,后是白色化妝土,晾干后進行留花剔地。燒制后,陶器呈現出“紅地白花”的特殊效果。剔花工藝及雙色著色使陶器表面營造出豐富的層次感。界首彩陶注重粗獷厚重的刻畫手法,表現出北方特有的質樸與力量之美。圖案繪制工具常用自制刻筆,刻筆尖是實心鐵尖,尖端又會磨制圓滑①,鐵尖頂端便于剔除表面一層的化妝土,尖而圓鈍是為了保護下面一層的化妝土不被刺穿。
(二)界首彩陶的圖案
界首彩陶的圖案處理既源于手工藝人對身邊事物的觀察,也借鑒了當地的木雕、剪紙和戲劇作品。因此,器身上的圖案并不是直接再現身邊事物,而是經過簡化處理,并對不同內容有不同的表達。例如,植物圖案的刻畫會將現實中的花草扁平化處理,舍去葉片或花瓣形態的轉折;人物和動物的圖案又會用線條刻畫出人物衣飾的褶皺與動物身上的紋理,以增強裝飾感。如,現藏于界首市博物館的《彩釉刻畫刀馬人紋尊》,整體為“S”形瓶型,瓶頸和瓶底均繪有植物紋樣,植物形態經過提取、歸納,呈現扁平與抽象的效果。瓶體中部鼓腹,繪有“刀馬人”,在線條的加飾下將軍衣飾翻飛,胯下坐騎馬鬃夾風,瓶體上下兩端與中部形成了動與靜的藝術美感。通過形態上的鼓腹和跳脫的圖案,陶體的視覺中心被突顯,人們的目光會在核心圖形處停留很久。三段式構圖形式在現有彩陶和留存影像中非常普遍,顯示出界首彩陶刻畫工藝已形成系統化和穩定的審美風格。
界首彩陶的圖案內容廣泛,早期以花鳥為主,后來逐漸出現人物形象,人物造型的出現可追溯至清末民初。“刀馬人”形象出自當代陶器大師盧山義之手,成為界首彩陶的又一亮點。過去,聽戲是老百姓茶余飯后的一大樂事,匠人在陶器上刻畫人物時,便自然而然地將戲曲與民間故事中的人物及其服飾融入陶罐上。匠人刻刀下的“刀馬人”是沙場征戰的將軍,他們身穿盔甲,背插靠旗,揮舞武器,與座下戰馬融為一體,整體造型夸張,充滿殺氣。每一件陶器上的“刀馬人”都有出處和故事,如《羅通掃北》中的羅通、《穆桂英掛帥》中的穆桂英、《興唐傳》中的秦瓊與尉遲恭等。
(三)界首彩陶上的三彩
在南北陶瓷品類中,界首彩陶的顏色辨識度極高,由米黃、赭紅和翠綠三色妝點。這三種色彩組合在一起,具有濃厚的民間鄉土氣息,經過燒制和掛釉工藝后,呈現出溫潤、喜慶的效果。專家從地域和時間角度考察,認為界首彩陶繼承了唐三彩的遺風②,歸屬于三彩陶系統。界首彩陶對三色的應用非常巧妙,不是簡單的“就型填色”,而是通過雙層雙色化妝土的疊加,形成“圖”“地”關系。“紅地白花”是匠人的精心設計,“點綠”工藝則透露出隨心灑脫,這種緊中帶松的掌控與前文提到的動靜結合形成了高級審美,也是界首彩陶工藝能夠傳承百年的精髓所在。
三、對傳統手工藝傳承問題的全新理解
在信息時代,僅將藏品陳列于博物館是遠遠不夠的。真正的傳承不僅在于保存,更在于活化。要使傳統手工技藝在新時代中繼續存在,必須將其融入現代生活。唯有如此,這些技藝才能真正實現從歷史到未來的傳承。
傳統技藝傳承的根本是什么?一是匠人精神。匠人追求卓越、不斷創新的精神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這種對工作的熱愛與尊重是一種人生態度和追求,這種精神需要傳承。二是傳統技藝。它是文化的一部分,蘊含了古人的智慧。通過傳承傳統手工藝,當代人可以了解文化根源,更加自信,還可以從這些技藝中汲取靈感,不斷創新。
經過對界首傳統文化的實地考察與文獻整理,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點做起。
第一,要正視現實。某些技藝可以傳承,而有些技藝則很難在當下留存。主要原因在于某些技藝在現代已失去實際使用價值。例如,現代人已經有了更輕便且價格低廉的塑料雨披,不會再選擇相對笨重的蓑衣。蓑衣只能走進博物館,或者存在于文字記載中。
第二,可以通過多種媒介,將不同的表達方式進行組合。技藝的傳承不僅僅是對工藝的保存和再現,更是對其內涵和價值的傳播與創新。當下是一個信息爆炸、多元化發展的環境,單一的傳承方式已無法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和接受習慣。以界首彩陶為例,除了在博物館展出實物外,還可以借助數字技術保存和展示相關工藝。如,以界首彩陶為主題的信息圖表設計,通過對信息分層和取舍,以圖文結合的方式介紹了彩陶的制作流程、發展歷史及相關經典故事。信息圖表設計使信息簡化易懂,是當下年輕人更喜愛的閱讀方式。通過大屏幕和小屏幕的傳送,既便捷,又覆蓋率高。再如,界首市IP形象設計以彩陶為核心元素,將界首與彩陶緊密結合。該IP形象將陶器擬人化,賦予它陽光搞怪的性格。隨著界首市文旅項目的推進,它將以吉祥物的身份為游客介紹界首,還可出現在文創產品的包裝中,統一界首的視覺形象。
在探索新的使用價值和表達方式時,彩陶需要重新走入百姓生活。過去,陶器主要作為容器使用,但由于其體量大、難移動,現在已逐漸被塑料、玻璃等材質的容器替代。因此,需要探索其新的使用功能,可以從體量變小、改變形態兩方面入手。花瓶、茶具、繪畫用具(如水滴、筆洗)等是可以探索的新方向。新領域的轉化必然在燒制環節對工藝有所調整,如用電熱燒制、氣體燒制、激光燒制等技術代替老式陶爐;應用數控技術,引進先進的烘干機、磨球機等設備,提高生產效率;在材料挑選、防水處理環節精益求精,解決陶器滲水問題;在茶具領域,彩陶制作要采用釉下彩,避免鉛、鎘等重金屬元素的使用,符合健康環保標準。
同時,彩陶還可以繼續延續擺件創作方向,但需結合當下人們的審美觀念作出改變。著名雕塑藝術家閆玉敏先生將敦煌莫高窟藝術元素、古代音樂與界首彩陶相融合,創作出精美絕倫的《水月觀音》《十二樂俑》等雕塑作品。《十二樂俑》是一組手持樂器的仕女小型擺件,擺放在一起,可以呈現古代音樂演奏的即視感。每位仕女的神態、動作、手持樂器各不相同,惟妙惟肖,充滿意趣,深受觀者喜愛。
經過一代代傳承人的不斷嘗試,界首彩陶技藝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導入算法后,將技藝與現代設計和工藝融合,研制出鏤空、瓶中瓶、穿軸轉動等新技術,使陶器更加靈動,增強了界首彩陶的獨特性。
數字技術的發展雖然擠壓了傳統手工藝的發展空間,但也為其帶來了新的機遇。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大數據平臺掌握消費者的喜好;應用數字化設計軟件進行產品設計,獲得數字模型,嘗試將陶土與其他材質結合(如玻璃、竹絲、皮質等),快速獲得可能性參數;采用數字化管理,借助計算機輔助管理軟件,根據產品周期數據,提高生產效率 ;利用虛擬現實技術、交互媒體和電子商務平臺展示技藝,并向全球消費者推廣,形成新的購買力。充分借助不同媒介的優勢,實現傳統手工藝的創新。
第三,技藝的拆分與重構——從傳承到創新發展。在了解數字技術的潛力后,我們意識到,不僅要思考技藝的傳承,還要探索其新發展。如將技藝拆分和重構,這種打散重構的方式,不僅拓展了技藝的應用范圍,還賦予了其全新的生命力。我們將“刀馬人”的形象、界首彩陶的三彩以及經典圖案拆分開來,分別提取造型元素、顏色和圖案,重新組合應用于生活中。
我們從界首彩陶的特點入手,將“刀馬人”圖案和陶器色彩單獨抽離出來。如,以“刀馬人”的形態為創意點設計文創產品“驚喜盲盒系列”。盲盒人物的形象和姿態來自陶器上的人物造型,但簡化了衣紋和配飾的線條,并加入了電子吉他、滑板等現代元素,將緊張的戰爭氛圍轉化為輕松的場景,讓古裝與現代元素碰撞出火花。
我們還嘗試提取“刀馬人”中馬頭的局部紋樣,設計成胸針;將陶器上的經典花卉紋樣用于木梳設計中;將彩陶的三彩應用于絲巾和文具的配色中。手機殼設計便是提取彩陶中的經典三色,附于幾何色塊,形成馬、魚等抽象形象。這樣的設計不僅提升了產品的內涵,也使消費者通過這些設計重新認識界首彩陶,這是傳統技藝發展新思路的一種體現與嘗試。
此外,我們將色彩與彩陶的經典圖案進行組合,設計出彩陶燈具系列、文創腕表系列和陶器小擺件等有趣的文創作品。當這些方案轉化成商品時,可以搭配界首彩陶的信息圖在博物館、旅游景點、文創店等地方售賣。這種不拘泥于陶器本身的延伸形式,能輕易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拓展了界首彩陶的應用領域,讓人們看到了傳統手工藝發展的更多可能性。
四、總結
在探索傳統手工藝新發展的道路上,我們不僅持續深化對區域文化的收集、整理,還積極將新科技融入其中,以拓展探索之路。在傳統手工藝與新時代的碰撞中,我們見證著創新火花不斷迸發。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時尚元素相結合,促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種融合不僅帶來了產品形式和設計理念的更新,更引發了對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的重新思考。
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創造,優秀傳統文化和精湛的技藝將持續滲透到時代的脈搏中,延綿而鮮活。我們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迎接新的挑戰和機遇,讓傳統文化在當代煥發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參考文獻:
[1]韓熙,盧赟,修亞男.數字時代的傳統手工藝:危機、轉型與創新路徑[J].上海工藝美術,2024(1):41-43.
[2]界首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界首縣志[M].合肥:黃山書社,1995.
[3]高峰.界首戲曲人物紋飾彩陶的成因及其藝術特征[J].裝飾,2012(1):116-117.
[4]郭延龍,李碩.非遺傳承視角下宣紙制作技藝文創設計研究[J].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2,21(4):72-77.
(編輯:高 瓊)
注 釋:① 許政:《回顧與反思:界首彩陶的歷史源流與傳承現狀》,《藝術生活-福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22年第1期,第51-56頁。
注 釋:① 黃漾:《界首彩陶》,安徽科技出版社,2020。
② 高峰:《界首戲曲人物紋飾彩陶的成因及其藝術特征》,《裝飾》2021年第1期,第116-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