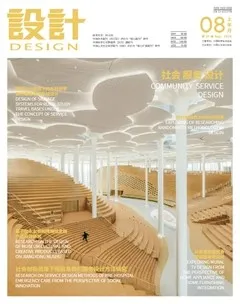設計社會學視角下20 世紀80 年代印花紋樣設計研究












摘要:為探究20世紀80年代印花紋樣的設計關系,以期為時下設計面對沿用題材,國外流行趨勢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設計提供借鑒。文章從設計社會學視角,對印花紋樣設計的社會關系、本體特征、設計社會學價值展開研究。20世紀80年代的印花紋樣設計發展受國家重視、市場追求、理論體系構建的影響,在題材、造型、色彩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的時代風貌。反映出時代工藝技術的發展、政策導向、大眾審美、更是民族和時代進步的縮影。
關鍵詞:20世紀80年代;印花紋樣;設計社會學;社會關系;設計特征
中圖分類號:J5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069(2024)15-0053-05
引言
自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紡織業進入蓬勃發展期,紋樣設計水平進步明顯,設計人員在國家大力支持下走出國門,遠赴歐洲等地學習和了解信息,加之引進成套印花設備,設計觀念和印制手段迅速提升,新的印花派路不斷涌現,為爭取訂單和出口創匯做了很大貢獻。不僅是面料花型設計,服裝、裝飾綢、企業技術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數百個品種和上萬只花色暢銷于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國內外市場空前繁榮[1]。20 世紀80 年代的印花派路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探索出自己特殊的設計方式和風格特點,并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承擔其獨特的藝術使命,記錄這一時期印花紋樣的設計轉型過程和紡織行業的現代化進程,是我國現代紋樣設計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印花紋樣與設計社會學概述
(一)印花紋樣的概念界定
20 世紀70 ~ 80 年代,設計人員通常對于紡織品流行花樣進行分析,指導設計生產任務,擴大銷售量。印花紋樣在其中占重要地位,其指將顏料、染料通過技術手段施印在紡織品上從而獲得各種花形圖案,并形成具有明顯特征性的一種類別和風格[2]。故在此說明,下文提及的“印花紋樣”“印花派路”“花色樣式”等詞均在討論范疇內。
(二)從“線形設計史”轉向“設計社會學”
設計的概念誕生于17 世紀的英國,對于設計史的研究初始就因設計作品的藝術特征而依附于藝術史。20 世紀30 年代,尼古拉斯·佩夫斯納的《現代運動先驅》確立了從藝術史角度以現行編年史為脈絡的敘事模式,直至20 世紀80 年代,阿德里安·福蒂的《欲求之物》作為設計史研究的轉折點,不局限于以風格和形式主義研究的設計史軌跡,“社會結構”跳脫出“背景”作為研究的架構,設計史顯現出向社會學交織的趨勢[3]。伴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滲透,設計社會學應時而起,認為設計問題是探尋人、物、社會三者間的聯系來追溯設計的本質,在構建設計理論體系的同時更著重其設計實踐方面的指導意義。
(三)印花紋樣的設計社會學研究
法國社會學者皮埃爾·布迪厄首次在社會學范疇提出“文化資本”的概念,并在具體研究中將資本和場域、習性理論統一起來,指出社會學的探詢對象是由政治、經濟、文化場等多個構成的場域。習性是人與場域互動的必然產物,連接場域和文化資本,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形成具有一定傾向性的過程,像一種設計實踐行為。文化資本是各場域長期培育的結果,是場域在行動者個體的客觀化[4]。當代設計正暗合了布迪厄的分析,設計作為行動者的一種實踐行為(習性),必然與社會結構(場域)形成互動關系,而因設計的人文屬性,兼具文化資本的特質,在構思、生產、流通中形成價值集合體。這為紋樣設計研究提供了另一個維度的介入方式(圖1),文章結合《百花》《流行花色》《中國絲綢印花圖案集》等資料進行實證研究,最終整理了由上海第七印綢廠、山東濟寧印染廠等生產的明確時間標識為20 世紀80 年代的樣片和圖像共500 款,從印花紋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和本體題材、造型、色彩特征入手分析其產生的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
二、20世紀80年代印花紋樣設計發展的社會關系
(一)工貿部門重視下出口創匯的需要
建國之初,我國紡織業發展與出口貿易岌岌可危,為更好地創匯,政府提出以對外貿易為主的發展策略,同時注重“設計、生產、貿易之結合”,三者由國家和產業聯合起來,并建立了報樣、選樣、交易的機制。改革開放后,這種高度集中的成交制度逐漸解體,轉向更加自由的來樣、仿樣制度。政府扶持紡織業進行改革,20 世紀80年代出口創匯持續以較高的速度增長,紡織工業生產總值從1980 年至1985 年增長48%,1986 年上半年外銷總值更打破了歷史水平[5]。1987 年,我國紡織品出口額達88 億美元,超過日本和中國臺灣成為世界五大紡織品出口國家和地區之一[6]。從這些資料和數據可以看出,紡織品在花色與品種上不遺余力地創新,在出口創匯方面大有作為。
(二)流行方法與市場審美的重視
20 世紀80 年代是印花圖案創作的一個高峰期,由于我國出口對象的轉變、設計師個人意識的提升和及時領會市場行情的需要,我國開始擴大與國際的交流,訂閱各種國外樣本,同時引進美國“PANTONE”色譜,還派設計人員常駐國外調研。如持續6 年參與德國法蘭克福的INTERSTOFF 國際織物展覽會并傳達信息到國內,以便行業內全面了解博覽會的情況[7]。探尋到國外流行趨勢后,編印了數冊新樣本,在新品類、新花樣的派路、配色、表現形式等方面都明確指出其適銷對路。值得注意的是,新樣本中豐富多彩的現代裝飾藝術、后現代主義、抽象派風格對于國內市場審美趨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人們的審美心理受新樣本的趨勢影響與國際流行色彩、圖案接軌[8],對于傳統具象、繁瑣的印花紋樣逐漸失去興趣,追求自然輕松、個性醒目的設計樣式。
(三)產業升級與理論體系構建
工藝技術和設計觀念制約著紋樣的格局,影響著最后的實樣效果,20 世紀80 年代我國致力于引進先進印染設備、建立新的經貿關系、注重設計理論的搭建,為設計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顧前20 年,印花技術落后導致花樣產生許多病疵,直到新型印花機和種子膠的引進才打破局限,設計師不但不受限制設計大塊面圖案和精密紋樣,操作上更為便捷。圓網印花機的普及更是完善了平網印花的接痕缺陷,為圖案設計開拓了更廣闊的天地。另外,相關設計院校專業開始恢復與擴招,及時調整課程建設理性教學模式,撰寫相關圖案專著及論文,以期構建國內設計理論體系。從1982 年至1986 年期間開展的3 次全國“高校圖案教學座談會”以及《絲綢》《江蘇絲綢》等雜志刊登的眾多理論設計方法探討中可一窺彼時的探索歷程。
三、印花紋樣設計本體特征分析
(一)印花紋樣的題材設計。
1. 異峰突起的幾何紋樣。20 世紀80 年代初,受日本、中國香港傳入的“三大構成”影響,具有現代設計構成美的幾何圖案發展迅速。在收集的500 張樣片中,幾何題材紋樣106 張,占總數的21.2%,基本印證了《日本紡織新聞》1985 年“條格在近二年內似乎一直占優勢”的報道[9]。分析發現,幾何花樣設計中往往以點、線、面的構成方法獨立排列或與其他題材進行組合,在彼時印花設計師的手下以超乎尋常的手法表現。
按照元素題材設計具體可分為5 類:(1)點格條子排列。采用單獨或多種點、格子、線條元素進行搭配設計,遵循秩序感、節奏感、韻律感,展現具有規律性的設計效果,出現頻率較高,如圖2(a)所示;(2)不規則元素排列。利用不規則幾何、平面花型等連續或散點式組成,較單純的點格條形態更加豐富,單體表現更為強烈,如圖2(b)所示;(3)平面構成形式。按平面構成設計原理,基本形可劃分成正負形和漸變,依照不同排列的方法,產生放射、分割、聚散、扭曲、密集等多種效果,如圖2(c)所示;(4)抽象塊面組合。此種設計形式由抽象畫派衍生,擯棄客觀的自然形象,以抽象色彩和穿插線條對畫面進行理性分割,大膽運用基本色和基本形,極富張力和沖擊力,如圖2(d)所示;(5)“混搭式”組合。通過和字母、中小型花卉、卡通形象、民族圖形等元素交叉,扁平式堆疊設計,視覺效果上更具有趣味性,如圖2(e)所示。
2. 復古回歸的民族紋樣。20 世紀60 年代因意識形態問題將國外民族元素“雪藏”,直至對西方設計思想、生活方式得以“解封”后,復古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浪潮席卷整個市場,開始追求奇裝異服,提倡個性、自由。在20 世紀80 年代印花紋樣題材中有大量的外來紋樣和少量的中國民族紋樣,各類民族紋樣皆區別于以往傳統寫實性和程式化的設計模式,強調主題想象性和創造性,追求平面化、線條感。
經過歸類分析,在民族題材選用上表現為:(1)多樣形態的佩茲利紋樣。佩茲利紋集精美古典于一體深受大眾喜愛,曾一度成為青島當地的“馬路服”紋樣[10]。其有多種設計形態,純色勾線、單色反地、多套色或輕松隨意的塊面表現,外造型酷似火腿,內部以花朵、幾何圖形裝飾,如圖3(a)所示,配色豐富,包容性強;(2)獨特骨架的波斯紋樣。波斯紋的特殊之處體現在其與眾不同的排列方式,如圖3(b)所示,通常將植物或幾何元素嵌入到波形、圓形連續狀骨架中,圖案呈現效果繁復有序,用色華麗高雅;(3)熱情張揚的夏威夷紋樣。主要以扶桑花的各類造型為設計主體,四周點綴椰子樹、魚類貝殼、海上帆船等形象,用自由線條和泥點打破規整的外輪廓,敷色十分艷麗張揚,如圖3(c)所示;(4)簡中求變的東方紋樣。這期間有少量中國的龍鳳、瓷器、青銅器,如(圖3(d),與傳統民族紋樣不同的是,其內外造型都更為簡化、抽象,不再采用寫實、繁瑣的表現效果,這是為市場需求作出的相應調整。此外,還出現了將佩茲利紋與波斯紋常見元素共構現象,統一而無違和感,實現民族文化的融合。
3. 抽象發展的花卉紋樣。在整理的樣片中,花卉題材為主共213張,占總數的42.6%,可見是20 世紀80 年代最常用的題材之一。但彼時傳統寫實花型較少見,花卉題材在吸取了“幾何形式法”的某些因素后,開始區別于純自然風格逐漸向現代性審美蔓延,呈現出抽象設計的趨勢。在花卉品種的選用上,除可辨認的品種外,亦有身份融合的作用。
按題材設計品類可分為:(1)常規品類。采用明確品種的花形進行單獨設計,易于辨認的有月季、芍藥、牡丹、梅、蘭、竹、菊,還有一些外來品種,如“馬蹄蓮”“仙客來”“卡特蘭”等,精準地傳達不同花種的設計寓意,如圖4(a)所示;(2)似花非花。此類花型與純自然的生長形態差異較大,設計時往往提取花卉特征進行創意性的加工變形,如圖4(b)所示,相較清晰、完整的花卉形象更受歡迎,不少客戶都認為花型不要太寫實,最好有“似花非花”的感覺[11]。(3)雜糅品種。發現許多花樣并沒有明確的花的“身份”,通常提取多種花卉品種特征進行結合,將不同花卉的特點糅合,呈現出共同的屬性,如圖4(b)所示,提取月季、芍藥、牡丹的造型和輪廓,在花瓣和葉子上難以區別究竟是何品種,呈現出抽象的設計語言。
(二)印花紋樣的造型特征。
1. 抽象手法的漸進使用與傳統寫實性驟減。20 世紀50 ~ 60 年代,由于片面接受國外“現實主義”藝術思想,圖案設計上禁令非具象花樣,直至20 世紀80 年代西方抽象思維進入中國,推動了花樣設計的轉向發展。傳統的寫實花卉充其量僅作為“保留劇目”起著點綴的作用[12]。以花卉題材為例,將自然生長形態的遵守、體積感減弱、光影塑造層次堅守等作為判斷標準,統計發現抽象性花卉紋樣為161張,占對應總數的75.6%,抽象趨勢顯而易見。
選取20 世紀70 年代與80 年代的代表性花樣進行對比發現,抽象手法設計的具體表現可分為3 個方面:(1)骨架構成混合穿插,70 年代規整的骨架逐漸瓦解,主體構成元素間邊界相互重疊明顯,較少出現清晰的散點式個體元素,互動性表現得更為強烈;(2)內外輪廓線條隨性,單體元素外輪廓與內在骨骼展現更為松弛,不拘泥于本身的具體外形,提取元素特點進行創意性設計;(3)表現效果敏銳自如,往往用較少的筆墨層次、靈活的塊面線條、泥點拓印等手法呈現出虛實共構的藝術效果,更具有感染力。如表1 所示,分析了蝴蝶和牡丹花元素的相似造型在骨架構成、輪廓特征、表現效果三方面的形態呈現,正符合這一時期的追求抽象的思維方式。
2. 織印結合的搭配方法。20 世紀80 年代提花加印花的服裝較流行,外銷花樣中對于織印層次感追求的傾向性較為明顯。用于提花的紋樣多是抽象或不規則的幾何塊面,印花的設計方法比較靈活多變,通常以清地占多數,不至于將提花的效果掩蓋,憑借織印二者的交叉,相互映襯,形成一種特殊的閃光效果。
在提花與印花的畫面分布、層次效果和趨向設計上都有相應的設計方法,具體為:(1)織印塊面設計分為塊面織大印小(5(a))、塊面織小印大(圖5(b))、織印塊面一致(圖5(c)),往往根據元素的特點進行考量,展現出對比與融合的效果;(2)織印兩者的設計層次亦可分為層次織少印多(5(d))、層次織多印少(5(e))、織印層次相當(5(f)),通過提花與印花花型大小和層次變化形成多種不同的搭配方式;(3)趨向設計大多將提花與印花花形形成交叉結構,如圖6 所示,提花部分的大花和圓孔狀幾何配以印花部分的小花形成扁圓形走向,橫向提花配以縱向印花,反之亦然,兩者協調一致,造型搭配得當。
3. 總組織形態的沖破。四方連續結構容易形成“程式化”之感,同時,為適應國際流行與時裝化發展,20 世紀80 年代的設計師們企圖在圖案總組織造型上尋求新的突破,在此需求下提出了“件料花樣”和大花回設計。山東煙臺絲綢印染廠為此成立了新品種開發科,配備優秀花樣設計與服裝設計師專門從事大花回設計與獨幅花樣設計[13]。
(1)大花回紋樣起到調劑和對照作用,花型偏大,用色大膽。印花設計時排列較稀疏且穿插靈活,留出較多地色,花樣顯得非常突出、舒暢,同時在花色上常用深綠、玫紅、元色、深紫等為地色,外花形上往往用各色線條和泥點集結來形成,對比恰到好處,如圖7;(2)獨幅紋樣設計往往考慮到服裝應用部位的整體效果,一件服裝從上到下,盡量避免簡單的重復,即使采用一般匹料花樣制成的服裝,也會采取拼裁的方法,用同花樣兩者配套色制成,以供市場需求。經分析歸類,獨幅式的連續件料設計按照造型呈現方式大致演化為6 類,重心式、獨枝式、過渡式、傾斜式、組合式、輕重式,見圖8,圖案和顏色的位置設計處理更妥帖合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件料的印花方式,不僅用于高檔服裝,在化纖、針織和各類織物上已普遍采用。
(三)印花紋樣的色彩調性。
1. 流行色的區域差異與理性應用。配色與花樣的關系密切,相輔相成,在20 世紀80 年代的對外貿易中,花色直接影響到印花品種的成交額。從成交花色與樣本分析看,不同對銷地區對國際流行色的概念、途徑各有相異,且我國在國際流行色的分析中形成了理性的本土化應用。
從適銷地區看,歐洲對于流行色表現較為敏感,我國香港地區則比較保守,特別是“本港”生意客戶,不易接受特別鮮艷的色彩。同時,根據“設計、打樣、成交、交貨”的周期,設計的色彩應遵循下一年同季度的流行色,但在一些交貨周期短的花樣上則采納當下地區流行的色彩。另外,通過駐外調研等信息的傳入,我國開啟了自有流行色的趨勢發布,1981 年中國絲綢流行色研究中心和1982 年中國絲綢流行色協會成立后,擬定了1983 年春夏季的24 種流行色方案。其他省市也追趨逐耆,如圖9 所示,為河北紡織品流行色調研組發布的1985/1986 年秋冬河北紡織品流行色,打破了以往沉悶的色調,分成朝露色、正午色、原野色、夜幕色4 類,以便設計時的合理配比。另外,“對于國際紡織品市場每年推出的各類流行色的應用一定要結合實際市場進行分析,因為市場上的宣傳成分較大與實際消費仍有一定距離[14]”,這體現了國內對于不同流行色宣傳的理性分析。
2. 活躍性色調與常年適銷地色。回顧20 世紀60 ~ 70 年代的印花設計,受認知水平和工藝的限制,較少采用明亮的色彩,深沉的“咸菜色”大行其道,伴隨設計思想轉變和提升,色彩運用有了新的突破,不再局限于“灰暗即高雅”的觀念,同時由于個別往年流行色的延續,在地色的運用上形成了常年適銷的色彩。
在20 世紀80 年代的花樣設計中,色彩傾向較為明顯。通過對比20 世紀70 年代與80 年代樣本中的粉色色調(圖10),可以反映出這種明快的趨勢,在明度、純度和對比度上都有了明顯的提升。此外,1985 年倫敦哈羅茲絲綢宣傳月系統地歸納了歐美流行的飽和純色,寶藍、翠綠、玫紅、鵝黃、大紅是主要色彩,并常常與黑色相配形成雙色花樣[15]。在地色應用上,往往會保留幾個往年的流行色,從大多數消費者實際情況考慮,只需換掉衣柜中的幾個色彩,就大致可以“跟上潮流”了,因此形成了常年適銷的色彩。經過樣本分析抽樣歸類,如圖11 所示,為常年適銷地色的應用占比,其中元色占比最大,單花卉紋樣中有45 款,占比21.18%。紅色其次,占比18.91%,藏藍、白、咖啡、米色等色彩同步出現,是設計中主要采用的地色[16]。
四、印花紋樣的設計社會學價值
(一)作為提升經濟效益與扮演時尚載體的角色
印花紋樣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各個角落,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見證者,其本體設計特征僅僅作為“表象”,本質是受到數個場域中的社會結構影響下,形成的各類設計社會學價值。20 世紀80 年代的紡織業已不同于往常求速求量的生產模式,在題材、造型、表現手法、色彩方面都與對銷地區的審美喜好、流行時尚所適應,持續創造出新穎的花樣,如對于抽象花樣的變形運用、件料印花的服用性考量以及明亮色彩的適當調配,皆回應前沿時尚的流行趨勢。并通過承擔時尚載體角色產生相應的經濟效益,刷新紡織出口額成為國內第一大類出口產品,甚至占據全球貿易的8%,在創造經濟效益方面頗有作為。
(二)文化差異的包容及傳遞先進審美觀念的媒介
20 世紀80 年代抽象思維、后現代主義、構成理念等西方文化大肆涌入,人們開始追求情感宣泄與釋放,紋樣能夠彰顯不同的審美個性,抒發內心的情緒,同時也起到維系和傳播民族文化的作用。這種包容與傳遞的媒介借用設計表現要素系統性的展現,即在紋樣設計時要在注重中華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傳承創新,吸納外來文化與國外藝術的優點,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如遵循形式美法則對中國特色元素的創新應用,打破固有條框采用自由隨性的線條,結合異域紋樣進行現代化轉譯等亦包含優秀審美文化本質,對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消費者的審美引導有著重要意義。
結語
20 世紀80 年代我國的印花設計逐漸走上世界性舞臺,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局面。在研究實物圖像中發現除花卉紋樣的流行外,幾何紋樣和民族紋樣也成為創匯的重要題材,受西方思維影響抽象性成為其最大的造型特征,架構工藝解決后流行大花回和獨幅紋樣,同時也將提花和印花融合形成別具一格的造型。而色彩的作用更加鮮明,遠看色近看花,彼時通過分析系統性的流行色情報創造出適銷的花樣,同時做到理性應用。彼時流行的花色經過幾十年的變遷,仍有相當一部分表現形式獲得沿用,有的甚至還大行其道,而這表明新舊之間的某種聯系和發展規律,可以見得,印花設計的發展始終與工業發展、科技進步及大眾審美水平的提高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與此同時,這也是設計人員創新求變、結合生產、研究市場不懈努力的過程。
基金項目:浙江理工大學浙江省絲綢與時尚文化研究中心基地成果;2023 年浙江省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計劃(新苗人才計劃)——“時尚審美視域下江浙滬地區絲綢文創產品的創新路徑”項目(2023R406070)
參考文獻
[1]楊殿吳.蘇州絲綢產品的發展和預測[J].江蘇絲綢,1983(02):48-58.
[2]鄭巨欣.中國傳統紡織印花研究[D].上海:東華大學,2005:12-13.
[3]阿德里安·福蒂. 欲求之物:1750 年以來的設計與社會[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4]張妤靜.社會學語境下設計研究與設計管理的多重使命[J].包裝工程,2018,39(20):39-42.
[5]張園和,李林.抓住有利時機 擴大出口創匯 振興我國紡織工業[J].經濟工作通訊,1987(04):30+29.
[6]伍蔭廷.紡織企業集團是擴大出口創匯的一支生力軍[J].上海企業,1988(07):4-5.
[7]朱富澄.產品開發要重視技術經濟的結合[J].北京紡織,1988(06):18-21.
[8]范存良.溝通信息和貿易的橋梁——國際博覽會簡介[J].絲綢,1985(12):13-14.
[9]吳文寰.分析國外紡織樣本探索品種發展方向[J].江蘇絲綢,1985(01):47-49.
[10]孫偉.山東70/80年代印花特點及對設計教學的啟示[J].絲綢,2008(09):21-24.
[11]范存良.花卉與絲綢圖案[J].江蘇絲綢,1982(02):40-48+51.
[12]范存良.絲綢圖案設計中的抽象手法[J].絲綢,1987(09):35-37+3.
[13]尹振卿,唐緒山.絲綢行業如何適應時裝化需要[J].絲綢,1985(07):4-5.
[14]龔建培.絲綢設計中流行色發展的歷史情境、敘事主體及模式研究(1960—1985年)[J].絲綢,2021,58(03):114-119.
[15]范存良.良好的開端 有效的嘗試——深圳印花綢洽談會筆記[J].絲綢,1986(12):11-13.
[16]陳生甫.流行性·藝術性·服用性——外銷印花圖案的特點[J].絲綢,1984(0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