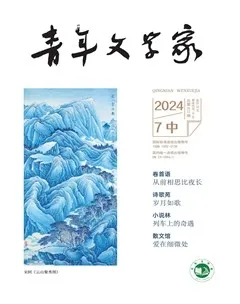后現(xiàn)代主義視域下《堂吉訶德》的敘事藝術(shù)研究

《堂吉訶德》是由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創(chuàng)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講述了一位名叫吉哈納的鄉(xiāng)紳,雖年近五十卻因沉迷騎士小說而決定開始模仿騎士小說中騎士的言行舉止,他的這種模仿行為在現(xiàn)實里卻受盡了謾罵、毒打和嘲弄,最終他在病床上幡然醒悟的故事。作者在敘述這樣一個想象、記憶、幻覺和現(xiàn)實相互雜糅的故事時,采用了荒誕不經(jīng)的敘事語言、戲擬反諷的敘事手法、重構(gòu)與解構(gòu)雙線并行的敘事結(jié)構(gòu)和充滿不確定性和不可靠性的元敘述方式。這樣顛覆傳統(tǒng)的敘事在本質(zhì)上歸屬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廣泛興起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敘事方式,后現(xiàn)代主義敘事是指去中心化的、消解意義的和反宏大的敘事。因而,本文將在后現(xiàn)代主義視域的觀照下,對《堂吉訶德》這部小說所采用的敘事語言、敘述方式、敘事結(jié)構(gòu)和敘事手法進行一個詳細的分析與研究。
一、敘事語言的后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
在《堂吉訶德》這部小說中,塞萬提斯常常擅于借助小說人物之口來講出一些荒誕不經(jīng)的語言,因而人物語言的荒誕性也成為小說明顯具有后現(xiàn)代性的第一個表現(xiàn)。堂吉訶德作為小說的主人公,經(jīng)他之口講出的頗具荒誕性的話語是最多的,尤其是在他談到讓他陷入極度瘋狂的騎士道時,他所說的話不僅夸張離譜,甚至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睜眼說瞎話的地步,這里主要選取小說中堂吉訶德講的比較典型的充滿荒誕性的話語來進行分析。
堂吉訶德講的第一段比較荒誕的話是當(dāng)他決定像騎士一樣去游行時,他自言自語的這段話,他說:“假如我倒霉或走運,在什么地方碰到某個世人,這對游俠騎士是家常便飯,我就一下把他打翻在地或者攔腰截斷,或者最終降伏了他,我讓他見一個人很好?我讓他進門跪倒在我漂亮的夫人面前,低聲下氣地說,‘夫人,我是巨人卡拉庫利安布羅,是馬林德拉尼亞島的主人,絕代的騎士堂吉訶德將我打敗了,并且命令我到您這兒來,聽從您的安排。’”這段話的荒誕性首先在于將近五十歲瘦弱的堂吉訶德根本不具有把敵人打翻在地或攔腰截斷的力量,并且在后面的故事中也證明了他的確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反而他自己常常才是那個被打翻在地還差點兒被攔腰截斷的人;其次,當(dāng)時的他并沒有夫人,當(dāng)然也就不存在漂不漂亮一說,另外現(xiàn)實中也不存在既是巨人又是島主且又被堂吉訶德所降伏的這樣一號人物,由此可見堂吉訶德所說的這段話是多么荒誕與無據(jù)。從堂吉訶德的口中說出的又一次讓人感覺無比荒誕的話是在堂吉訶德來到一家被他誤以為是城堡的客店時,他把女仆稱為高雅的嬌女,把店主稱為卡斯利亞諾大人,把腳夫稱為騎士,把與腳夫的爭執(zhí)稱為戰(zhàn)爭,他的這種稱呼不僅夸張,還給人一種睜眼說瞎話的感覺。堂吉訶德的第三段頗具荒誕性的話是他對一個請求得到他徹底幫助的孩子說的,在他阻止了一個殘暴的地主毆打并拒付一個孩子的工資后,孩子告訴堂吉訶德只要他離開后,地主肯定會變本加厲地毆打他,甚至剝掉他的皮時,堂吉訶德是這樣答復(fù)那個孩子的,他說:“只要我讓他聽我的,他就得以騎士規(guī)則的名義發(fā)誓,他保證會給你工資。”之所以認為堂吉訶德說的這段話靠不住,是因為他所謂的騎士規(guī)則只存在于小說里,現(xiàn)實中沒有人會尊崇這種規(guī)則,更不必指望一個殘暴成性的地主會遵守他說的這種規(guī)則,他說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話不僅沒有幫助到孩子,反而使他遭到了地主更加嚴厲的毒打,孩子也因此憎恨堂吉訶德。另外,小說中堂吉訶德的侍從桑丘·潘沙以及捉弄堂吉訶德的各種人物,甚至包括小說的作者以及小說的故事的敘事者都講著諸如此類的充滿荒誕性的話語,此處不再贅述。總之,《堂吉訶德》這篇小說的敘事語言總的特點是荒誕的,這種荒誕具有明顯的消解語言意義的作用,體現(xiàn)出了后現(xiàn)代主義敘事語言的典型特征。
二、敘事手法的后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
《堂吉訶德》這篇小說敘事手法的后現(xiàn)代性表現(xiàn)為作者塞萬提斯對戲擬、反諷兩種敘事手法的靈活運用。
(一)戲擬手法的采用
戲擬作為一種敘事手法,是指作者在寫作時刻意對某一作家或某種類型化的作品的敘事手法進行模仿,從而使作品產(chǎn)生喜劇或嘲諷的效果。因此,戲擬又被稱為滑稽模仿或戲謔模仿。《堂吉訶德》這部小說戲擬手法的運用表現(xiàn)在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對已有騎士小說的寫法進行了模仿。首先,作者對舊有騎士小說中的人物設(shè)定進行了模仿,他通過幻想的方式打造成了騎士小說中具有騎士精神的一位游俠騎士,不僅賜給他“堂吉訶德”這樣一個符合騎士氣質(zhì)的名字,還給他配備了騎士游行必備的一切裝備,一身甲胄、一頂頭盔,一副長矛,一匹叫羅西南多的馬以及每個騎士身邊通常都會帶著的一個侍從,接著又塑造出了每部騎士小說中必然出現(xiàn)的另外兩種人物形象,騎士的情人杜爾西內(nèi)婭和與騎士進行斗爭的各種反面人物形象。而單純的模仿是不能稱之為戲擬的,只有在模仿中加入滑稽和戲謔的成分,使這種模仿產(chǎn)生喜劇嘲諷的效果才稱得上戲擬。塞萬提斯在模仿騎士小說中的人物設(shè)定時加入了大量的滑稽戲謔成分,被他設(shè)定為高貴的騎士堂吉訶德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一個年老瘦弱的平庸鄉(xiāng)紳,而騎士的侍從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侍從,只是一個一心想得到一個島嶼并作總督的貧窮農(nóng)民,騎士美麗的情人杜爾西內(nèi)婭其實不過是一個健壯粗陋的農(nóng)婦,而與騎士發(fā)生爭斗的各個反面人物也只是兩架大風(fēng)車、兩群羊和幾個普通的腳夫而已,這種戲擬手法的使用使小說頗具喜劇和嘲諷效果。其次,作者對舊有騎士小說的小說情節(jié)進行了滑稽的模仿,根據(jù)騎士小說中騎士在城堡接受地位崇高的大人賜予“騎士封號”這一情節(jié),作者模仿出了堂吉訶德在臟亂差的客店中,請求俗不可耐的店主封自己為騎士的戲謔情節(jié)。此外,作者還讓堂吉訶德模仿騎士小說中騎士的言行舉止,比如騎士小說中的騎士幾乎是不用睡覺的,他們在游行中總是干著懲惡揚善、除暴安良的工作,因而作為騎士的堂吉訶德也經(jīng)常干著守夜的工作并且對毆打孩子的地主進行了威脅和阻攔,最夸張的是堂吉訶德還模仿騎士在求愛時所接受的苦修,但是他硬生生地把苦修模仿成了發(fā)瘋。總之,《堂吉訶德》整部小說都采用了戲擬這種敘事手法,因而使得小說十分具有喜劇效果。
(二)反諷手法的采用
使小說具有后現(xiàn)代性敘述特征的除了戲擬手法的運用外,其中作者所采用的反諷手法也是不可或缺的關(guān)鍵。反諷作為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敘事手法,主要指的是作者實際要表達的真正用意與作品表面呈現(xiàn)出的意義是完全相反的,作品產(chǎn)生的這種反差效果被稱為反諷。《堂吉訶德》這部小說的反諷主要集中表現(xiàn)在小說的人物的整體形象以及他們的語言和行動上。首先,從騎士形象的整體塑造來看,小說塑造出的堂吉訶德這樣一位具有高尚的騎士道精神的騎士,表面看來是對這類騎士的推崇,但其實作者的真正用意卻是對堂吉訶德所代表的騎士進行的批判與諷刺,因為騎士身上所謂崇高的騎士精神在現(xiàn)實里不僅是虛無的,而且還沒有什么實際的用處,甚至還會起到反作用。另外,小說中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也極具反諷意味,這種反諷意味可以從堂吉訶德從地主手中拯救將要被毆打的孩子這件事得到最具體地體現(xiàn),從表面看,堂吉訶德救孩子這一行為是出于善心,但是實際上僅是堂吉訶德完成自己對騎士道精神追求的一種私心,他在完成了騎士應(yīng)該完成的勸阻發(fā)誓行為后就瀟灑地騎著馬離去了,并沒有真正為孩子的現(xiàn)實處境多做任何的考慮,所以這種實際的偽善和表面上的真善形成了強烈的反諷效果,而毆打孩子的殘暴的地主,一邊嘴上說著不再毆打孩子并且要付孩子工資,一邊卻把孩子緊緊綁在了樹上開始了狠狠的毒打,這也是作者對這類言行不一致的人進行的反諷。總之,《堂吉訶德》這篇小說中使用的戲擬、反諷的敘事手法是頗能體現(xiàn)出后現(xiàn)代主義的敘事特征的。
三、敘事結(jié)構(gòu)的后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
解構(gòu)與重構(gòu)是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作品常采用的敘事解構(gòu),《堂吉訶德》這部小說便采用的是這種重構(gòu)與解構(gòu)雙線并行的敘事結(jié)構(gòu)。縱觀整部小說,敘事結(jié)構(gòu)一直處于不停地重構(gòu)與解構(gòu)當(dāng)中。
(一)騎士小說內(nèi)容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
塞萬提斯對騎士小說內(nèi)容的解構(gòu)表現(xiàn)在他對舊有騎士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和情節(jié)進行了解構(gòu)。小說中,作者對堂吉訶德的騎士形象、桑丘·潘沙的侍從形象、杜爾西內(nèi)婭的情人形象,以及與騎士抗?fàn)幍姆疵嫒宋镄蜗蠖歼M行了不同的程度的解構(gòu),又在重構(gòu)時賦予每個人物現(xiàn)實與虛構(gòu)的二重身份,如堂吉訶德的鄉(xiāng)紳與騎士身份,桑丘·潘沙的農(nóng)民與侍從身份,杜爾西內(nèi)婭的農(nóng)婦與貴女的身份等。同時,作者也對堂吉訶德分裂的人格做了突出的表現(xiàn),當(dāng)堂吉訶德清醒時,他是無比的睿智與聰慧;當(dāng)他精神失常時,又是那么的愚蠢和笨拙。另外,作者對騎士小說內(nèi)容的解構(gòu)和重構(gòu)還表現(xiàn)在對舊有騎士小說情節(jié)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中,他打破了舊有騎士斗爭的悲壯情節(jié),在重構(gòu)這種斗爭情節(jié)時加入了搞笑與滑稽的成分,比如小說中就細致地描述出了他誤把風(fēng)車當(dāng)敵人發(fā)起進攻的情節(jié),“他戴好護胸,攥緊長矛,飛馬向前,沖向前面第一架風(fēng)車,長矛刺中了風(fēng)車的翼,可疾風(fēng)吹動風(fēng)車的翼,把長矛折斷成幾截,把馬和騎士摔倒在田野……”作者對人物形象和小說情節(jié)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旨在表現(xiàn)出一種用想象重構(gòu)現(xiàn)實,用現(xiàn)實解構(gòu)想象的顛覆傳統(tǒng)的特點,從而起到消解騎士小說意義的作用。
(二)騎士小說形式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
《堂吉訶德》這部小說在文體形式上對原有的騎士小說的形式進行了解構(gòu)與重構(gòu)。小說在文本形式上已經(jīng)不再是傳統(tǒng)的騎士小說了,作者打亂并拆分了騎士小說原有的敘述模式,在對小說進行重構(gòu)時,將小說、評論以及詩歌等各種文體雜糅在一起共同組合成了新式的騎士小說。小說一開篇就加入了敘述者的評論,在談到堂吉訶德的別名叫吉哈納時,敘述者評論道:“細推來,他應(yīng)該叫吉哈納,不,這對于我們來說無關(guān)緊要,只要我們說起他來不是虛妄之論就行。”敘述者評論的加入,為小說增添了親切感,拉近了讀者與敘述者的距離。另外,上卷的第十四章開篇就寫到了已經(jīng)去世的牧人留下來的詩歌:“狠心的姑娘,你既要眾口宣揚/你堅如鐵石又冷若冰霜/我得把地獄里慘叫的聲音/裝入我幽抑苦悶的胸膛……”詩歌的加入也增加了小說的文學(xué)性。塞萬提斯對騎士小說的內(nèi)容和形式的雙重解構(gòu),使小說完全具備后現(xiàn)代性的特征。
四、敘事方式的后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
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這篇小說中采用了元敘述的敘事方式,這種敘事方式使小說內(nèi)容出現(xiàn)了一系列悖論,這種悖論導(dǎo)致了小說的真實性是不確定和不可靠的。首先,小說中存在的多個敘述聲音是小說產(chǎn)生悖論的關(guān)鍵原因,小說的作者、敘述者、譯者以及讀者交替地出現(xiàn)在這部小說中。最先出場的是作者,他出現(xiàn)在序言中,當(dāng)作者正在寫一篇序言時卻又偏說自己并沒有寫序言,這是互相產(chǎn)生悖論的。接著出場的是敘述者,小說的敘述者有兩個,一到九章是一個敘述者,而剩下的章節(jié)作者又選擇了阿拉伯的歷史學(xué)家來擔(dān)任敘述者,不同的敘述者是不可能寫出一部相互銜接、連貫的小說的,這與敘事的完整同一是相悖的。并且,當(dāng)敘述者在敘事時,作者自己和譯者又不間斷地對敘述者敘事的真實性進行了評論,甚至在下卷中還出現(xiàn)了上卷的讀者來為敘事的真實性做擔(dān)保。另外,小說中除了敘述聲音的此起彼伏和互相對立外,小說人物是否真實存在也瓦解了小說的真實性和確定性,這表現(xiàn)在堂吉訶德派桑丘·潘沙去找他的情人杜爾西內(nèi)婭時,桑丘·潘沙卻從未見過杜爾西內(nèi)婭,包括她現(xiàn)實中的農(nóng)婦原型也從未在小說中真正出現(xiàn)過,因為堂吉訶德在路上見過的那三個農(nóng)婦中根本沒有真正的杜爾西內(nèi)婭的原型,那不過是桑丘·潘沙隨便編造出來欺騙堂吉訶德的。并且,作者借下卷公爵夫婦之口對杜爾西內(nèi)婭是否確有其人的懷疑表達了這個人物和她的原型可能并不存在。這樣的敘述安排使《堂吉訶德》這部小說的真實性被瓦解,從而突出了小說的不確定性,小說中還存在相類似的悖論,這些悖論和對立剛好表現(xiàn)出了《堂吉訶德》具有后現(xiàn)代小說的不確定性。
本文通過對《堂吉訶德》這部小說的敘事語言、敘事手法、敘事解構(gòu)和敘事方式來分析和研究了該小說的敘事藝術(shù),并總結(jié)出該小說最突出的敘事特征就是在它敘事中蘊含了濃厚的后現(xiàn)代性,這種敘事藝術(shù)打破了傳統(tǒng)敘事的局限,充滿了實驗性和先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