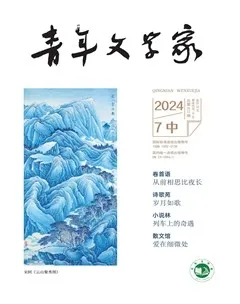《嘉莉妹妹》中的共時意象空間建構


西奧多·德萊塞(1871-1945),是美國現代小說的先驅,現實主義作家之一。《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這兩部小說奠定了西奧多·德萊塞在美國文學史上承前啟后、立足當世的小說家的地位。辛克萊·劉易斯曾評價《嘉莉妹妹》道:“其為寫實且充滿激情的生活掃清了維多利亞式、豪威爾斯式的文雅之風。”(《來自大街的人:精選散文和其他作品》)西奧多·德萊塞身處美國自然主義向美國現代主義邁步的過程中,前接現實主義“摒棄”理想之風,后啟現代主義,并被譽為美國現代小說先驅。同時在20世紀,評論界認為西奧多·德萊塞與福克納、海明威并列為“一戰”之后美國僅有的三位小說家。與福克納醉心于意識世界,海明威以行動證明“此在”相比,西奧多·德萊塞在“自由主義的想象”與打破傳統的敘事方式方面顯得觀點獨到,令人耳目一新。盡管西奧多·德萊塞的小說家地位已毋庸置疑,國內對他的研究卻略顯曲折。《外語教學與研究》(曾用名《西方語文》)1957年第3期刊載的朱樹飏的《西奧多·德萊塞:偶像破壞者》是國內研究西奧多·德萊塞的首篇論文。這篇論文在對西奧多·德萊塞諸多作品分析的基礎上,著重強調西奧多·德萊塞創作過程本身及當時美國社會的歷史語境,反思鍍金時代(Gilded Age)的偽善,雖含有社會學批評立場的韻味,但其對西奧多·德萊塞生平諸多作品的總結和剖析無疑是當時乃至現在的重要參考資料。之后對西奧多·德萊塞的研究便進入了漫長的停滯期,直到1981年出現了毛信德的《德萊塞簡論》,此文將西奧多·德萊塞人生創作劃分為幾個時期與階段,讓人們較為全面地領會了西奧多·德萊塞創作的成熟之路。以這兩篇“開山之作”為背景,后續涌現了圍繞《嘉莉妹妹》中的物品產生的諸多城市研究、圍繞嘉莉本身的女性研究,以及所蘊含的自然主義決定論的哲學研究等關于《嘉莉妹妹》的文學內外部研究。
然而,各式理論的輪番上演,都缺乏對《嘉莉妹妹》中時間和空間的較為深層的探究。龍迪勇曾在《空間敘事學》中提出:“敘事在時間上具有久遠性,在空間上具有廣延性。”《嘉莉妹妹》中并不缺乏這種康德式的“先驗的感性形式”,“時間和空間只有預設對方的存在并以之為基準才能得以考察和測定”。面對“并置”(Juxtaposition)這種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紀實與虛構”的敘事手段,傳統的“經典敘事學”向“后經典敘事學”的偏重時間維度的轉向已不能滿足空間維度的作品研究了。當然,源自結構主義春風下的“空間敘事學”方興未艾,不得不承認作家們的創作心理仍然是探討空間敘事學的合理出發點,敘事中的“來源”依舊是不可或缺的著墨點。
因此,本文旨在揭開西奧多·德萊塞筆下美國城市的神秘面紗,嘗試闡釋出西奧多·德萊塞對美國物質文化中的城市空間的認識和觀照,進而剖析在此過程中形成的“現代性”的先驗領悟和超前批判。
一、《嘉莉妹妹》中的四種空間單位
追根溯源,西奧多·德萊塞在創作《嘉莉妹妹》時存在其創作心理的空間特性。“意識事件”就是“指在敘事行為即將開始之際出現在敘述者意識中的事件”(龍迪勇《空間敘事學》)。西奧多·德萊塞曾在自傳中發出這般感慨:“有時候,當我現在回頭看它,那些普通的墻壁似乎只包含了讓我討厭和不愉快的東西,然而我知道,人們在那里心滿意足地工作……他們似乎是馬……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就被環境擺布。”(西奧多·德萊塞、理查德·道威爾、詹姆斯·L·W·韋斯特、內達·M·韋斯特萊克《業余勞動者》)在西奧多·德萊塞回憶其創作旅程時,時常追憶往日寫作的艱難時光。這種“有意回憶”超脫了時間上的流俗,在其作品中更體現了社會發展的縱深維度。
此外,西奧多·德萊塞企圖在《嘉莉妹妹》中展現現代性城市符號、隱喻與象征。“對城市情況的個性理解;《城市》中論述的城市發展進程典型地基于文雅舉止的個人主觀性,他們的個人選擇成為包括空間結構、犯罪、窮困和種族主義在內的總體城市情況的最終詮釋。”(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城市文化讀本》)個人的時間線與城市空間結構相結合,使“被敘述的空間”有了共時的含義。創作主體讓位空間事物。作者的記憶為城市描繪上了絢麗的色彩,空間也不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單位,而是充滿人文色彩的底蘊。當然,西奧多·德萊塞作品中的空間既是嘉莉等人的遭遇,也是自己創作歷程的真實寫照。由此“形象的跨主體性”在《嘉莉妹妹》中呈現的也是一幅作者與作品、作品與時代、時代與讀者的精神畫卷。
《嘉莉妹妹》里的空間建構可分為四種類型。其一,微觀空間,即具有特殊含義的房間中的擺件、搖椅等。其二,宏觀層面的公共空間,包括街區、景觀、百貨商店等。往往這些地方與主題的關聯最為密切,街上的行人與餐廳里的顧客,透過玻璃的對視與回眸便是他們時間與空間上的相遇。主體建構的空間范疇也在作品中脫離了物理的空間單位的概念。其三,具有臨界屬性的空間單位。《嘉莉妹妹》中曾多次出現“門廊”的意象,“門廊”“窗臺”都是具有“跨境”的空間結構。這種空間上的“內”與“外”更增添了空間建構的外延性,然而這種空間絕非靜止的,而是可流動的、可跨越的。其四,聽覺下的空間單位。西奧多·德萊塞立體地構建了空間單位,滿足了作者“期待視野”,拉近了與當代城市中生活的讀者的距離。
二、微觀意象性空間
《嘉莉妹妹》中并未出現“家”的字樣,而是用flat、address、number等指代嘉莉的住所。這樣的安排實則是現實照進了作品的一種現象。西奧多·德萊塞在艱苦創作的過程中,曾在囊中羞澀時去他姐姐家吃了一頓飯,他姐姐關心地詢問他的住所,出于自尊的西奧多·德萊塞當時給出的是錯誤的“柳樹大道414號”。而作品中嘉莉對杜洛埃的來訪,表現出的是刻意的躲閃。毫無疑問,現實中的西奧多·德萊塞和作品中的嘉莉都存在著挽尊之舉。
當然,“家”也是嘉莉逃離現實的臨時居所。在這片四角天地中的搖椅上,她看到的是“燈光照耀的街道”“湖濱大道上的宅邸”,在“家”中的搖椅上,她再也聽不到總是騷擾她的男同事的呢喃,以及機器咔噠咔噠的打眼兒聲。然而,這些聽不到的恰恰是19世紀末最為熱鬧的聲音。1890—1910年間,美國人口大幅增長,經濟也迅速發展,每個大亨都站在由低級雇員組成的金字塔的塔頂,自此美國走向前所未有的繁榮期。
而早在定居“家”之前,狹小封閉的火車車廂早已讓時間與空間糾纏得難舍難分。初來乍到的嘉莉面對杜洛埃的殷勤雖顯矜持,但杜洛埃口中的林肯公園和芝加哥河都是嘉莉未曾涉足的地方。不同的時間線的人生經歷在這狹小的空間內交織在一起。車廂作為理性秩序空間的代表,增加了旅途中嘉莉對于芝加哥的想象與期待,命運的齒輪已隨著火車的飛馳而悄然轉動。而第二次的火車之旅則更是推動了時空的壓縮與情節的發展。火車的行進對于解決這個僵局起到了很大作用。赫斯渥違背嘉莉意愿的私奔之舉,使得在飛速行進的火車上的嘉莉也變得無可奈何。現代化初期的行進設備,悄然改變了人們的選擇和認知,物開始逐漸影響甚至控制人的抉擇。
三、宏觀意象性空間
走出“家門”,芝加哥與紐約的魅力更是令嘉莉意亂情迷。嘉莉尤其羨慕批發商行里的職員“可以看到明亮整齊的辦公桌椅和滿世界的毛玻璃,看到職員在埋頭工作,看到溫文爾雅、身著時髦西裝的干凈襯衫的商人或踱步,或幾人坐在一起”。嘉莉眼中逡巡而不敢進的“高級”批發商店鋪,何嘗不是作繭自縛囿“完整的人”于空間之內的桎梏。“圍城”式的“云泥之異”與“天壤之別”實則是彼此缺乏現代性的自我審視與批判的現象。
走進劇院,嘉莉的命運迎來了真正的轉變。在劇院這一公共場域下,體現的是資本主義“服從”和“義務”等原則。初次登臺的嘉莉因為有赫斯渥等人的蔭庇,對此并無過多體會。在不得不謀生時,秩序終于露出了它本應該有的獠牙:“那你為什么不跳呢?別像死人一樣把腳拖來拖去。我需要的是充滿生命力的人。”20世紀的劇院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已悄然發生了質變,不再是“弄臣”與國王之間權力不對等的游戲,而是帶有“進取”“征服”意義上的觀眾與演員的對話。博得滿堂彩一方面是觀眾對嘉莉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嘉莉階層個體凌駕中產的表征。面對包廂中“麋鹿會的紳士們”,嘉莉的表演“高傲而輕蔑”。這樣看來,曾經與嘉莉相知相伴的杜洛埃和赫斯渥,不過是嘉莉事業道路上的墊腳石罷了。相比大獻殷勤的杜洛埃和赫斯渥,與嘉莉有緣無分的艾姆斯卻是其演藝生涯的導師。“要當一名出色的演員。我覺得演戲是一種偉大的事業。”僅僅這一句贊美的話就讓嘉莉怦然心動。嘉莉明顯曲解了艾姆斯的本意,悟出了這句話不應該存在的“弦外之音”:“倘若她成為優秀演員,就可以贏得他這種男人的贊美。”劇院之下是多組二元對立的演練場:命令與服從、秩序與混亂、無不異化和分裂著嘉莉。
四、具有臨界屬性的意象性空間
在姐姐家,唯一令嘉莉感到寬慰的幻想之地,便是連接“內”與“外”的走廊。這不起眼的連接居所與城市街道的狹小空間,卻是嘉莉在現實與理想掙扎時的唯一出口。初次向姐姐和姐夫提議去雅各布戲院的嘉莉,在姐夫不以為然地搖頭中作罷。“我想下樓去,到樓梯角那站站。”如果說這次的逃離是“內”力所推,那么第二次的樓梯口便是“外”力所引。擔心杜洛埃會來找她的嘉莉,早已站在門道上等待,而她所真正期待的并不是來去無常的那個男人,而是幻想著紙醉金迷的夢。“街上的景象使嘉莉激動不已,心情久久難以平息……她的想象兜著小圈子。總是停留在與金錢、打扮、服飾或享樂相關的項目上……周圍的小世界占據了她全部的注意力。”人與人的關系逐漸淡漠,即使是血親面前;而人與物的關聯卻越發緊密,小小的門道隔絕了時間、混淆了空間,重現的是嘉莉在“存在”中的理想“此在”。
“家”也逐漸變成了區分階級的場所。大紅大紫的嘉莉被引至威靈頓飯店下榻。而富麗堂皇的“家”空間對其異化也加快了腳步。“我不知干什么好。”一天,嘉莉坐在一扇俯瞰百老匯大街的窗戶旁,對蘿拉說道:“我覺得很寂寞。你呢?”資產階級往往通過對物的占有來抵抗瞬息萬變、稍縱即逝的現實世界。此時的居所實則是紐約這座大城市的暗喻—富麗堂皇的裝飾,遺世獨立的富貴,然而這卻是頂級的異化,因為它有悖人性與人倫。威靈頓飯店只是嘉莉的臨時居所,在這里沒有家人、親人和愛人的陪伴。所謂的欲求不滿之后的空虛,嘉莉體會得淋漓盡致。
五、聽覺意象性空間
西奧多·德萊塞筆下“聲色犬馬”的芝加哥和紐約城又怎么少得了聽覺的感知與體認,聽覺維度的“觀照”甚深。對此西奧多·德萊塞早已開宗明義:“諸般美景宛如音樂一般,常常會使頭腦簡單的人放松警惕,削弱他們的意志,使他們走上邪路。”在認識事物時,視覺讓位聽覺,在主體構建與空間想象的過程中,音樂是功不可沒的。“我不知道音樂是怎么一回事”,她心潮澎湃,涌起難以名狀的向往,“但音樂總讓我覺得自己好像期望著什么……”毫無疑問,“把我們引入歧途的常常不是邪惡。而是對美好事物的渴望”。欲望不僅會物化,更會以有聲的方式將城市的形象在嘉莉的腦海中一次次地勾勒出來。
當然“聲音”有時并非物理意義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回聲。
“‘唉,你失敗了!’那聲音說。‘為什么?’她問。‘看看周圍的人吧。’它耳語道:‘看看那些好人吧。他們瞧不起你的行為。看看那些正派的姑娘吧,特別她們知道你是個軟蛋,一定會遠遠躲開你。你未曾嘗試就屈服了。’”“每當嘉莉獨自一人向外眺望公園的時候,她就會聽到這個聲音。當沒有別的事情打岔時,當生活中歡快的一面有點模糊時,當杜洛埃不在眼前時,這偶爾出現的聲音便會在耳邊響起……她總要回答……她孤苦伶仃,想找點事情做。可是害怕呼嘯的寒風。這些困難就是她的回答。”這里嘉莉對“聲音”的感知是被動的。這種“雙聲部”現象總是以見縫插針的形式審問嘉莉的行徑是否符合道德標準。對于“浮士德困境”的處理,嘉莉表示這也是無可奈何之舉。欲望在寄人籬下的外衣下有了其正當的理由。
西奧多·德萊塞在《嘉莉妹妹》中運用社報編輯的細膩手法將不可捉摸的時間空間化,通過空間敘事學建構了19和20世紀之交的美國城市生態。當然,其中嘉莉流露出的不僅僅是西奧多·德萊塞文學之路的現實寫照,也是對消費主義下的“現代性”的批判。與物理空間描述不同,西奧多·德萊塞筆下的宏觀、微觀的意象性空間呈現的是美國城市的欣欣向榮,視聽雙感共同參與了城市印象的個體化建構。
原本體現政治與軍事形態的城市,早已呈現出資本主義飛速上升的特征。現代性的消費主義、功利主義悄然影響著以嘉莉為原型的人。同時,人的異化也與城市發展呈“正相關”態勢。西奧多·德萊塞是為數不多揭示這種偶然與必然的城市現代化問題的專家。然而,這種超前領悟與批判對“現代性”的理解也只有在“大蕭條”之后的回憶中不斷地被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