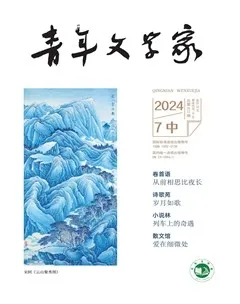敦煌《燕子賦(甲)》及其發展源流研究
賦是中國文學中的重要類型與兩漢文學的代表,提起它人們通常想到的是氣勢恢宏的漢大賦,其實不然,還有一種別具風格的賦同時存在和發展,那就是俗賦。關于俗賦,馬積高先生在《賦史》中將其定義為“清末從敦煌石室發現的用接近口語的通俗語言寫的賦和賦體文”,這一定義是針對唐代敦煌俗賦而言的,事實上俗賦的產生遠遠早于唐代,它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燕子賦(甲)》(以下行文簡稱《燕子賦》)便是一篇典型的俗賦,它以動物代言形式敘述故事,行文以四言句為主,語言通俗,風格詼諧,情節完整,是敦煌俗賦中的優秀代表。但《燕子賦》這類擬人故事賦并非憑空出現,它與西漢的《神烏賦》、三國曹植的《鷂雀賦》有著重要的文學淵源。本文將在對《燕子賦》基本情況進行介紹的基礎上,探究俗賦中擬人故事賦的發展源流,同時將《燕子賦》與《神烏賦》《鷂雀賦》進行對比,以期對擬人故事賦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敦煌《燕子賦》基本情況
《燕子賦》在敦煌卷子中有七個寫卷,一是P.2653,開端稍有殘缺;二是P.2491,全,賦題作“燕子賦一卷”;三是P.3666,末尾殘缺,賦題作“燕子賦一卷”;四是P.3757,只存開端十八行;五是S.6267,太破損,多斷行;六是S.214,卷首殘缺;七是S.5540,僅存末尾一小段。除以上七卷外,根據伏俊璉的《兩篇風格迥異的〈燕子賦〉》,P.4019《書儀》后還殘存《燕子賦》后半一段,以及俄國孟列夫編的《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第1484號著錄有此篇。本賦的寫作年代,從雀兒自述參與唐太宗征遼事可知寫作年代上限不超過貞觀十九年,再結合雀兒恐嚇燕子時說“明敕括客”可知此賦當作于武周圣歷元年實行“括客”政策以后,以及唐玄宗開元九年至十二年朝廷對逃戶給予優遇之前。再結合《燕子賦》開頭的詩歌“雀兒和燕子,合作《開元歌》”推斷,此賦當作于唐代開元末年或天寶初年。關于本賦的作者,這幾個卷子都未有記載,但通過對比《資治通鑒》可看出,《燕子賦》對征遼一事描述得很準確詳細,只有官員或能接近上層的文人才可能知道得如此詳細。而且,賦中多引用史籍中的典故,并能熟練化用,可見作者有很好的文學修養。故而可以推測出作者是文人或者是有良好文學修養的官吏。
《燕子賦》的故事情節很簡單,敘述了仲春二月,燕子夫婦剛剛建好巢穴就被雀兒一家強占,燕子被打,于是向鳳凰告狀,鳳凰判案,雀兒因有上柱國的功勛得以免罪釋放,最后燕雀和好的故事。文中大量運用俗語,生動活潑,是一篇具有鮮明民間風格,思想性和藝術性很高的佳作。總體來看,《燕子賦》具有以下特征:其一,采用對話體形式,語言上使用四言韻語,且根據內容需要自由換韻。用語通俗淺近,多摻雜俗語,形成詼諧幽默的風格。其二,作為一篇擬人故事賦,《燕子賦》以物喻人,塑造了燕子、雀兒、鳳凰、鴇鷯等眾多生動的禽鳥形象,編織成一張社會關系之網,在揶揄戲謔中鞭撻現實。
二、由《燕子賦》看擬人故事賦的發展源流
以禽鳥代言敘說故事的俗賦歷史悠久,從《詩經》中的禽言詩開始,到先秦諸子的動物寓言故事,再到漢代的《神烏賦》、三國的《鷂雀賦》,最后到《燕子賦》,清晰展示了這類賦作的發展源流,并對后世文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以禽鳥為主角的擬人故事賦其發展淵源可上溯至《詩經·鴟鸮》,“鴟鸮鴟鸮!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這首詩以一只母鳥的口吻,訴說被鴟鸮抓走幼鳥后依舊辛苦經營修補巢窩的感受,堪稱一首借鳥寫人的佳作,母鳥受鴟鸮的欺凌而喪子破巢的遭遇正是底層人民悲慘情狀的形象寫照,母鳥凄慘的呼號與怨訴傳達著底層人民的不盡悲痛。這首詩語言較為通俗,全篇基本用四言,在語言、句式以及擬人手法的應用上都與俗賦十分相近。先秦諸子也常用寓言故事來表達觀點,《莊子》中就有很多動物寓言故事,這些動物也像人一樣對話,如《逍遙游》中大鵬展翅飛向南冥,蜩與學鳩對它加以評論;《秋水》記載了坎井之蛙與巨鱉的對話。這些動物寓言故事雖然與禽鳥相爭的故事還有所不同,但是這些寓言擬人化的手法和豐富的想象對禽鳥類擬人故事賦的產生肯定會有一定的影響。
到漢代,以禽鳥相爭為題材的擬人故事賦真正出現的標志是1993年江蘇連云港尹灣村漢墓出土的《神烏賦》,它的出現填補了俗賦發展源頭的空白,將俗賦的歷史提前到了漢代,也使我們得以弄清《燕子賦》的源頭和承繼關系。《神烏賦》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陽春三月,神烏夫婦經過考察決定將巢筑在府君宅邸的高樹上,不料筑巢的材料被盜鳥偷竊,雌烏去追討并譴責了盜鳥的盜竊行為,但盜鳥態度蠻橫,拒不承認盜竊,雙方廝打在一起,雌烏不敵,受傷墜地,被官府的捕頭捕獲后系在柱子上,盜鳥反而逍遙法外。雌烏僥幸掙脫了綁縛逃回巢中,但余縛纏身,雄烏施救無果,欲與雌烏共同赴死,雌烏勸雄烏要好好生活,隨即投地自殺,雄烏悲痛離去。《神烏賦》作為一篇擬人故事賦,成功塑造了雌烏、雄烏與盜鳥三個形象,借神烏夫婦的悲慘遭遇表達了對社會的批判。但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和強權的壓迫,作者也無能為力,能做的只有逃避,主張效法鳳凰、蛟龍,遠世避禍。全賦以雌烏與盜鳥、雌烏與雄烏的對話敘述故事,聲容辭氣各肖其身份,對話具有論辯性質,基本上是四言韻語,換韻自由,語言通俗易懂,是一篇比較典型的擬人故事賦。這篇俗賦的出現也讓人看到了賦的另一面,不光有文辭優雅的文人賦,也有通俗接地氣的俗賦,展現了賦文學的多樣性。1996年《文物》雜志刊登的《尹灣漢墓簡牘初探》也認為《神烏賦》“其風格跟以往傳世的大量屬于上層文人學士的漢賦有異,無論從題材、內容和寫作技巧來看,都接近于民間文學”。
沿著《神烏賦》開創的道路,曹植接續發展,在吸收民間俗文學養分的基礎上加以文人化的改進,創作了《鷂雀賦》與《蝙蝠賦》兩篇動物賦。但《蝙蝠賦》多殘缺,已很難考證,唯有《鷂雀賦》可供研究。《鷂雀賦》主要寫的是鷂要捕食雀兒,雀兒巧辯逃走的故事。雀兒先是巧言辯詰,勸說鷂不要吃自己,再憑著自己的機智敏捷,利用多刺的棗樹避難,后兩雀相遇,雀兒先是夸耀一番,同時又發出一種脈脈溫情的無望的呼喚,“自今徙意,莫復相妒”。此賦篇幅雖短小,但賦中鷂、雀二鳥的對話惟妙惟肖,二鳥的情態與動作在對話中都得以生動體現,而且此賦全用俗語寫作,不落文人辭賦的窠臼,還雜有民間俗語,反映了曹植在俗賦創作過程中對民間文學的吸收。在題材上,《鷂雀賦》雖不是寫禽鳥奪巢、爭巢,但主題仍是兩鳥相斗,雖然雀兒弱小,根本無法與鷂相斗,但可看出與《神烏賦》中雌烏與盜鳥相斗不敵的情節類似。禽鳥相斗的情節在民間文學中存在歷史悠久,漢代不光《神烏賦》描寫了這一題材,焦延壽的《焦氏易林》卦辭中也多有涉及禽鳥相爭的情節,如《明夷》卦:“鶴盜我珠,逃于東都。鵠怒追求,郭氏之墟。不見蹤跡,使伯心憂。”這與《神烏賦》的情節相差無幾。再比如《焦氏易林·大有之十四》:“雀行求食,出門見鷂,顛蹶上下,幾無所處。”這與《鷂雀賦》中的情節也十分相似。可見,禽鳥相爭的情節在漢代就已十分流行,曹植寫作《鷂雀賦》時應該是在題材上對這種民間流行的故事予以了吸收。在曹植的影響下,后世也有文人參與到了擬人故事賦的寫作中來,如晉代傅玄的《鷹兔賦》,成公綏的《蜘蛛賦》《螳螂賦》,宋齊時期卞彬的《蝦蟆賦》,北魏元順的《蠅賦》等,都是借物寫人的佳作,可見擬人故事賦在當時很盛行。
到了唐五代時期,俗賦更為興盛,就是處于西北邊陲的敦煌,俗賦也在寺僧、學郎、小吏之間廣為流傳,敦煌藏經洞中就保存了《晏子賦》《韓朋賦》《燕子賦》《茶酒論》等多篇優秀賦作。其中《燕子賦》就是沿著《神烏賦》與《鷂雀賦》開創的道路繼續發展,在題材和形式上吸收借鑒了前二者,都以禽鳥為主角,使用代言體敘說故事,都使用四言韻語,換韻靈活,語言通俗,風格詼諧,都吸收了民間文學的素材,由此可見從漢魏俗賦到敦煌俗賦之間清晰的傳承線索。
宋元以來,以說話、雜劇、諸宮調等為代表的俗文學的興起和文人文學的發展對俗賦造成巨大沖擊,俗賦逐漸衰落,擬人故事賦更是十分罕見,現今可見的唯有蘇軾的《黠鼠賦》一篇。在賦中,蘇軾以幽默的口吻描寫了一只老鼠裝死逃脫的故事。此賦語言通俗,具有口語化特征,風格詼諧幽默,是一篇俗賦佳作。
三、《燕子賦》與《神烏賦》《鷂雀賦》之對比
《燕子賦》與《神烏賦》《鷂雀賦》都是同類俗賦,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性。相較而言,三者的共性主要體現在情節、題材的相似性,它們都反映了同一母題。從故事內容來看,這三篇賦都涉及因巢穴而引起禽鳥相爭、打斗的母題,這種“禽鳥奪巢”或是“鳩占鵲巢”的母題并非只存在于這三篇賦中,如唐代李頻的《黃雀行》,其中有“朱宮晚樹侵鶯語,畫閣香簾奪燕巢”之句;韋應物的《鳶奪巢》,其中有“野鵲野鵲巢林梢,鴟鳶恃力奪鵲巢”之句,等等。可見雀奪燕巢的故事在唐代十分流行。再比如藏族故事《駱駝和山羊》講的是迷路的駱駝向山羊借宿,最終占領了羊棚還把山羊趕到外面凍死了的故事。從社會學層面來看,這一母題所敘述的故事無疑是不公平社會現象的投影,作者借這一母題敷演故事,意在表達對豪強逞兇凌弱的批判和對弱者的同情。
除了共性外,《燕子賦》與《神烏賦》《鷂雀賦》還存在很多不同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對祖本的改寫體現出不同的情感內涵與審美傾向。過去的敦煌研究者在探究《燕子賦》源流時,一般都認為《燕子賦》繼承了漢魏以來的俗賦傳統而有所發展,舉例說明時最遠也只能提到《鷂雀賦》,直到《神烏賦》的出土才使人們弄清楚了《燕子賦》的祖本是《神烏賦》。雖然《燕子賦》在情節、技法上都學習繼承了《神烏賦》,但它并沒有一味模仿,而是有自己的創新。《燕子賦》取用了《神烏賦》中神烏夫婦建屋材料被盜,前去追索反受欺,結果“毋所告訴。盜反得免,亡烏被患”的情節,加以發展,改成燕子被雀兒侵占房屋反被打,燕子往鳳凰處訴冤,鳳凰斷案,雀兒被打,最終雀兒以軍功得免,燕雀和好的故事。其將原本的悲劇結尾改寫成了喜劇,變成了皆大歡喜的結尾。究其原因,當與不同時代的精神內涵與審美傾向有關。漢、唐雖同為鼎盛王朝,以漢賦、唐詩為代表的文學作品也都顯現出宏偉的氣象,但深入而言,漢代氣勢恢宏、波瀾壯麗的文學風貌之下還有著渾樸悲壯的一面,如《古詩十九首》蘊含著濃郁的感傷之情,《胡笳十八拍》《孔雀東南飛》給人沉重憂郁之感,漢代集史學與文學之大成的《史記》更體現出強烈的悲劇色彩,它們共同形成一種悲劇氛圍,在此背景下,《神烏賦》也通過神烏一家的不幸遭遇體現出悲傷之情與無可奈何之感。相較而言,唐代文學則體現出盛大雄渾的美學風貌,洋溢著青春氣息,唐代的美學風貌似乎有更多的底蘊,更大的氣勢,在此影響下產生的《燕子賦》自然充滿了歡快與樂趣,體現出積極向上的心態。雖然社會上有“雀兒”這樣的惡棍存在,但“燕子”這樣的平民百姓仍然相信正義的存在,敢于向“鳳凰”訴冤。其二,敘事能力的發展與成熟。從《神烏賦》到《鷂雀賦》再到《燕子賦》體現出俗賦創作過程中敘事能力的發展與成熟。從篇幅來看,《燕子賦》遠遠超過了《神烏賦》與《鷂雀賦》,描寫對象大大增加,也更加細致生動,如雀兒這個形象通過語言、動作的描寫,將它的狡猾、狂妄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且,《燕子賦》的情節也變得更加復雜曲折,語言更為靈活跳躍,幽默意味極大增強,這都顯示出俗賦從漢發展到唐時,其敘事能力逐漸發展成熟。其三,女性形象的弱化。在《神烏賦》中,雌烏既敢單獨追趕盜鳥,又能對盜鳥好言相勸,相勸不成才訴諸武力。當雌烏重傷將亡,雄烏欲與它共同赴死時,它卻勸雄烏要好好活下去,另娶賢妻,并善待孤子,說完投地自殺。它的勇敢堅決、深明大義和多情重愛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影響,雌烏與漢樂府《病婦行》中的病婦、《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有相似之處。相較而言,《鷂雀賦》與《燕子賦》中的雌鳥形象較為單薄,描寫不足。
總而言之,《燕子賦》作為擬人故事賦中的佳作,不光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還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通過探究其源流演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俗賦的發展歷史。